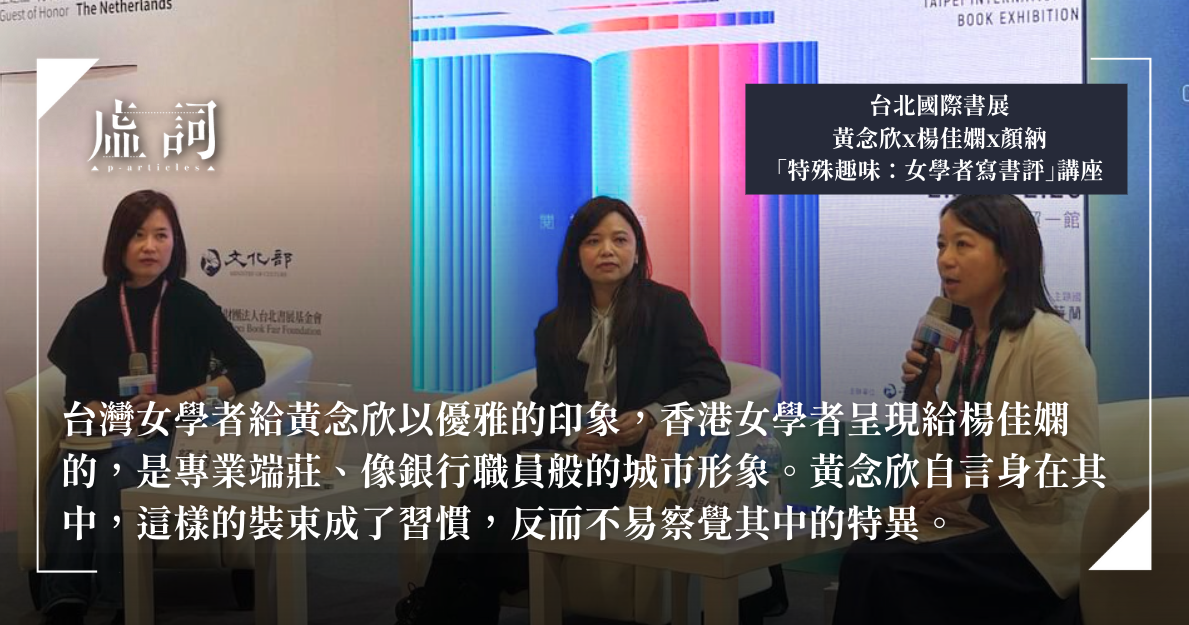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講座記錄"

在擠迫之城擁抱情緒病患者——曾繁光 X 黃怡 X 曾卓然「都市病.病都市」講座記錄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4-03-25
黃怡繼而分享了四篇短篇小說,當中有三篇都收錄在《擠》裡。第一篇〈哭泣的女人〉啟發自畢卡索的名畫 ‘Weeping Woman’,講述一名OL隱瞞抑鬱病歷,以失戀掩飾情緒崩潰的故事。黃怡指,哭泣只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才被允許,否則會阻礙日常,帶來社交困擾,偏偏抑鬱引發的哭泣無可避免,為免被公司作個別看待甚或解僱,女主角選擇謊稱失戀。「主角深信大多數人都能理解分手是怎樣一回事,對失戀的人抱有必然的憐憫和同情,故哭泣是被容許的。然而,抑鬱是一種長期疾病,主角擔心旁人終有日會覺得她已哭夠,故她再度陷入掙扎,思考是否需要再假裝與新男友分手,甚至抄襲愛情小說的劇情,好讓同事不會追根究底,懷疑她有情緒病。」黃怡補充,這些情節看似荒謬,卻全都源於身邊人的真實分享、在社會中面對的不安與憂慮,黃怡的創作常以這些困擾為起點,書寫人物面對的困境。

漣漪繁波漾,參差層峰峙 ——許廸鏘 X 張詠梅「筆落言詮:侶倫《向水屋筆語》注釋的意義和價值」講座記錄
報導 | by 林穎茵 | 2023-09-09
在《向水屋筆語》中能看見作品與時代的關係,也能看見作者情感的變化與矛盾。張詠梅提到:「侶倫自身喜歡感傷頹美的東西,又認為自己的創作很嚴肅等,但侶倫整體的文風是很真誠、樸素、溫和的色彩。」許廸鏘對侶倫的戰時日記更是感受深刻:「就算在戰亂途中仍創作不斷,四周寄稿追求發表。令人驚訝的是當時環境混亂、砲火連天,出版社竟然也能將稿費寄到侶倫的手中。」他更笑言:「慚愧自己編了幾十年雜誌連一個仙都沒有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