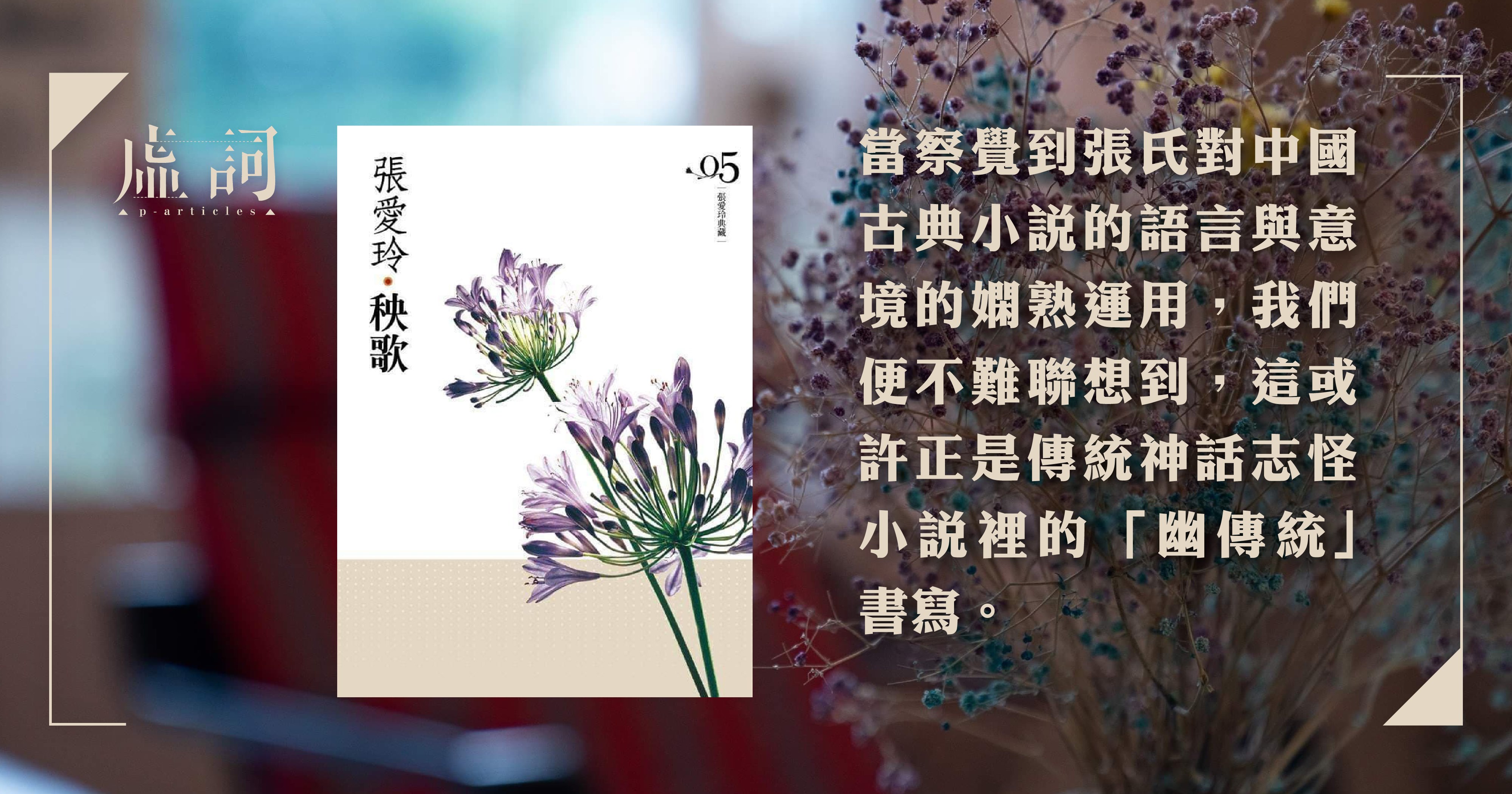【虛詞.張愛玲分重作】百年還魅張愛玲:餘音不散的《秧歌》
「祖師奶奶」張愛玲冥壽一百週年,港台文壇對其重讀與重述蔚然成風;除了重複翻頁紀念,或許這也是讓我們再度開啟鬼魅竄延的契機,試圖從其作品派生更多與時代當下有所對話的異讀可能。這次我想談談長篇小說《秧歌》,那是張氏筆下最為鬼氣森然的作品,故亦當是我們今天所以對其「百年還魅」的重要切入點。
《秧歌》是上世紀五〇年代張氏避居香港時創作的,本以英文書寫並發表,其後自譯並改寫成中文版本。長久以來,此書無論在內容真實性抑或政治意識形態上,都是極具爭議的。一方面,它寫的是中共「土地改革」,張氏卻被質疑從未參與運動;另一方面,它披戴鄉土小說之形,卻似有「反共小說」之實。真實與虛構,形態與精神,在後世的評價中都是不穩定的,意義浮沉徘徊——恰也暗示了張氏自身在中國現代文學系譜上,猶如無家可歸的吉普賽(Gypsy)。若說張氏應歸入中國現代文學群像的任何一系之下,那都總會顯得格格不入,毋寧可稱之為某種境內流亡(domestic exile),以她自己的話便是不無弔詭地「包括在外」。事實上,上世紀九〇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學界基本上鮮談張氏,至近年錢理群、溫儒敏等有關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再)論述,提到張氏篇幅亦較少,只列於鴛鴦蝴蝶派、通俗小說之後,評語寥寥,顯然未受重視。反觀上世紀六〇年代,美國漢學家夏志清(Hsia Chih-tsing)率先舉出張氏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性,於《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並舉之與魯迅、沈從文、錢鐘書等,對《秧歌》等數篇作品大幅稱譽,成為當代張學研究之為顯學的基礎。這現象展示出張氏顯然有別於五四以降中國現代文學正朔的審美視野和意義判斷,而作為了一道無以化約的奇特風景,誠如黃子平說,她是主流文學史無處安放的作家。
帶著如此理解,我們再讀「反共小說」《秧歌》則顯得饒有意思。胡適說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自當也指向其時中國民眾在本體論層面上的空洞與匱乏;今天讀來,我認為未嘗不可以「餓鬼」一詞替代之。飢餓固然具象在對農村飢饉、向官借米的殘酷描寫,但在飢饉來臨前夕,顧岡所感受到那「奇異的虛空之感」,豈非也指向精神上的惶惑不安?追根究底,張氏在此寫的就可謂是在現代中國的飢餓者頭上,徘徊不散、攪擾生者的鬼魂。我認為這裡的鬼魂至少是有三種意義並置顯現的。它最先是鄉人所畏懼的「鬼神之忌」,一種傳統的奴性民族靈魂;進而,它與地方幹部「無窮盡的剝削」以及無所不在的竊聽告密是同義的,那是共產黨的——若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指出,也是馬克思的——指令(injunctions):「大家彷彿都有點顧忌,因為有幹部在座」;再者,那是飢餓幾死的「反革命」份子的魂兮歸來,如譚大娘在拒絕協助金根夫婦後的心虛之言:「不像是風。倒像是他們倆回來了。」鬼魂的意思是:不在場者以在場者諱言禁忌的方式,得以發揮其總已可見(joujours déjà vu)的、令人不安的作用。
這個鬼魂事實上時刻被揣在張氏懷中,如《傳奇》再版序說,她感受到的正是由此而來一種「惘惘的威脅」。這或許也是王德威所指出,纏祟在近百年來中文現代小說的歷史潛意識:「一個世紀的現代經驗卻見證了歷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盡,反而以最沉痛的代價,輾轉回到我們身邊......提醒了我們潛藏其下的想像魊域,記憶暗流。」假如說一般作家所書寫的是鬼魂「除之不盡」的無奈,那麼張氏則仿佛是刻意以「左右開弓」式的禮讚與嘲諷,更動員錯置歷史正統的神話敘事鏈,拉扯其中讓鬼魂暴竄的破口,施展一種前無來者的、華麗而蒼涼的還魅手法。在《秧歌》裡,這種還魅很常表達以夢魘般的漫遊,並體現成角色攜乘並回歸於某種詭秘(uncanny)的精神徵候。比如在過年前,月香與女兒阿招悄悄塗抹紅艷異常的胭脂,在屋中隨燭影無聲走動,讓人讀來心生寒氣——若再細思,這場景其實便是作為之後在關帝廟的粉紅牆下,金根中彈、阿招死去的預知逝亡紀事,更甚遙遙指向了最終那個算是某種意義的反高潮的秧歌戲台。誠如夏志清指出,戲台意象於《秧歌》裡頻頻出現,非但殘酷地啟示了假戲真做與人生如戲的真理,老頭加入零落的年輕人隊列載歌載舞,便更可說是「百鬼日行」的上演了一場中世紀意義的死亡之舞(dance macabre),在冬日暖陽之下,難掩陰森淒涼的鬼氣。
昨天才被亂槍屠殺,翌日就要熱烈歌舞——民眾如同折子戲裡的角色,為地方幹部(或身在更高處而總是不在場的萬惡鬼魂)所操縱命運,其中所體現出強烈的身世懸浮之感,書中這樣形容:「繞著月亮跑著跳著」,我相信張氏在此使用月亮的意象絕非隨意的。像我在別文分析,魯迅筆下的狂人在月光之下看清繁縟禮教原來是「吃人」二字,那片月光其實也同樣照及了張氏的眼簾,比如《金鎖記》裡那首尾呼應的月光便仿若咒語,不斷撥擾當下,驅使著某種病態怨念的傳衍(月亮【luna】具有瘋子【lunatic】的隱意,狂人與曹七巧便作此狀)——正是以月亮為指示物,張氏得以起乩還魅,反覆招弄其完而不了的故事。如此我們便能理解,當她在描寫政治把戲之時,何故那些鬼故事式的戲台會隨處出現:此中可謂一種月光之下的噩夢志怪。進而,這種寫法其實有跡可循:當察覺到張氏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語言與意境的嫻熟運用,我們便不難聯想到,這或許正是傳統神話志怪小說裡的「幽傳統」書寫。正如茫茫黑夜裡的月光殘照——我想起蔡元豐老師曾引用馬敘倫的考據,指出「其實『幽』並非完全漆黑無光,而是漆黑中微弱的螢火......會意為『火微』」——當金根揣著龐大的恐懼與壓抑,試圖抵抗幹部「不在場的在場」的鬼魂:「就像心裡有一個飄忽的小小的火焰」,追述記憶的齒輪啟動剎那所生之火花,正是一束反抗黑暗的幽光,如蔡老師說,這許也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意義的,在絕境裡一絲啟明(illumination)的可能。
這樣我們也許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夏志清在論述《秧歌》時的話:「我們用人類的火炬去照它,共產黨畢竟是件不真實的東西,是一種邪魔鬼怪......在我們的道德想像之中,共產黨是一件怪物:它殘暴超過舞台上最血淋淋的戲,超過了我們想像中的地獄。」這亦算是直白地解釋了,為何《秧歌》會被稱為「反共小說」,而不能容於中國大陸的文學史論述了。當然,作為小說家的張氏始終是個冷諷者,並且其情緒往往是悲觀的。假如金根真的是小說中(或不存在)的那個啟明者,我們甚至會懷疑那束轉瞬即逝的幽光,是否僅是長居黑暗的幻覺——思及他的命運是為幹部槍射,冠上了「反革命」之名並被共黨追捕,下場可想而知——別告訴我這是一線生機的隱喻。如是,除了金根這個角色,黨員顧岡(或連同《赤地之戀》的劉荃)或許同樣值得我們比照發想。張氏描寫這個角色,是有別於書中其他幹部的,他有私慾,會饞食、會好色、會妒忌、會逃避,他毋寧更像個人——一個讀書人。對此張氏是毫不留情的,在這個角色身上,我們讀到的是她對知識分子(也許亦是小說家自身的化身?)的嘲弄與鄙棄,甚或呼應了魯迅的話:「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我們今天讀來,實在極有重量。當知識似乎無能於改變現實政治,我們究竟從何擺脫那黑暗權勢的惘惘脅迫,面對暴政之際,綻放出連同勇氣、智慧也永不滅的黎明光芒?百年過後,當這些鬼魂徘徊到當下香港,餘音不散的,又豈止一闋秧歌?
備註:
一、參考書目
張愛玲:《秧歌》。香港:香港皇冠出版社,1999年2月初版六刷。
二、引用論文、相關評論
王德威:<從除魅到招魂>,收《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人文,2007年10月,頁161-164。
王德威:<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收《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人文,1993年6月,頁337-341。
夏志清著、夏濟安譯:<第15章 張愛玲>,見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頁293-328。
勞緯洛:<百年還魅張愛玲:從《金鎖記》談到時代裡的愛怨懼>,載《明報》世紀版,2020年9月30日。
蔡元豐:<啟蒙中的黑暗——論李歐梵的「幽傳統」>,載王德威、季進、劉劍梅主編:《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香港:三聯書店,2020年7月第一版,頁11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