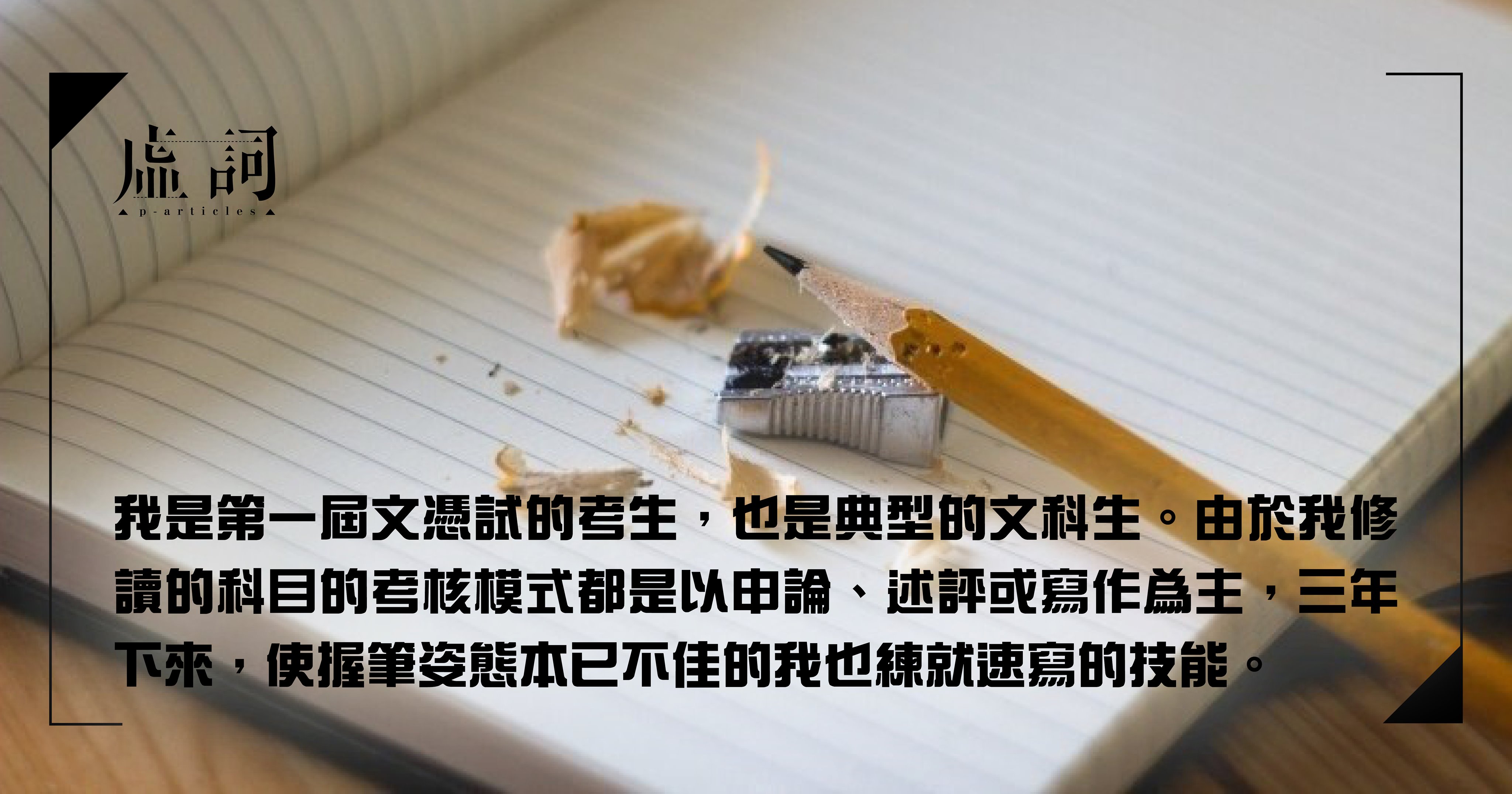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落草者言:一個「中文人」對香港中文教育的幾點反思(上)
教育侏羅紀 | by 邱嘉耀 | 2021-09-24
(題為編輯所擬)
楔子
每年的這個季節,是修讀教育文憑課程的學生最忙的時候。才稍稍適應學校的環境,赫然發現實習已到尾聲。回想在學院上課的日子不遠,繳交論文或反思報告的限期卻又將屆(案:或在下班後曳著疲乏的肉身返校,或把心一橫將紙本付與速遞公司──這是中大的傳統)。至於對瘡痍滿目的求職信字字斟酌,以及在夜半不斷刷新招職網的頁面,幾乎成為了日常。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自信心,總不免對鏡自練(憐),以熟習面試的流程(並慨嘆漸深的黑眼圈)。這興許是每年這個季節的屬性──對意欲投身教育界的新鮮人而言。我想。
以上種種,我都沒有親切的體會,而是從師友間所聽聞。我想以事實相印證,與上文大抵相去不遠。主修中學中文的我快要從這個課程畢業了。但我卻自那宣佈即將抵站的廣播聲裡躍出車廂,沒入草莽間。暫不入行是個錯誤的決定嗎?我想並不至於。然則,主宰理性的那個我不時要求我交待出理據,好說服它此行不虛。對此,我是無能為力的。然而為了這數月來的光陰似乎沒有等閑拋擲,我於是開始草擬這篇文章,以反思香港的中學中文教育。我想這應該是不錯的,由於它跟我若即若離的緣故。
中文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稱職的讀者
不妨先從中國語文科的責任說起。
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預告短片推出後, 引來我不少朋友轉載。不管反應上是惋惜或憤怒,還是感嘆與感激,他們的寥寥數語背後或轉載這行為本身,似乎都共同分享了一種共鳴感。這是一種情緒反應,它的基礎是人的同情共感的能力。我想,這與太史公讀孔子的著作而「想見其為人」,或古往今來的讀者掩卷太息、廢書而嘆,在本質上並沒有的區別,只是表達的媒介不同而已。自預告片出爐後,好評如潮,網上也出現不少分析和評論。師友談論其宗教意蘊,影評人感慨於錯綜複雜的中港關係, 導演提示片中的聲音設計, 連移居臺灣的蕭生也重作馮婦,就其間深沉的寄託一一細剖。 眾聲喧嘩,何其璀璨!這是藝術的力量。然而,文本的意義並非不證自明,必待乎讀者的參與和解讀。上述對金像獎預告短片的不同角度的賞析,就是他們各自運用其「閱讀」能力的成果。雖然中國語文科的教材仍以文字為主,我認為,使學生具備基礎的閱讀能力,乃至能夠將所讀所思所感清晰表達出來,是中文科應當肩負的責任。
溝通情意是人類應該掌握,並致力精進的基礎能力。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一點。先不論口頭上,在我的觀察,現在許多人(甚至是主修中文系的學生)卻無力以文字傳情達意。我很難不為此感到悲哀──雖然,我更不忍的是不少人誤闖中文系,茫然間四載光陰過去,甚至自此走上人生的歧途。孟子說「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上〉)閱讀能力、表達能力的建立和表現,或囿於個人性情才分,或受到客觀環境所限制,因此,這並非全由自主(註1)。儘管如此,我無意排除學生的責任,但當他們意識不到這是有意義的,甚或壓根不理解責任究為何物的時候,作為促導者的教師,其重要性於焉彰顯。
「述而不作」與「存而不論」:我在中學所接受的歷史和中文教育
按照官方課程文件,「中國語文教育」此一學習領域係由「中國語文科」、「中國文學科」和「普通話科」三個學科所組成(註2)。歷史或中國歷史科則隸屬於另一學習領域: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層面而言,歷史和文學教育縱然互不統屬(卻相關),起碼在我在中學的學習經驗中,它們的精神其實頗一致。故仍在此聊書數筆。
莊子在〈齊物論〉則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這段文字可見莊子的知識觀。具體來說,則涉及以何種態度和方法來看待或理解知識的命題。莊子主張齊物,不以區別概念為然。唐代的成玄英疏解後文「聖人議而不辯」的義理時,謂「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跡」,很值得參考。既然是非利益因時而改變,也就沒有絕對正確的知識。這既是一種超越的歷史眼光,也是一種通達的看待知識和人生的態度。知識的內容會因時而變化──在這一點上,孔子和莊子都有相近的認識(註3)。 然而,相對而言,莊子傾向反對知識的立場,孔子卻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承認有一些知識有其價值,而標準則繫於是否與古道相契。若以此為譬,我想,我在中學所接受的中文教育的經驗,就是將我看待知識的方式模塑成「述而不作」與「存而不論」的過程。
我是第一屆文憑試的考生,也是典型的文科生。由於我修讀的科目的考核模式都是以申論、述評或寫作為主,三年下來,使握筆姿態本已不佳的我也練就速寫的技能。當時,面對嶄新的考試制度,師生都無異於摸著石頭過河。也許與辦學團體有關,普遍來說,校內教師無論在行事還是教學上,個人風格都不太強烈。教授文科的老師,固非言必稱堯舜的那一種老先生,也不怎麼跟學生宣揚某些價值或抱負。他們的共通處是都不怎麼教授應試技巧。因此,我是頗為自己能掌握公開試的要求而自豪的。我隱約覺得有些技巧在不同科目都可以共用。譬如中文科要求整合資料,發表見解,略加論證的「綜合能力」卷,就頗與通識科的作答方式異曲同工。那時間,同學常苦於交出去的考卷的篇幅不甚可觀。我卻揣摩出以下的方程式:主題句、引用例證、略述各自利弊優劣。此外,不妨虛擬問答,以顯示個人思考之周延。
其實,這是一種扭曲了的「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固是孔子的謙辭,他多少還認為古道有其內在的價值。因此,他所以傳述舊聞、刪定《六經》,背後實有其原則和價值。我的應試心法不過是剪貼拼湊。論點不足時,不妨從不同層面分別討論。至於不同觀點之間的關聯,卻全然不顧。倘若論證時一旦感到捉襟見肘,就把熟記的古今名言或事例盡數拋出,這和裝腔作勢不能說有本質上的差別。以我當時的經驗,不少教師、考官是頗為受落的,甚至認為我以強記為樂。
高中的某節班主任課,中史老師從班房門外往內探頭掃視,隨即向我招手。我立時走到門口,他遞給我一本成語辭典,並以他略帶滄桑的嗓子,道:「這是給你的。知你喜歡背誦,日積月累,對學習應該很不錯。」回到座位後,我把書翻到背面,卻見標示銀碼的價錢牌仍未揭去。至今回想,又喜又悲。
我的公開試成績是不錯的。這多少與我那憑著師心領略的「法門」有關。其間,卻不是沒有經受過挫敗。中五那一年──如果記憶不差──老師讓我參加區內的歷史專題研習比賽。比賽要求評價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貢獻。不曾讀多少課外書的我,厚著臉皮把教科書上的內容略加整合,便和組員上臺報告。問答環節時,評判問我們如何回應「三民主義」難以實踐的批評。我們回答了什麼,早已渾忘(忘記也好)。那天使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鄰校學生以「造王者」為主軸,探討孫氏的功過得失。相形之下,我那報告實在蹩腳無趣極了。也不知道那時候的自己可感到赧顏?
「述而不作」可以分「教」和「學」兩個層面講。前者指教學活動側重傳授學科知識或價值觀,後者大抵可以我那囫圇吞棗般的學習法為例子。可能是性格的關係,即使對事情存疑,我卻不輕易「打爛沙盆問到篤」。回想我的中學生涯,儘管我對述而不論的教學法並不特別反感,卻造就我於初習得的知識,往往保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比如說,中文科老師見我在作文中抒發了一些負面情緒,便溫言勸勉,說文章立意以正面積極為宜。溫柔敦厚的她也許有其堅持,故不好直說這是公開考試的潛規則。那時候我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只嘆當年不曾讀到何福仁先生論文學教育的那一類訪談或報導(註4)。
如何審美,什麼知識:中文科的內部矛盾與困境
當我們問知識是什麼,以及應該怎樣看待知識的時候,就像靈魂出竅似的,以第三身的視角反思這個世界。不妨再後退多一步,談談審美和知識的關係。
我當研究生的時候,有次曾跟中文系一位年輕老師說到〈醉翁亭記〉至今仍是中文科常用的教材。他隨即嗤之以鼻。這反應的背後固然有其審美上的依據,而這美學觀念顯然與現行中學課程的取向大異其趣。然而,隱藏在香港的中文教育背後的審美觀究竟如何?在此不得不提到樊善標教授的說法:
作品編進教科書成為課文後,就給人「神聖」的幻覺,由是作品的感情簡化了,遠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作者也變成了異於我們的「超人」(註5)。
他在另文的觀點,又與上引文字互參:
不過作品一旦成為範文,並且抽離了原來的脈絡來講解,它的價值觀就會變得單純而狹隘,一方面佐證了世上有一套古今不變的價值體系,賢愚善否判然有別──這當然只是幻象;另一方面則把寫作活動神聖化了,似乎只有某些認可的情感才能寫進作品裡,為日常生活的瑣屑感受必須嚴格淘洗(註6)。
換句話說,教科書中的名篇往往以一種去脈絡化的方式講授。與此相配合的,還有被有意無意忽略不顧的細節,對文章關目一切從簡甚至視若無睹的注釋,以及以斷章取義的手段,將文章剪裁成主題突出、價值單一如同嶄新作品的編輯。於是,在教科書的引導下,朱自清〈背影〉中的父子之情顯得無比純粹,李白成了浪跡天涯的浪蕩子,杜甫堪比一飯三吐哺的周公……此外例子尚多,似乎毋須一一枚舉──至於陶淵明、西西的面目如何,讀者自可在互聯網上檢索樊教授的文章,或許會為你帶來揭秘的快感(或由於感到作家面目一新或模糊而帶來的失落感)。
我在中學時的閱讀量不多,尤其令我煩惱的是撰寫閱讀報告。老師所推薦的《金鎖記》或《尹縣長》都是與我隔閡的文字,因此我在許多時候只是總結一下故事情節,敷衍塞責,將述而不作的精神發揮到底。那時候,我喜歡讀的是金庸、衛斯理的小說,季羨林、梁實秋、林語堂、余光中的散文,偶爾拈起亦舒或天航的言情作品,竟也心有戚戚起來。文學科有選修單元,閑淑貞靜的老師教授蘇軾的詩文詞,我也喜歡起來。現在回顧我中學時的閱讀趣味,以詩文為主,其中又以散文最得我心(我至今仍缺乏耐性閱讀長篇小說)。美文與雜文,分別滿足我對語言和知識的追求。繁褥與淡雅,則是那些作品常見的審美特徵。在這個背景下,我怎能感受到《藥》中魯迅所寄託的深沉悲哀?如何能夠體會到竇娥捨生取義的壯舉背後的情操,以及瀰漫全劇的崇高感?即便如此,我還是與真、善、美的文學觀不太靠近。「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蘇軾〈超然臺記〉的這幾句話彷彿支持了我的想法和興趣。故此,我既為東坡「十年生死兩茫茫」的夫妻情誼所感動,也深陷於「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孤獨情味,趑趄而不前。
古往今來可觀的中文多的是,儘管如此,我並不主張──現實也不可能──盡把它們納入基礎教育的課程。落草者如我自不能拋出可行的方案,故必須借鑒專家。教育學者李子建、黃顯華以下一番話,頗發人深省:
課程內容的選擇始終離不開「價值」的取捨,即究竟從浩如煙海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化傳統作出「理性」的選擇,抑或依據學習者需要、能力和興趣作出選擇,抑或按照設想的學科結構、或知識的形式作出適當安排,抑或考慮社會的需要和發展加以配合,抑或把上述各種方式加以均衡地處理,仍使課程設計者費煞思量(註7)。
此論中肯。李、黃二氏將「知識」和「文化傳統」加以區分,應該只是為了便於行文而已。
(當文科生遇上中文科教育,又正走在中文教育的路上,作者抒懷之餘,並分析當前中文教育的困境,下篇全文連結:https://bit.ly/2LEBJ0I)
參考:
1. 有關孟子的義命觀及其倫理學意義,陳特先生有相當扼要簡明的析論,可參考。陳特:〈孟子〉,《倫理學釋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277-302。
2.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年。
3. 比如孔子就認為不必拘泥於「禮」的形式和內容,而應該秉承其背後的精神。見《論語.八佾》:「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陽貨〉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4. 〈何福仁訪談(上):文學不做救世主〉、〈何福仁訪談(下):應該要有「失敗者的文學」〉,《虛詞》,2018年12月7日、 2018年11月27日。
5. 樊善標:〈合上文學教科書之後──在大學中文系重遇中學課文〉,《中國語文通訊》第68期 (2003年12月),頁27。
6. 樊善標:〈殘留記體和後來看法──重讀中學課程裡的新詩範文〉,轉引自氏著〈合上文學教科書之後──在大學中文系重遇中學課文〉,同上注,頁30。
7. 李子建、黃顯華:《課程:範式、取向和設計(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62。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