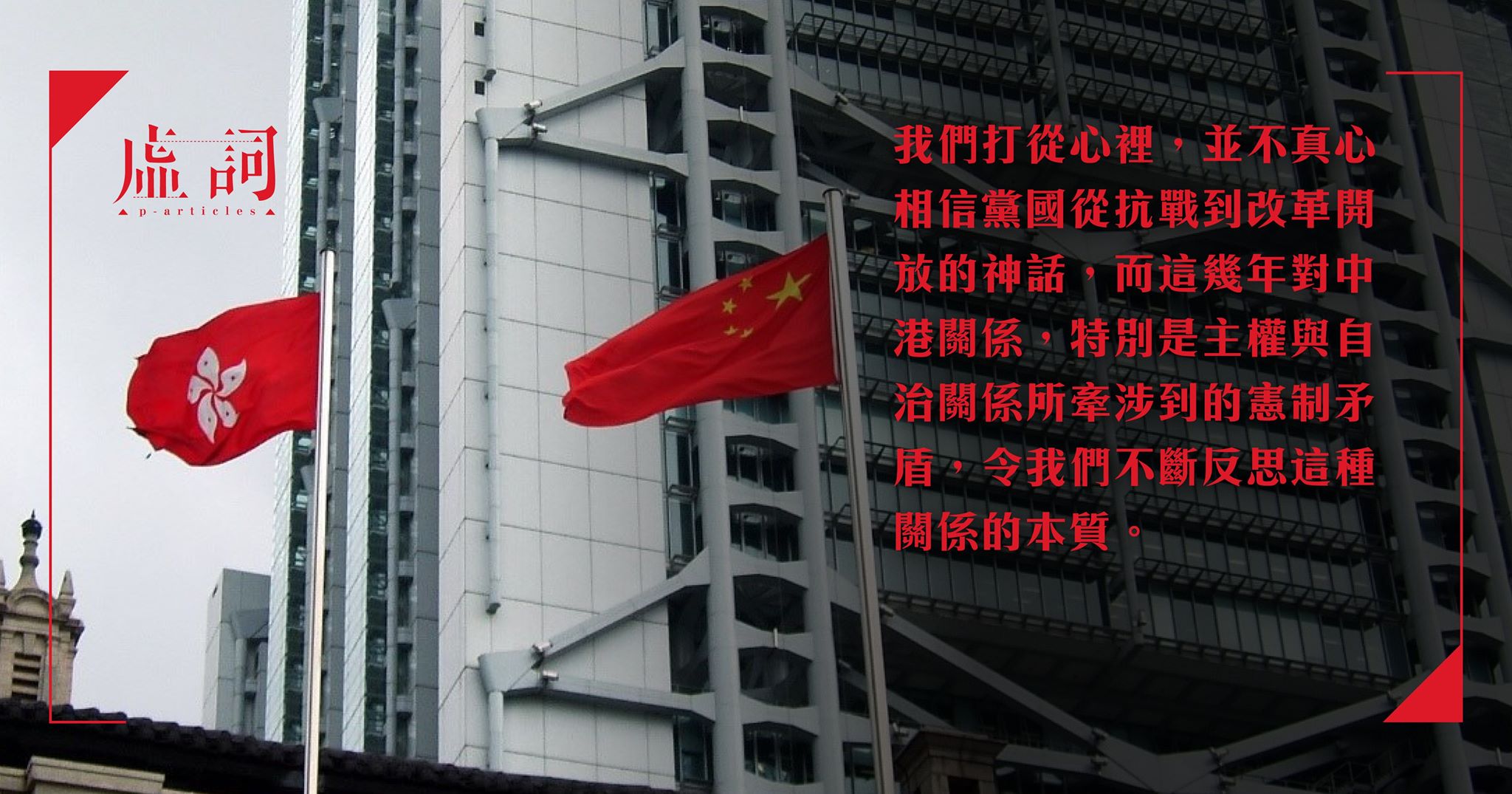王權與主權
一、主權一思考,人民就發抖
回歸以後,香港一直陷入中港憲政關係的爭論中,深遠地影響了政府施政,亦順帶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共主權意志與香港本身作為國際城市的本質有所衝突,也關係到香港人對中共主權的認受性一直有所質疑,尤其是當今習近平在位,有欲振中央朝綱之勢,但觀其所作所為,如銅鑼灣書店事件等,反倒更難以強制港人向心。近日特首強推的《逃犯條例》,姑勿論是特首抑或中央的主意,反而激起了香港社會的反抗意志。
說來主權這回事,就好似古代的王權,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也不過是公民選一個代表,當幾年國王,再看看他的政績,讓不讓他連任,由世襲制變成選舉制,統治合法性的工具由血緣和法統變成了選舉結果,變來變去,有些反對西方民主的國家還是回到終身制和世襲制的老路,外加思想拑制和洗腦工作,也不過是為了統治長久一點而已,但與當初那些「受命於天」的宣告或者「利國利民」的承諾,已經越來越遠。然而那些被臣民所歌頌的國家領導人,不過是每日在密室中憚精竭慮謀利並消滅反對聲音的獨夫而已,近來讀到飲江的近作,不禁莞爾﹕
馬克思一思索
馬克白夫人就發笑
馬克白就苦笑
皇帝被謀殺
但唔輪到佢
輪到佢
但夫人唔再忠於佢
夫人鍾意馬克思多過鍾意佢
有可能先於皇帝
馬克白被謀殺
這要看莎士比亞如何構想
如何安排
如何發揮
他
的
想像
馬克思一思索
馬克白夫人就發笑
她深知歷史的正劇
歷史的悲劇
以至鬧劇
而這是莎士比亞四百年後墓穴探出頭來
才發覺的
才驚覺的
我的頭呢
莎士比亞摸一摸自己的頭
馬克白夫人
就發笑
不,莎士比亞夫人就發笑
或者,兩位夫人
相視而發笑
噯,還要走來一人呢
馬克思夫人?
AlphaGo夫人?
特朗普夫人?
我的頭呢
掛在很遠很遠的樹上
飛翔在很近很近的雲端
你的 我的
頭呢
布幕打開
城堡外
三個夫人在發笑
人民,只有人民
及其夫人
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但,烏托 美好 公義
(下刪365字)
毋有陰謀預言詭計
的家園
和家國
還很遙遠
還很遙遠……
莎士比亞唸過了台詞
捧回自己的頭
回返墓穴去了
退票
有女性主義者高聲嚷著叫
退票
有不是女性主義者
和 平權主義者
也大聲嚷著叫
退票
而 當所有台上台下
與乎遠方網上觀眾
群組看客疑歐派
留歐派
嚷著叫
退票
莎士比亞
就發笑
再次從墓穴走出
他摸一摸自己的頭
和劇場上那些
3D打印的頭
遙想已然消逝
又終將消逝
的靈魂
沒事沒事
他說
莎士比亞
就是四百年前
幽州台上
與湯顯祖
齊名
那個
沒事
沒事
的莎士比亞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
而發笑
而涕下
而發笑
而謝幕
而發笑
(莎士比亞湯顯祖特朗普暨一眾夫人400週年紀念)
在莎劇中,馬克白是弒君者;在俄國革命中,布爾什維克也是弒君者(列寧下命令槍殺沙皇一家),而中共則是透過內戰和在精神和肉體上消滅反對者來獲得統治的。他們都無法拿到有合法性的主權(legitimate sovereignty),因此作為沒有合法性主權的君主(sovereign),他們充其量只能算是僭主(tyrants)。而這些弒君者的政治理念甚至不是自己想出來的,而是馬克白夫人和馬克思想出來的,因此馬克白一思考,馬克白夫人就發笑;列寧、史太林、毛澤東等現代僭主一思考,馬克思就發笑。
當然,就如詩中第一句說的,馬克思在思考他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心思簡單但行動貼地的人民,也會發笑。然而當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化作史太林式的政治措施時,人民的反應不再是笑,而是恐慌、逃亡,或絕望地反抗。
這都說明了為何霍布斯邦說的那個「極端的年代」,總是充滿了形形色色的災難,甚至比中世紀更嚴重,因為以往王權總是遇上教會或貴族的阻擋,無法把鋼刀架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教會相信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受俗世法律管轄的對象,而現代僭主只認定所有人民都被他的法律主宰其生死。然而僭主不是上帝,他也會病死,或死於其團伙的權力鬥爭裡,故此現代僭主的統治合法性,反而是籠罩了多重陰謀的迷霧,變得更神秘莫測,也更充滿不穩定性,與他們所稱頌的科學和理性,更有天壤之別。
二、主權的誕生
主權源於王權。現代西方世界的主權概念,源於中世紀的王權。在中世紀那些國王所管轄的「領土」裡,王權和教會權往往互相重疊,雙方鬥爭不已,審視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我們就發現,王權與教會權的鬥爭,如亨利四世在位時的「敍任權(investiture)之爭」,如何影響了整個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區的發展。到了後來,在某國家,國王最終將自己地區的教會置於教會系統以外,從而實現了王權,如英國﹔但更多國家是由國王自命為教會的守護者,從而擴張了王權,如法國、西班牙,甚至奧地利。
在文牘和刀劍之間,主權一直都是一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概念,直到十六世紀法學家尚‧博丹定義「主權」(souveraineté)開始,它才在文字上存在。博丹的定義,無寧是為主權賦予一種神學般的意義,他說﹕「主權是一個公民國家(république,指法蘭西王國,因為它體現法蘭西人民意志)的絕對及永久權力。」"La souveraineté est la puissance absolue et perpétuelle d'une République." 由於它是絕對的,所以不可分割,由於它是永久的,所以不會有時間限制。這種主權所指的,當然也是王權,因為國王代表了人民。而日後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裡,主權除了是人民公意(general will)的體現外,還只受限於人民公意彰顯的某些時刻,一旦這個「公意」時刻過去了,主權就暫時隱退。二十世紀法學家卡爾‧施米特甚至在《政治神學》裡說﹕「主權者決斷例外狀態。」”Souverän ist wer über den Ausnahmezustand entscheidet.”反過來說,主權者(可以是君主、獨裁者、寡頭,或人民,總之是握有主權之人)的存在,是要由「例外狀態」來反證的。究竟「例外狀態」有何意義呢﹖施米特的說法就是按「緊急狀態」(即上面說的「例外狀態」)懸置一般法律及憲法,就像電影《寒戰》的那句對白﹕「在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然而這想法並不新穎,因為博丹也說過,主權是可以懸置公法(civil law)的。
我無意梳理一位二十世紀德國法學家與十六世紀法國法學家的傳承關係,不過兩者對於主權的討論倒是很有趣。博丹和施米特都認為主權者可懸置法律,但博丹認為他擁有絕對權力,很有「君權神授說」中的無遠弗屆的意味。而施米特只是提及到「例外狀態」,也指出主權是一種「邊界的概念」(borderline concept),性質上就有很大分別。相對於盧梭的意志說,施米特採取了一種決斷論的說法。意思是,只要主權者認為是「例外狀態」,就可以「決斷」(überentscheiden)是「例外狀態」。但「決斷」並非英語的「決定」(decide),英譯本將其勉強譯成decide over,也許意味著,除了意味著主權者能決定哪些時刻是「例外狀態」外,還有權力決定在這種狀態中應該做哪些相關的事情,例如頒佈甚麼法律,實行甚麼措施。盧梭的主權是以議會的立法意志凌駕行政決策,施米特的主權反倒是被「例外狀態」召喚出來凌駕行政、立法的主權者決斷了。
三、國王永不會死
相比之下,中世紀以王權為面孔的主權,是否更整全、更有威力呢﹖也許我們應該說,古代王權是一種切切實實的象徵,因而人民對那個「他」也更有直接的感覺。首先,現代主權都被裝扮成一個大而化之的概念,它包括領土、全體人民、境內所有國民、民族,其承傳之文化、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系統在內的政府機關,這些大而化之的概念都在掩遮一個事實﹕當主權執行實質政策或措施時,實際上都是國家元首與他的幕僚在討論、簽署法案、頒佈法例,無論是川普與他的白宮精英,抑或習近平與政治局常委或者他的派系菁英,都一樣。可是在麥克白殺死鄧肯王之後,貴族和人民一向視鄧肯王為他們的主權代表,而國王可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一個人。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在《牲人》(Homo Sacer)中亦引用了中世紀史家康托洛維茨(Ernest H. Kantorowicz)的《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指出西方中世紀以來對於王權就有一種獨特的概念,認為國王有兩個肉身,一個是主權的肉身(Sovereign Body),一個是神聖的肉身(Sacred Body)。
這部奇特的歷史著作採用了離經叛道的筆法,書中從伊莉沙白一世時期英國法學家普勞登判例報告(Plowden's Reports)說起,除徵引中世紀教會訂立的君主儀式和關於基督的身體比喻外,還解讀莎劇《理查二世》和但丁《神曲》的相關文字,汪洋恣肆得不成系統。關鍵概念來自普勞頓對於英國國王的定義,他說國王擁有兩個肉身,一個是自然的肉身(Body Natural),一個是政治的肉身(Body Politic),自然的肉身很好理解,因為無論他是英國國王,抑或川普習近平,都一樣會死,死後肉身會朽壞。而政治的肉身就關乎人民對國王的神秘信仰,其意義在於﹕即使國王的自然肉身會朽壞,他的政治肉身也會永恒不朽。簡單來說,這也是一個隱喻,比喻他治下的國家、民族,但中世紀的人相信這些隱喻有切切實實的力量,正如他們相信聖餐就是耶穌的血肉一樣,即使國王駕崩,人們會為他製造蠟像(wax effigy),作為他仍然活著的表徵。
康托洛維茨進而指出這兩個肉身其實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中世紀法國人為駕崩國王製作蠟像時,其實是相信國王仍然在另一種方式活著。阿甘本認為康托洛維茲的「兩個肉身說」,是關乎主權的暗黑神祕一面﹕即博丹討論主權時說的絕對權力(puissance absolue),而法國人這種儀式其實有一個更古老的源頭,就是羅馬人在皇帝臨終時會為他製作蠟像,這個蠟像就像垂死的皇帝般躺在病榻上,元老院議員和護士長各站在這個蠟像的兩邊,醫生假裝為蠟像把脈並為「皇帝」提供治療建議,這項儀式重覆七天後,他們才正式宣佈「蠟像」死亡。與羅馬人不同的是,中世紀法國人相信國王是不死的。阿甘本說,古羅馬人必須官方宣告將皇帝肉身「奉獻」(consecratio)給「死亡」,然後該皇帝才可以進入公墓並被供奉成神像(colossus),即「被奉為神」(apothesis)。
四、王權與宗教的結合
所謂「政治的肉身」,其實是將國王的肉身神聖化,以達成將國王神化,變為神人的目的。中世紀法國源於法蘭克人建立的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其統治者明白到,必須將王權與教會權力結合,建立國王領導封建貴族的合法性政權,所以接受了羅馬正統教會的信仰。在林美香主編的文集《百合與玫瑰﹕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法王權的發展》第一章〈王權神聖化﹕法蘭克國王的祝聖典禮〉的作者陳秀鳳指出,他們讀出舊約聖經中摩西為兄長亞倫祝聖(塗抹膏油在後者頭上),以及撒母耳為掃羅和大衛祝聖的意義,那表示被祝聖者是上帝認可的世俗統治者。
相對於這種類比,中世紀甚至有論者認為國王就好比基督,因為根據新約福音書,基督坐在上帝的寶座旁,受命掌管世界。《百合與玫瑰》作者之一的陳秀鳳,也提到在中世紀早期統治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國,甚至提出將世俗統治者喻為基督。康托洛維茨在書中提及十一、十二世紀一位精通神學經典、宗教儀式及教會法的諾曼人無名氏(Norman Anonymous),他認為國王是宗教和教會融合的混合人格(persona mixta),這位無名氏從舊約受膏為王者和新約福音書關於基督的記載為理據,支持國王等同基督的論點。
墨洛溫王朝後來被丕平家族篡位,其後裔查理大帝建立了一統法、德兩地的加洛林王朝,但他死後又分裂為法、德等國。但加洛林王朝諸帝沿用宗教名號,自稱上帝代理人(Vicarius Deu)﹔爾後統治德國的神聖羅馬皇帝,都自稱為基督代理人(Vicarius Christi)。這種名號變相等於聲稱自己在世上履行基督職責,不管臣屬、領主抑或教會人員都可以任免,挑起了教會和皇帝就「敍任權」的鬥爭,直至後來亨利四世在位時,這場鬥爭終於以皇帝失敗告終,以後只有教宗才可以自稱為「基督代理人」。
喜愛莎士比亞的康托洛維茨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史劇《理查二世》(而不是悲劇《馬克白》),展現莎士比亞時英國對「國王的兩個肉身」的概念。在英國歷史上,理查二世本是政體之首,但因暴虐而被波林布洛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推翻,後者弒殺理查並登基成為英王亨利四世。在莎翁筆下,這位下場悲慘的國王無論呼吸、嘴巴,都被描寫成不同凡品,是上帝挑選的異數。在第三幕第二場裡,理查二世率軍攻打亨利的領地愛爾蘭,他親吻了土地,大臣卡萊爾說﹕「陛下;那使您成為國王的神明的力量,將會替您掃除一切障礙,維持您的王位。」理查王說﹕「每一個在波林布洛克的威壓之下,向我的黃金的寶冠舉起利刃來的兵士,上帝為了他的理查的緣故,會派遣一個光榮的天使把他擊退;當天使們參加作戰的時候,弱小的凡人必歸於失敗,因為上天是永遠保衛正義的。」理查二世很明顯亦很理所當然地自視為天眷。在後面第四幕中,波林布洛克審問理查二世,康托洛維茨認為,莎士比亞把這情景寫得好像彼拉多審問耶穌一樣。
五、光環
也許當今我們對於古代以基督教或儒家闡釋「受命於天」以統治百姓的說法嗤之以鼻,可是我們如何看待中共政權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的統治合法性呢﹖相對於中華民國的合法性理據,即推翻滿清並接受清帝遜位的憲政基礎,中共無疑只能訴諸武功,如聲稱自己領導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人,趕走「半封建,半殖民」的蔣介石政權。然而如果我們都相信統治必須源於某種類似「上帝」或「天意」的超自然意願,那麼世俗一切行政權力背後,都必須率先獲得這種宗教上的肯定。阿甘本寫了《牲人》以後,還寫了《王國與榮耀》,將世俗國王和政府的關係,與上帝和天國的關係作為類比,思考古代政府(主要指羅馬、拜占庭)為何更重視各種繁文縟節、儀仗、歡呼形式。
其實阿甘本早在《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的最後一章,就嘗試以羅馬法考掘權力(potestas)及權威(auctoritas)的分別,而在《王國與榮耀》,他進一步談及了權力背後的榮耀(gloria)。簡單來說,權力總是法定的、有形的,因為權力的界定,在職位者才得以運用其權力,但這只是表面。權力的背後還需要獲得認受性,這涉及到權威的根源﹔而榮耀,似乎更需要透過觀察繁複的宗教儀式(liturgy)和民眾歡呼(acclamations)才能發現出來。阿甘法和康托洛維茲都有提到,中世紀法律都清楚訂明各種宗教儀式的細節。同樣地,無論是中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抑或今日中國蘇維埃政體,都有規定繁複的儀式和民眾歡呼的形式,甚至視為政治問題。為何我們的主權總是需要榮耀呢﹖阿甘本從聖經保羅書信對人民(laos)一辭的運用中看出,只有儀式才能讓群眾(ochlos,或譯愚群、暴民)變成「政治化」的人民(laos),君主也必須透過這些儀式和歡呼而被高舉起來。對於今日中國大陸的主權來說,香港人是否「愛國」,會否接受包括升旗禮等儀式在內的國民教育,是否以身為中國人為傲,其實都關乎「榮耀」,卻是核心的政治問題。假使我們拒絕接受這些儀式及歡呼式及背後的榮耀,主權者就無法把我們納入「政治性」的人民範疇,也無法透過「我們」對他的歡呼,確認對我們的主權。
如果權威是滋養權力的土壤,那麼榮耀就好比是權力的光環,這種光環並非純然宗教性質的,因為無論對康托洛維茲抑或對阿甘本而言,任何世俗政治本質上已滲滿了宗教色彩,這也是任何政體必須有的特質,否則就無法凝聚被統治者,或它的「群眾」,將其組織成這個政體的人民,為了這個主權去捐軀,去犧牲小我。而榮耀也能產生一種近乎宗教(這裡宗教亦可適用於崇拜國家的無神論政權)的氛圍,讓人民產生向心力。
六、但丁的回應
在十一、十二世紀,法學家重新對羅馬法感興趣,哲學家受阿奎那影響,重提阿里士多德著作《政治學》中的政體分類。國王重新定義自己的權力形式。陳秀鳳在《百合與玫瑰》中的第二章〈王權世俗化﹕中世紀晚期法學思想與法蘭西王權〉,指出那個時代的法國統治者,開始將「國王」(rex)及「王國」(regnum)轉變成「君主」(monarcha)及「君主制」(monarchia),陳秀鳳指出,國王權力仍受地位更高的皇帝影響,而君主則無此意義上的羈絆﹔另一方面,阿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裡也指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體。這時候出現了一部名為《格拉西安教諭》(Decretium Gratiani)的法學著作,以羅馬法重新詮釋王權,捍衛中央集權,定義君權、王權及法律範疇。這些趨勢,方令神人般的王權統治慢慢轉變到如同「依法治國」的中央王權制度。
雖然西歐的君主漸漸脫下神權的面紗,披上法律和哲學的外衣,但國王還是要成為一種符號。康托洛維茨指出英國十二世紀哲學家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在著作《論政府原理》(Policraticus)裡面,認為國王有一種「象徵公正的形象」(rex imago aequitatis),例如他有「公平的形象」、「正義的形象」等,他心目中的君主是一種公共人物中的典範形象,雖不受法律約束,但卻是法律和公平的僕人。當然,君主重視法律,其目的不過是用來貶抑教會權力。雖然《國王的兩個身體》探討對基督的論述如何塑造英國日後憲政王權,但康托洛維茨仍不忘他的另一部著作《腓特烈二世﹕世界的驚奇》(Frederick the Second: Wonder of the World 1194-1250),還是要在《國王的兩個身體》中提一下腓特烈二世。這位英主被喻為「世界的驚奇」(Stupor Mundi),自幼失祜,既要繼承父親的神聖羅馬皇帝之位,又繼承母系西西里王室的土地。他精通希臘、拉丁、阿拉伯等語,熟讀古典哲學,但從小就在首都巴勒莫街頭與市井之徒打滾,深深認識到「以法治國」的需要,即使格雷哥里九世等教宗三令五申要他組織十字軍,也一次次被他推搪了。
就像當時的哲學家一樣,腓特烈二世也發現,法律是一種絕對的理性,也可以伸張他的王權,而對羅馬法的興趣,甚至令他重拾羅馬皇帝尊號imperator,表現他不是單純一個統治西西里或德國人的國王,而是權力無遠弗屆的「大帝」。他在拿坡里創建了歐洲最早的大學,並建立了考核制度以選賢任能,打破神職人員和貴族壟斷的局面。腓特烈二世還宣告﹕「必須同時是正義的父與子,她(正義是陰性名詞)的主人和儀人。」這句話不啻宣告主權君主既不受法律約束,又必須受法律約束。
但是,「以法治國」的腓特烈二世也不是康托洛維茨心中的理想典範。《國王的兩個身體》最後一章是關於但丁對君主制度的思想,這看來與「中世紀政治神學」這個論題不太貼合,然而康托洛維茨卻認為但丁的思想正好代表著一種「以人道為中心的王權」,與過去「以神為中心的王權」與及「以法律為中心的王權」截然不同。
說起但丁,我們只知道他是詩人,是《神曲》的作者,而不知道他其實是一位政治哲學家,他的另一部著作《論君主制》(De Monarchia)就提倡君主應以普世正義的統治取代神權的統治。《神曲》的《地獄篇》和《煉獄篇》充斥不少對當時政治及教會領袖的嘲諷,包括他極之痛恨的教宗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這位教宗來自意大利阿納尼(Anagni)的名門望族,一位西班牙外交官形容他只關心「長命百歲、榮華富貴和家底雄厚」,他迫害受民眾愛戴的上任教宗塞勒斯廷五世(Celestine V),訂立法律規定任何國王不得向神職人員興稅,後來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入侵羅馬,他被法軍俘虜,受辱而死。但丁在《煉獄篇》第20首提及耶穌釘十字架時也引用了這個教宗的例子﹕
我看見百合花進入阿納尼,
祂的基督代理人變成俘虜,
我再一次看見祂被嘲笑,我看見
醋和膽汁都被更換了,我看見
祂在兩個活著的強盜中間被刺穿。
耶穌和兩個強盜一起釘十字架,按聖經上的記載,在瀕死一刻,他極度口渴,所以羅馬士兵才把醮滿醋和膽汁的海棉遞到他嘴邊,然後他就斷氣,羅馬士兵見狀,立即用矛刺進他的肋骨來檢查,耶穌體內的血水立即湧出來,在這幾行裡,但丁對耶穌的態度很難講得上是同情。另外,百合花是法國王室的標誌,基督代理人自然是教宗博尼法斯。康托洛維茨認為這不是單純的嘲諷,因為在《神曲》裡面,所有皇帝和教宗都下了地獄和煉獄,天堂裡沒有他們的位置。這對剛才提到的那些國王來說,不是很盡興嗎﹖
在但丁的時代,意大利各城邦在政治上受德國的神聖羅馬皇帝管轄,在宗教上受羅馬天主教的教宗管轄,教宗與皇帝之間經常鬥得你死我活,連意大利各城邦和各顯貴家族都分為親皇帝派和親教宗派。另外,法國國王也經常派軍隊來蹂躪教宗所在地羅馬及意大利其他地方,發動無窮無盡的戰爭。對於像但丁般熟讀阿里士多德的人來說,他又怎會不聯想到阿里士多德說的「最理想的人」(optimus homo),來設想一個真正具合法性的君主應該是怎麼樣的人呢﹖
故此康托洛維茨認為,但丁為「國王的兩個身體」提供了一個人道主義的答案﹕教宗和皇帝和你我一樣,也不過是人,在上帝面前,他們必須盡教宗制(papatus)和帝制(imperiatus)的職責,但既然他們都只是人,就必須成為一個最理想的人。阿甘本撰寫《例外狀態》時,正好是「九一一事件」過後,美國這個世界帝國正以反恐為名,發動瘋狂的「全球內戰」(global civil war,阿甘本語)。書中以談論施米特「政治神學」展開,但阿甘本沒有忘記但丁在《論君主制》裡面想像的一種世界主權,那種主權的合法性基礎來自實現普世和平、正義、自由及和諧、不分信仰的全人類社會,而非神聖的宗教氛圍,或法理的基礎。這說來有點烏托邦的意味。在《例外狀態》的另一處,阿甘本還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也許有一天,人類將會把法律當作無用的玩具那樣把玩,不是為了維持它們的正統用途(canonical use),而是為了永遠把它們從那種用途中解放出來。」
無論是作為自願流亡或被拋來拋去的難民,香港人從來都是無國家、無主權的世界公民。我們打從心裡,並不真心相信黨國從抗戰到改革開放的神話,而這幾年對中港關係,特別是主權與自治關係所牽涉到的憲制矛盾,令我們不斷反思這種關係的本質。我們信任普通法,相信基本法能處理普通法與中國大陸法之間的矛盾,但中國在處理憲法結構問題時,屢次以主權者凌駕法律的作風,說明廿二年回歸的法治假定只是同床異夢。我們不想對這個主權發笑,更不想發抖,我們只想要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社會,不用把國家首腦奉為神,也不需要國家元首頒布所謂的「法律」來治國,而是依照人人平等及正義的原則治國。
參考書目﹕
Giorgio Agamben and Daniel Heller-Roaz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Giorgio Agamben. “Kingdom and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Princeton: 1997)
Ernst H. Kantorowicz: “Frederick the Second: Wonder of the World 1194-1250” (Head of Zeus Ltd.: 2019)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林美香 主編﹕百合與玫塊﹕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法王權的發展 (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