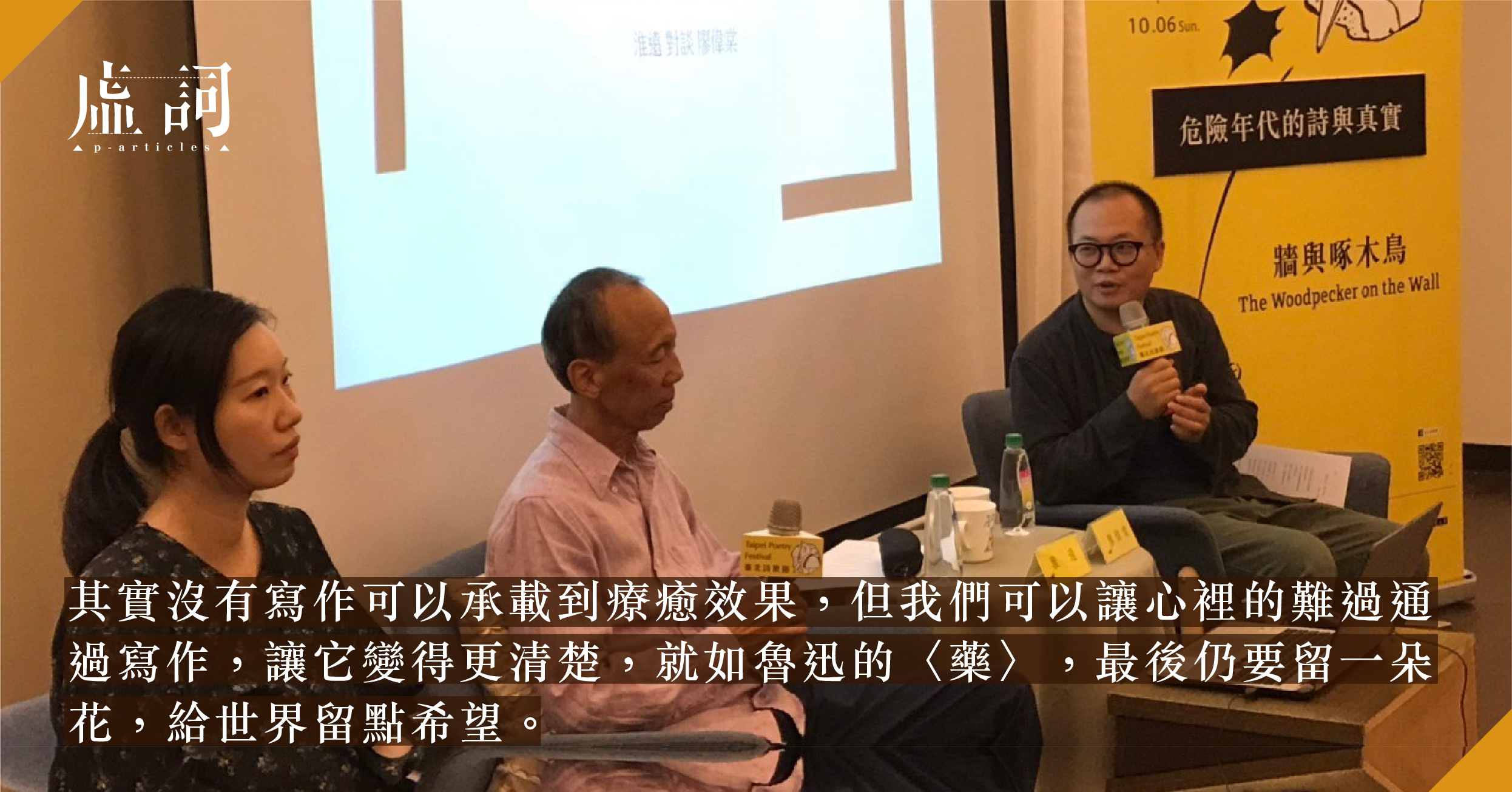詩、軍錶與警棍——淮遠在臺北詩歌節
懶鬼終於出門,今次從香港走到臺北,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的夜晚,淮遠沒有戴帽。又一年臺北詩歌節,今年主題是《詩與啄木鳥》,官方文案寫「詩是探照燈,能照見幽微與貧瘠,詩人正是辛勤而執拗的啄木鳥,堅持鑿進深處,鑿出光來。」說淮遠辛勤也許有點不符我們對他的想像,但執拗是必然的。講座名為「危險年代的詩與真實」,由移居台灣的廖偉棠與淮遠對談,也由移居台灣的陸穎魚當淮遠的國語口譯。
三位香港詩人在臺北詩歌節,話題自然離不開香港政局。全晚的對談可以由三段動蕩時期串起:8964、70年代、2019。淮遠作為時代的見證人,在這三段時期都寫出異於主流的詩歌。這次臺北詩歌節,廖偉棠幾乎以一種熱情如推銷的語氣向臺灣讀者介紹淮遠,「是他那個年代最好的詩人,也是我最喜歡的香港詩人之一。」從70年代開始寫作,淮遠從早期的詩歌創作轉到散文,後來又繼續寫詩,他的詩集《跳虱》更是收藏家與愛書人的夢幻逸品。
初版《跳虱》只印了200本,淮遠向台灣讀者介紹道,那時他在編輯部工作,公器私用拿資源印自己的詩,成了詩歌愛好者之間秘密流通的絕版之作。詩集封面是晾在欄杆上的兩隻襪子(我想一定很臭),事源淮遠是個收藏癖,那時熱愛收集襪子,就胡亂拍了張照片當詩集封面。話口未完,台下居然出現了讀者拿出這本絕版作品衝到臺上與淮遠合照。假如就像廖偉棠所說,淮遠是他年代最好的詩人,那這個年代實在遠遠還未結束,甚至可以說,只要淮遠繼續寫詩,他的高峰就不會過去。而且誰想到在臺灣會看到超級粉絲呢。
從八九六四的一隻手錶開始
廖偉棠從淮遠的詩作〈手錶〉展開這次對談,詩作寫的是8964,廖認為這是眾多寫六四事件的詩作中最好的一首:
那年夏天,一名解放軍把平亂紀念手錶賣給一位看護長。看護長把它賣給香港來的表弟。表弟隨即在王府井某酒店,被電鬍刀的刀片,削掉了指頭上一片肉,流了一些血。血和肉說再見的喊聲,嚇壞了醫務員。醫務員向一名解放軍報告:那人血肉道別的聲音,跟那些學生一樣。
廖偉棠指出,這首詩展出了香港政治詩別於台灣的特別風貌——日常化。他指一般而言,小說比起詩歌與散文更能承載虛構的力量,但這首詩插入了短篇小說的寫作手法,敘事性強烈,同時又在後段加入超現實的維度。這是小說難以達到的高度,敘事的迴路又如迷宮。血肉的意象又彷彿指涉了80年代末,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血肉相連、血濃於水的共同體想像,忽然一削,就完全切割開了。
「其實在寫這首之前,我有三十年沒寫詩了,我都在寫散文。是因為64詩輯約稿我才寫的。」淮遠說道,「我有20多年都在收藏手錶,尤其喜歡收集軍錶,詩裡面的軍錶是那時我去北京向我的表哥拿的。」換言之,詩中敘事是真實事件,平亂紀念手錶是89年北京當局發給解放軍的紀念品,用一隻手念來換取血腥鎮壓也許過於不道德,導致淮遠認為他在王府大酒店被電鬍刀割掉手指肉是命定的懲罰。〈手錶〉就在如此背景下誕生。
七十年代自由的跳虱
談及為何在詩歌當中習慣用敘事手法,淮遠坦承自己不甚喜歡抒情詩。他從小讀得太多抒情詩與抒情散文,但卻獨愛敘事古詩,比如〈長恨歌〉與〈兵車行〉等,他認為抒情作品已經太多了,而且太難寫好。至於自己的美學傾向,他認為是個人性格所致:「我為人瑣碎,後來不寫詩而寫散文更是因為散文可以承載的瑣碎可以更多,更能突顯出我的性格。」
就在這種美學思路下,淮遠專攻短詩,尤喜可以在瞬間完成的短詩,是一個剎那,一個念頭裡就能寫好的詩。廖偉棠向台灣讀者介紹淮遠的〈跳虱〉一詩,並笑言這是自己在教詩歌寫作課時,是放在最後一周才教的文本。「常言詩無達詁,但這首詩又有甚麼詁呢?有些詩歌是無解的,但無解有時可以代表詩人已經到了最高境界。」
〈跳虱〉
我看見一群跳虱攀附著風
風說我不想帶著塵埃旅行。
風說得對
事實上跳虱和塵埃一樣
但牠們說:
我們想你吹掉
我們身上的塵埃。
在70年代,吳仲賢在培正中學附近的文青咖啡廳截住蹺課的淮遠,把17歲的他邀進《70年代雙周刊》,淮遠稱那時的自己「又唔做野,又唔讀書」,是個標準憤青,純粹找點事情來做過過日子。那時的他已有收藏怪癖,家裡養了二十隻以上的貓,後來就是貓身上的虱觸發了他寫出〈跳虱〉一詩。
70年代是段遙遠而美好的日子,淮遠記述,那時即使雙周刊也會因為宣傳無政府主義而被皇家香港警察沒收一大部份,但大家頂多只是捱幾下警棍,李國威還是可以寫關於警棍的詩,癌石可以在詩裡閹割警察,地下異見詩歌依然自由出版。就連如今成為香港詩歌史上的重要作品,邱剛健的〈鎗斃〉與〈靜立一分鐘〉,也由淮遠主編的文學版下發表。不過在如今警察所控制的香港,可能難以實現了。
二零一九年的寫作還可以療癒內心嗎?
談及在警棍陰影下的香港,淮遠問廖偉棠:你現在寫政治詩,寫完後可以解決心裡的沉重感嗎?淮遠坦言,有時重讀自己的政治詩,還會忍不住落淚,完全沒有言說過後的療癒效果。廖偉棠沉思一會,才回答:「其實沒有寫作可以承載到療癒效果,但我們可以讓心裡的難過通過寫作,讓它變得更清楚,就如魯迅的〈藥〉,最後仍要留一朵花,給世界留點希望。」詩人沒有警棍,只有詩歌作為武器。
至於為何要透過詩歌而非其他,是因為詩歌作為一種「非常」的文體,它的本質是突破日常且拒絕麻木的。淮遠亦同意廖的說法,指出在紀錄非常日子與非常事件時,詩的力量比新聞更大。傳統新聞是不帶感情的,而詩的確可以轉化心頭的沉重為藝術。廖偉棠說:「我們是詩人,詩人的天職就是寫詩。而在香港,就有許多不依從自己天職的警察,沒有守好本份。」
其後兩位詩人各朗讀數首自己在反送中事件後寫的詩,氣氛持續沉重,直到活動臨結束前,兩人討論到如何看待與自己政見不合的詩人所寫的詩。兩人並無舉出實例,但淮遠道出了他的標準:「其實異見並無問題,總有人會站在對面,但我所判別的標準是他的作品是否出於真誠。」他遙舉莫言為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寫出支持中共的文章,使淮遠拒絕閱讀他的作品。
對談過後,觀眾熱烈舉手發問,從70年代開始創作至今的淮遠彷彿一部香港文學史在台灣讀者面前攤開,討論從詩學到香港文學無所不包,從粵語寫作到淮遠獨特的寫作風格,甚至有留台港生問到粵語使用者如何良好運用書面語寫詩等,逼近創作與語言本質的鋒利問題。「詩是探照燈,能照見幽微與貧瘠」,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的淮遠與廖偉棠,就如理論愛好者常言道的「少數」(Minority),以粵語與特有的思考模式,透過嚴峻政治環境下的詩歌,講解香港的非常狀態,撐開了日常的裂縫,「堅持鑿進深處,鑿出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