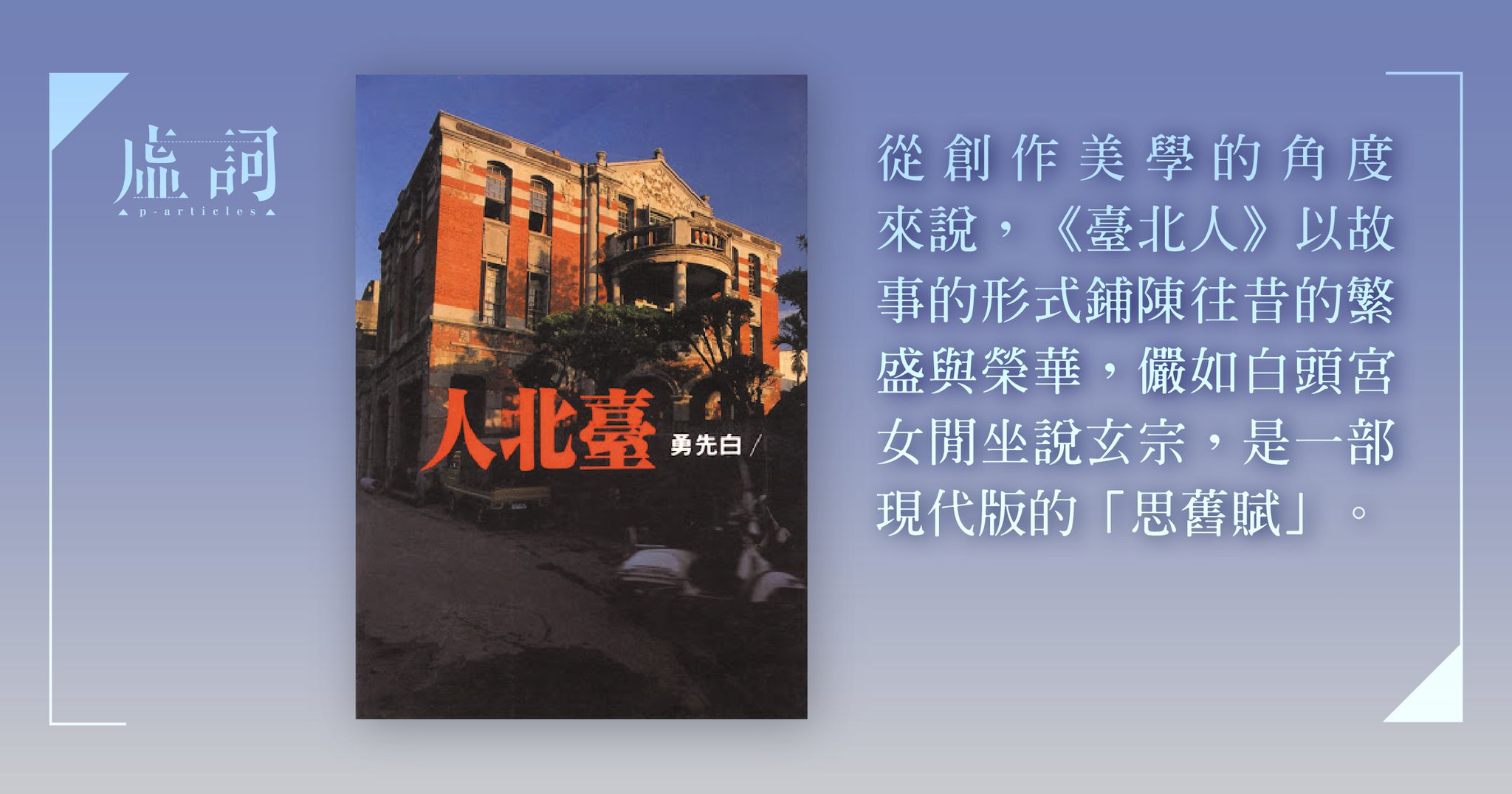現代「思舊賦」——白先勇《臺北人》新論(下)
2. 白頭宮女說玄宗——蒼涼美學
《臺北人》刻寫一代民國「謫客」的眾生相,表現這批流亡者的悲情人生,以及他們的流離之痛,同時也流露出繁華事散的蒼涼史觀與人生觀。夏志清在《白先勇論》中說︰「《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粱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註7)」確實,《歲除》《梁父吟》《花橋榮記》《秋思》《國葬》等作品,內容涉及到了一個風雲變幻又憂患深重的大時代,從辛亥革命、五四、北伐、抗戰到國共內戰,一部民國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都在一個個人物的故事之中。不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白先勇在反映社會歷史事件時,並不依社會意識型態來判斷是非對錯,也沒有以「寫史」的形式來「報導」,他始終從文學的藝術本位出發,以人道的原則,對史實作形象化的處理,將其化為故事的有機部分。
小說家正視社會、直面人生,並不迴避政治與社會的大是大非,然而,也要看到,他不同於社會歷史學家、政治家,或道德家,不會以世俗的政治或道德意識型為依歸,也不會以「政治正確」為創作原則。小說家的文學本位是講故事,他遵循的是藝術的法則,即以形象化的方式,透視、演繹社會歷史。文學反映社會現實,不是簡單的複寫,而是「創造性複製」。別林斯基說得好︰「若要忠實地摹寫自然,僅僅能寫,就是說,僅僅駕馭抄寫員和文書的技術,還是不夠的;必須能通過想像,把現實的現象表逹出來,賦予它們新的生命。(註8)」這創造性想像,就是以藝術的法眼來觀照現實,並作出意象化的呈現。無論是寫實的呈現,還是誇張、變形表現,都需要將史實鎔鑄到故事的肌理之中。白先勇深諳藝術的法則與創作規律,總是能夠與社會現實拉開距離,讓紛紛揚揚的歷史煙塵在時間中沉澱,將外在的經驗內化為生命體悟,融入到個體人生故事中,像劉禹錫的《烏衣巷》、元稹的《行宮》、杜牧的《金谷園》一樣,通過具體的意象,揭示滄桑人生,表現興亡盛衰的歷史感。
從創作美學的角度來說,《臺北人》以故事的形式鋪陳往昔的繁盛與榮華,儼如白頭宮女閒坐說玄宗,是一部現代版的「思舊賦」。
《思舊賦》講述一位老女僕探訪舊主人的故事,情節十分簡單,但主題意蘊與創作格調都極富藝術品質。老僕順恩嫂在一個冬日的黃昏來到李宅門前,「望著李宅那兩扇朱漆剝落,已經沁出點點霉斑的檜木大門,出了半天的神」﹙P111﹚。這是整條巷子中唯一的舊屋,前後左右都起了新式的公寓高樓,李宅這棟破舊的木板平房被團團夾在當中。小說起筆就營造出一幅凋敝的景象,接著又通過兩個老僕的對話,講述出李家「比不得從前了」的衰落情況。夫人兩年前去世,「初七」未過,兩個年輕的僕人便勾搭著偷跑了,還把夫人一箱玉器盜得精光。李家小姐和一個有老婆的男人搞上,大了肚子,跟父親鬧翻,離家而去,長官也氣得幾乎出家當和尚。李家的少爺到外國留學,則落得個精神失常,整天傻坐在院子內的蒿草中。作品透過兩個老僕的口,感嘆一個名門之家的興敗,「死的死,散的散」﹙P119﹚,「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P122﹚。這是一篇飽蘊詩情與象徵色彩的小說,如散文詩一般韻致深長,譜出了一曲繁華事散、沒落凋零的輓歌。《思舊賦》淒迷的藝術氛圍,是《臺北人》美學格調的一大寫照。
白先勇就是以這樣一種藝術筆調,鋪陳出一個又一個「臺北人」的故事。這些飄零人,苟活在殘敗的軀殼內,沉醉、沉緬於各自的「過去」中。
《歲除》藉講述一餐年夜飯的情景,揭示一位老兵五味雜陳的人生。故事中的賴鳴升,從台南來到台北劉營長家吃團年飯,三杯酒下肚,話匣子一打開就是小半部民國史。他當年在四川的時候,已是騎兵連長,眼前的劉營長還是他的部下。這個老兵北伐時打過孫傳芳,抗戰時參加過台兒莊戰役,而現在淪落到做榮民醫院的伙伕頭。時移世易,高下易位,當劉營長舉杯向他敬酒時,他已不能領受,故而霍然立起將劉營長按到椅上,以哥兒、老鄉的情份對飲。席間的軍校學生俞欣興沖沖地問「老前輩也參加過『台兒莊』嗎」,他打鼻子眼裡笑了一下道:「『台——兒——莊——』,俞老弟,這三個字不是隨便提得的。」﹙P63﹚他突然間氣吁吁扯開衣服,露出胸膛上一個碗口大的殷紅圓疤,紅著一雙眼睛說:「俞老弟,我賴鳴升打了一輩子的仗,勳章倒沒有撈著半個。可是這個玩意兒卻比『青天白日』還要稀罕呢!憑了這個玩意兒,我就有資格和你講『台兒莊』。沒有這個東西的人,也想混說嗎?」﹙p64﹚酒不醉人人自醉,他的光榮履歷也只能在這個時候,對著一個軍校生榮耀一下而已。現實中的他滿肚子的酸楚,「吳勝彪,那個小子還當過我的副排長呢。來到台北,走過他大門,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上禮拜,我不過拿了我們醫院廚房裡一點鍋巴去喂豬,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P67﹚「這幾十年,打滾翻身,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沒經過?到了現在還稀罕什麼不成?老實說,老弟,就剩下幾根骨頭還沒回老家心裡放不下罷咧。」﹙P67-68﹚一位老兵的人生況味,只能在這樣的時刻吐露一番,就像他最後走進盥洗室翻江倒海的嘔吐一樣。
生在將軍之家,給了白先勇一個創作的優勢,即能夠近距離觀察審視名門顯貴的生活,揭示高層「臺北人」的生命情態。《梁父吟》和《國葬》是這部「民國史」中極有份量的篇章,作品中的翁樸園、李浩然都是曾經叱咤風雲的人物,身世顯赫,卻又結局淒涼,他們的生命史都有滄涼、悲壯的悲劇感。
《梁父吟》中的翁樸園是一位元老級的人物,參加過武昌起義、北伐,一身戎馬倥傯、縱橫捭闔。故事中的樸公剛參加另一元老王孟養的公祭禮,由王的學生、幕僚雷委員陪伴回家。他邀對方入屋小坐,閒聊下棋。樸公在言談間提起與王孟養結識的淵源,也就帶出了一段革命歷史,三個四川武備學堂的同學桃園結義,參加武昌起義,王孟養如何在黃鶴樓上揮馬刀喊口號,三人如何東征西討等等,聊開就是一段輝煌的人生歲月。話題回到治喪之事上,樸公對王孟養之子不了解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頗有看法,決定以他自己的名義在「七七」那天替孟養辦一場超渡。雷委員與樸公對弈二十手光景,棋盤一角被打圍勒死了,他思索期間,見樸公垂著頭,已經矇然睡去,於是喚醒樸公向他告辭。樸公說,「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P138﹚這句可圈可點的話,對人物內在心理作了深刻的揭示,突顯出老將的不死之心。現實與心願形成落差,更見悲劇性的張力。
《國葬》這篇壓卷之作,一如《梁父吟》的續篇,是對一位老將悲劇人生的最後描說,也是對其鷹揚虎嘯一生的最後敬禮。小說中的陸軍一級上將李浩然,是北伐英雄、抗戰功臣,又是國共內戰的敗將。故事是以第三人稱的客觀敍述展開,視角鎖定在將軍當年的副官秦義方身上,以他的眼睛及心理活動,去環視葬禮的盛況以及回顧將軍的人生片斷。敗軍之將,不敢言勇;負國之臣,不敢語政。廣東背水一戰,全軍盡喪,手下三虎將或隱居香港,或住進榮民醫院,或當了和尚。李浩然退隱台灣後,沉寂落寞,晚景淒涼。老副官跟隨將軍三十年,在啓靈時,他也蹭上敞篷的侍從車,送老長官最後一程。
整個部隊士兵倏地都轉過頭去,朝著靈車行注目禮。秦義方站在車上,一聽到這聲口令,不自主的便把腰桿硬挺了起來,下巴頦揚起,他滿面嚴肅,一頭白髮給風吹得根根倒豎。他突然記了起來,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謁陵,他從來沒見過有那麼多高級將領聚在一塊兒,章司令、葉副司令、劉副長官,都到齊了。那天他充當長官的侍衛長,他穿了馬靴,戴著白手套,寬皮帶把腰桿子紮得挺挺的,一把擦得烏亮的左輪別在腰邊。長官披著一襲軍披風,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掛在腰際,他跟在長官身後,兩個人的馬靴子在大理石階上踏得脆響。那些駐衛部隊,都在陵前,排得整整齊齊的等候著,一看見他們走上來,轟雷般的便喊了起來:
「敬禮——」﹙P277-278﹚
這最後的一幕也是今昔對照,以過去的榮耀反襯今日的悲愴。老副官硬挺起腰桿領受著部隊給將軍的那一份敬禮,這一幕又是何其悲愴與諷刺?
白先勇就是以這樣的文學性手法揭示一代「臺北人」的命運,表現其歷史意識與滄涼史觀。他不作長江大河式的宏大敍述,不描繪英雄人物指點江山的壯闊場面,只專注於揭示在歷史的摺縫裡存活的生靈。他擅長以人物為中心,鎔鑄社會歷史風雲。這得益於他所接受的中西方文學文化滋養。早年在台灣讀書,辦《現代文學》時,他已從現代主義經典中得到歐風美雨的洗禮。留美期間,像許多留學生一樣,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產生認同危機,本身的價值觀與信仰也都得重新估計。他對文學創作有了新的認知,也在創作中實現了脫胎換骨的轉化。他曾表示在愛荷華作家工作室學到不少東西,如從珀‧盧伯克﹙Percy Lubbock﹚的《小說技巧》中,得到敘事觀點的啟示,掌握到小說創作的兩大要訣,敘述法與戲劇化。所謂戲劇化,就是製造場景,運用對話。他自言︰「一篇小說中,敘述與對話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小說技巧不是『雕蟲小技』,而是表現偉大思想主題的基本工具。(註9)」正是有這樣的藝術認知,以及「自我的發現與追尋」(註10),他的創作展現出新的視野與技藝。同時,他也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傳統。他說︰「雖然在課堂裡念的是西洋文學,可是從圖書館借的,卻是一大疊一大疊有關中國歷史、政治、哲學、藝術的書,還有許多『五四』時代的小說。我患了文化饑餓症,捧起這些中國歷史文學,便狼吞虎嚥起來。(註11)」通過這一段求索,他實現了中西融通的藝術修煉,實現了創作上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也產生了獨具美學風格的藝術傑作。
《臺北人》中的作品大都暗用「三一律」的戲劇結構原則,時間、地點、動作高度集中,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遊園驚夢》《歲除》《思舊賦》《梁父吟》《國葬》等,都是截取一段時間的橫切面,以閃回的方式作今昔對照,平行敍述。
在這批小說中,《花橋榮記》是一篇極富藝術成色的佳作,在人物形象刻畫上尤顯功力。小說以榮記米粉店老闆娘的視角,展示出一群台北淪落人的悲慘命運。小店的包飯客多半是寅吃卯糧的小公務員,許多又是廣西老鄉。從前在柳州做木材生意的李老頭,有「李半城」之名,流離台北,在店裡吃了八年包飯,七十歲大壽獨自點了一桌菜,第二天就上吊而死;另一個秦癲子,在廣西當過縣長,流落台灣,瘋瘋癲癲,最後死於大水溝中,欠店裡大半年飯錢。這些食客中的國文老師盧先生,是一個本份的斯文人,坐下就悶頭吃飯,有點氣色不足的樣子。盧先生家世顯赫,爺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台,又創辦桂林的培道中學,是當地有名的大善人。他家的體面公館在戰爭中被一把火燒光了。老闆娘有心將自己的姪女介紹給盧先生,撮合一對亂世兒女,卻被他一板正經地拒絕了,「請不要胡鬧,我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P171﹚。原來他心有所屬,且一心一意等待著他的心上人。他終於等到了喜訊,臉上也泛起了紅光。香港的表哥聯絡上他的未婚妻,只要有十根金條子,就可將她偷渡過來。他拿出用十五年時間苦苦攢下的五萬五千元,結果人財兩空,精神大受打擊,也變了一個人。他跟「肉彈」洗衣婆阿春姘居,結果又遭一劫,阿春在家偷人,盧先生捉姦反遭打傷。這個靈肉沉淪的人最終心力交瘁,死於「心臟麻痹」。一個令人唏噓人生故事,深刻反映出一代「臺北人」的飄零之苦,以及鄉思之情。這個作品特別見功力的地方是,講故事的方式更靈活多變了,敍述與戲劇化交相配合,表現得天衣無縫。人物之間多了互動,老闆娘與盧先生的交集,增強了小說的戲劇性效果,盧先生的人物形象也得到立體呈現。
夏濟安曾讚白先勇「文字很老辣」(註12),此評斷言之極是。白氏語言是地道的「中國話」,既文且白,還不乏接地氣的俗語。十分難得是,沒有歐化毛病,沒有文藝腔。他筆下的人物,一個個都有著自己的「鄉音」,金大班張口就是上海話「娘個冬采」;賴鳴升這個老兵則一口四川話,「他做大是他的命,捧大腳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幹不來」﹙P67﹚;花橋榮記的老闆娘,用桂林話吐出小生意人的苦楚,「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白了一頓」﹙P165﹚。筆下人物的語言,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情理與腔調,這是白先勇高妙藝術功力的又一明證。
概括而言,《臺北人》從文學的本位出發,透視現實,反映歷史,是一部藝術成色極高的典範之作。
結語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白先勇不是那個在黃鶴樓上揮舞馬刀喊革命口號的激昂少年,而是站在大洋彼岸回望故土的遊子。當年,他佇立密西根湖畔、蹭蹬在紐約街頭,一時不知身在何方,白雲千載空悠悠,國破家亡獨徬徨,體悟到一個千年前中國詩人的感懷,一個轉身也就完成了一次藝術生命的蛻變,兀然而立,成為現代的崔顥、劉禹錫。時間、空間的距離,使他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看那一代流散飄零人的生命景況。異域他鄉的高樓,勝似黃鶴樓,他隔洋發出了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感時傷懷之慨。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浮生如夢一場空,這種虛幻的人生觀以及悲憫之心,形成了他的蒼涼創作意識及美學意趣。他筆下的「臺北人」緊抱着「過去」、回眸歷史,追憶往昔,留下悵望夕照的孤獨身影,已永鑄於中國文學人物長廊。《臺北人》沿續了中國文學的感時傷懷抒情傳統,如一曲現代版的「思舊賦」,與文學史上一篇篇弔古傷懷的經典形成古今合鳴。而他自己,也成為了「永遠的白先勇」。
〈本文依據文本︰白先勇《臺北人》,爾雅版,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