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手再念一次:鍾玲玲重寫《玫瑰念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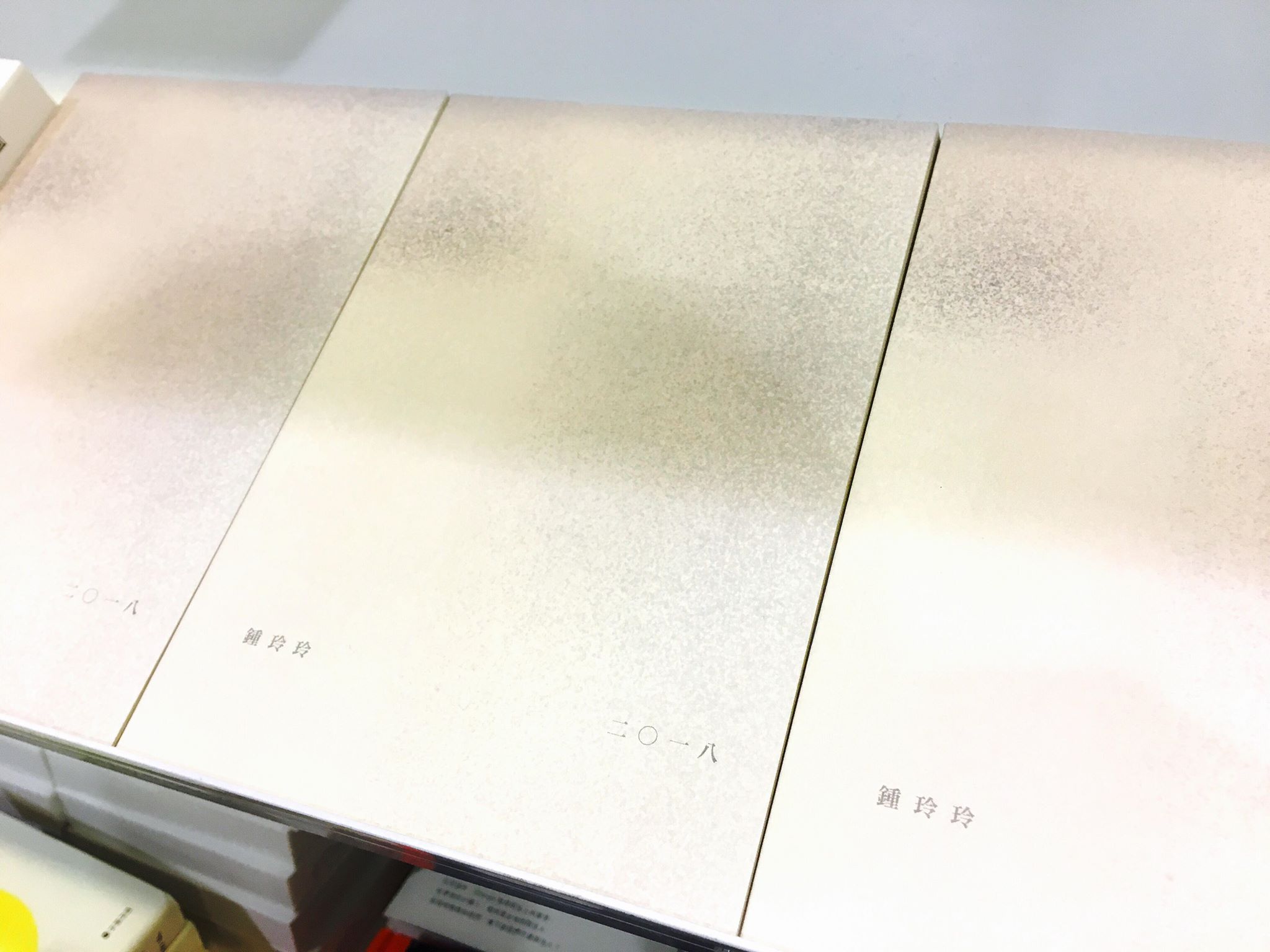
2018年版的《玫瑰念珠》試著回答舊版「愛是甚麼」的問題。
今年書展主題是「言情小說」,說是李碧華、張小嫻表示不參與,於是就以Middle補上。在這件事上我不太關注Middle是否與張愛玲齊名,喜歡張的讀者定當知道的,現在是連張愛玲晚年的假髮也可以展出的時代,齊名都不過是巧立名目填滿展區的一種方法而已。我真正介懷的是「言情」——既作為類型(genre)的一種,也作為情動理論(Affect Theory)的關注點——在主流認知內變得何其狹隘,事實上「言情」也得看看,言的是甚麼情。今年悄然出版的鍾玲玲新書,說是《玫瑰念珠》的新版。迫不及待讀完後,我再一次被鍾玲玲所言之情震懾。如果「言情」就是「說愛」,本年度「言情」之最,非鍾玲玲莫屬了。
1997年,鍾玲玲也曾出版《玫瑰念珠》,內裡寫的是父母輩陽桂枝、汪玫莉,兒女輩文生和愛菲;2018年出版的《玫瑰念珠2018》寫的同樣是父母輩陽桂枝、汪玫莉,兒女輩文生和愛菲。這無疑是一場重寫。比對這兩本書的重複與差異,雖然兩書在整體敍述風格上仍然是「自我的昇華取代了純粹的發展」,1 因為不斷指涉內心思緒與私密經歷,小說仍然走向私語小說一途,讀起上來本是不易取得共鳴的。不過,因為後者明顯不像前者那麼零散,乍看之下不像1997年版的「拒絕讀者」之姿那樣決絕。2 不再零散,主題便更突出,我們還是能從中抓住關鍵的叩問:甚麼是愛?
兩本《玫瑰念珠》都圍繞最關鍵的概念「愛」,一個人是怎樣學會「愛」的呢?鍾玲玲不止去談人愛另一個人的各種方式,同時要叩問「愛」有多少形式,「愛」又是甚麼。1997年的文生不懂得甚麼是「愛」,身為母親同時是作家的徐良琴其實也不懂,在觀察兒子對愛的好奇時,敍事者不斷質詢何謂「愛」:
但這個世界上,應該還有許許多多的愛,可愛是甚麼呢,就好像一日不弄懂它,就一日無法說愛,他但願能弄懂它,卻不知甚麼時候。3
——鍾玲玲《玫瑰念珠》(1997)
2018年版的《玫瑰念珠》試著回答這問題。世界上那麼多人說「愛」,「愛、愛、愛、愛。一切都是為了愛」,4 從各種「愛」的呈現看來,愛情也好、親情也好,愛總是勾起人一切的情感,不純然是正面的,更多時是負面的情緒:
愛的奧秘教人心酸。[……] 母愛讓愛菲從此愛上了愛,並且像有機物質那樣,隨同周遭的變化而變化。為甚麼事情不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呢?
——鍾玲玲《玫瑰念珠2018》
這便是所謂情動(Affect)的關鍵所在。「情」的性質只有在人面對不同事物的時候才能展現,情總是由自己內心而發,同時受他者所牽動,其能動性在主體與他者之間不斷流動。所以敍事者說,愛是不斷變化的,無法定義。它可以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但卻不是無頭無尾的無依無靠的,愛只能依賴人。
「玫瑰經是怎樣念的?」黃念欣在一場對談中問,董啟章回答手持玫瑰念珠念玫瑰經的方法後,她再道:「所以用玫瑰念珠念一遍玫瑰經,好像體會了聖母一生?」5 我一邊翻閱她與董啟章對談新版《玫瑰念珠》,一邊回想鍾玲玲重寫玫瑰念珠的行為,事實上,黃念欣一語道破閱讀《玫瑰念珠》兩個版本的關鍵。因為「情」的特質,寫「情」必寫人,寫人而又以私語成書,則《玫瑰念珠》是鍾玲玲的自我書寫,正如念玫瑰經等同體會聖母的一生,讀完《玫瑰念珠》讀完鍾玲玲的一生。而重寫自己的前作,即是重寫自己的一生。事實上,1997年版《玫瑰念珠》鍾玲玲已有寫人一生的自覺:
她的一生若然由她來寫,定然是打從這兒開始的。
——母親一連生下三個女兒,我排行第三,卻名列第四,因在我的前頭,還有大媽的一個女兒。
眼看著快要走到盡頭了,卻又從頭來過。6
新版更直接指向自己,作者的身影完整地出現在小說內:
現在你已經知道太晚的意思了。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對晚期就是災難又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這是終點,無所謂了。一個作者能寫甚麼要看他是個怎樣的人。我沒有種子,只有土壤。在這種荒誕的努力中,充份說明沒有任何價值是自然就有的。發表是為了答謝少數曾經喜歡我的人。我已經把話說盡再沒有更多了。
可以說,當作者以更老練、更直率、更「不刻意討好」的晚期之姿重寫自己的作品時,新舊作品的差異需要關注,就像回答何謂愛,令作者的創作母題更突出;而其重複亦必定更具意義,作者事隔多年再寫同一件事,是對一個情節與意念的再肯定。更值得注意的是,《玫瑰念珠》表面上只寫自己,也很純粹且單一地只叩問「愛」是甚麼,「情」為何物,但這場私密言談出版後,其公共性卻同時展現出來。作者表明書寫自身,那麼這些私語就直接面對讀者了,而其情動力亦在這之間流通與體現。
但是,回答「愛」的問題,究竟是為了甚麼?又或是,為何我們要問何謂愛,為何一本小說需要重寫?叩問「愛」不過叩問「人」。我們不妨從另一角度來思考「言情小說」。歷來「言情小說」就是大量印刷、結構重複的時令讀物(無論是20年代被強烈批評的被鴛鴦蝴蝶派,還是所謂三、四毫子小說),因其重複,意味著我們可以捉緊整個被結構化的情感展演形式(情感無分高低,只分深淺),去談論其社會、文化上的意義。雖然書展一個唔該眼高手底,把得來的好題目隨便意思意思敷衍過去,但是,讀者仍可用心翻翻沒有入選的「言情」作家作品,例如鍾玲玲的《玫瑰念珠》。畢竟「言情小說」本是依賴讀者存在的文類,所謂情所謂愛,只有在人(作者)和人(讀者)之間才能生存。
1 同上註,頁75。
2 黃念欣:〈如何撿拾生命中的玫瑰與念珠?——讀《玫瑰念珠》的「晚期變奏」〉,《晚期風格:香港女作家三論》(香港:天地圖書,2007年),頁66 – 67。
3 鍾玲玲:〈說愛我的人是誰〉,《玫瑰念珠》(香港:三人出版,1997年),頁6。
4 鍾玲玲:《玫瑰念珠2018》,香港:水煮魚文化,2018。
5 黃念欣、董啟章:〈無所屬的玫瑰,有所屬的念珠——對談《玫瑰念珠2018》〉,《字花》第74期(2018年7月),頁124。
6 鍾玲玲:〈本事〉,《玫瑰念珠》,頁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