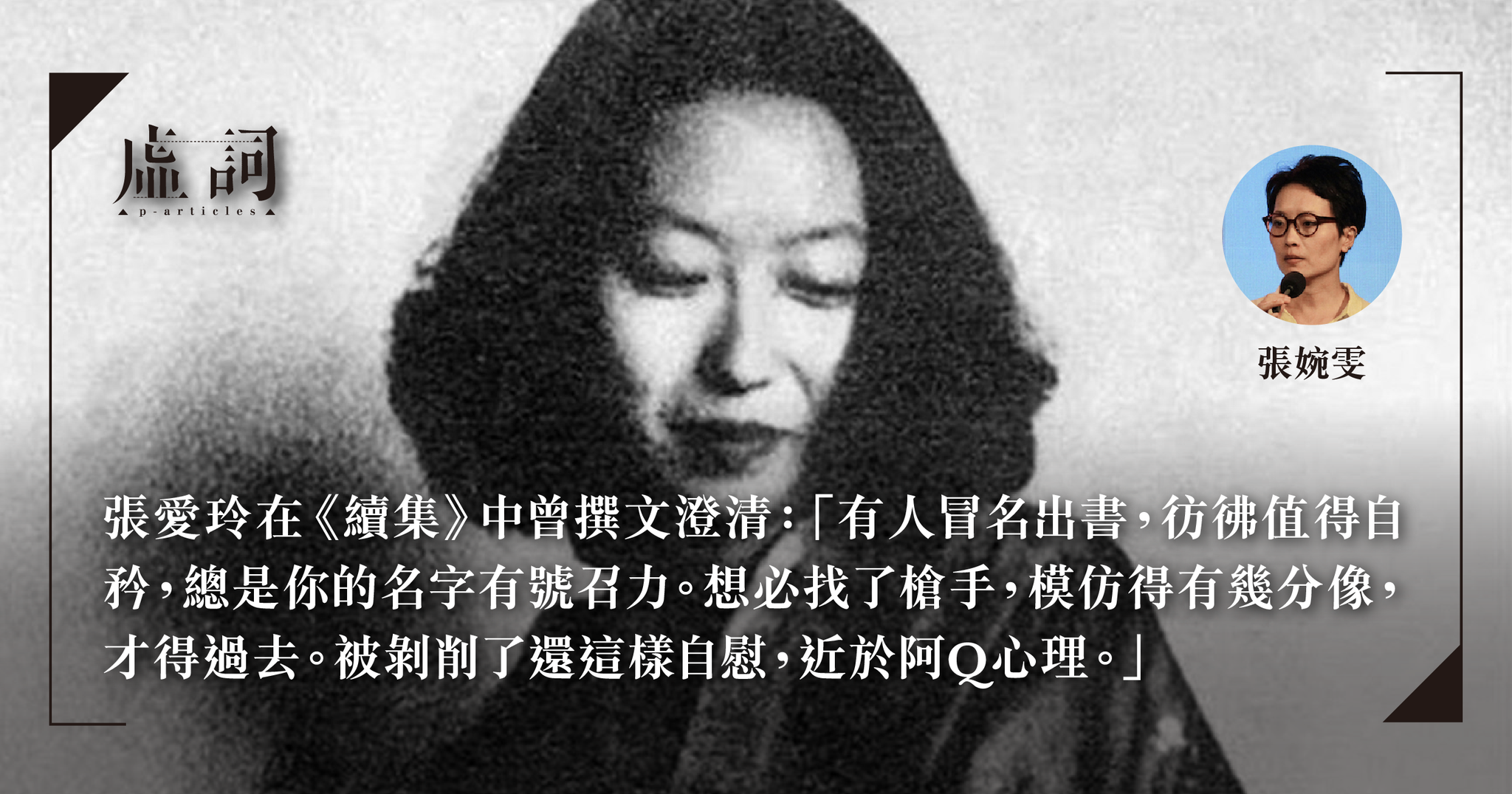【悼米蘭昆德拉】嚴肅的輕蔑:米蘭昆德拉的〈愛德華與上帝〉
繼續悼念昆德拉,李敬恒從《可笑的愛》的〈愛德華與上帝〉揭示了主角在原則和宗教信仰之間的掙扎,並由此發現昆德拉待人處世的獨特視點,到底何謂活得真誠、真誠有何代價,以及嚴肅與輕浮的界線如何促成道德問題。 (閱讀更多)
【無形・辛波絲卡,種種可能】遇上從前的自己:辛波絲卡的〈少年〉
你有否幻想過遇上少年時期的自己嗎?你又會有何反應?李敬恒是次分析辛波絲卡的〈少年〉,寫「我」和少年的「她」偶遇,然而二人在各方面都大相徑庭,關係幾乎形同陌路,最後發現盛載着母愛的圍巾一直連結着她們,從而延伸到李敬恒對少年的聯想,原來有些話題終究是難以啟齒。 (閱讀更多)
【悼米蘭昆德拉】文青的界線,並悼米蘭.昆德拉
因著米蘭.昆德拉辭世,鄧正健撰文悼念自己文青時代的偶像之死。生命是輕,但因為不能承受,所以讀來沉重。昆德拉之所以能在他的文青時代紮根在心,是因為展示了一種文學哲學化的敘事可能。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