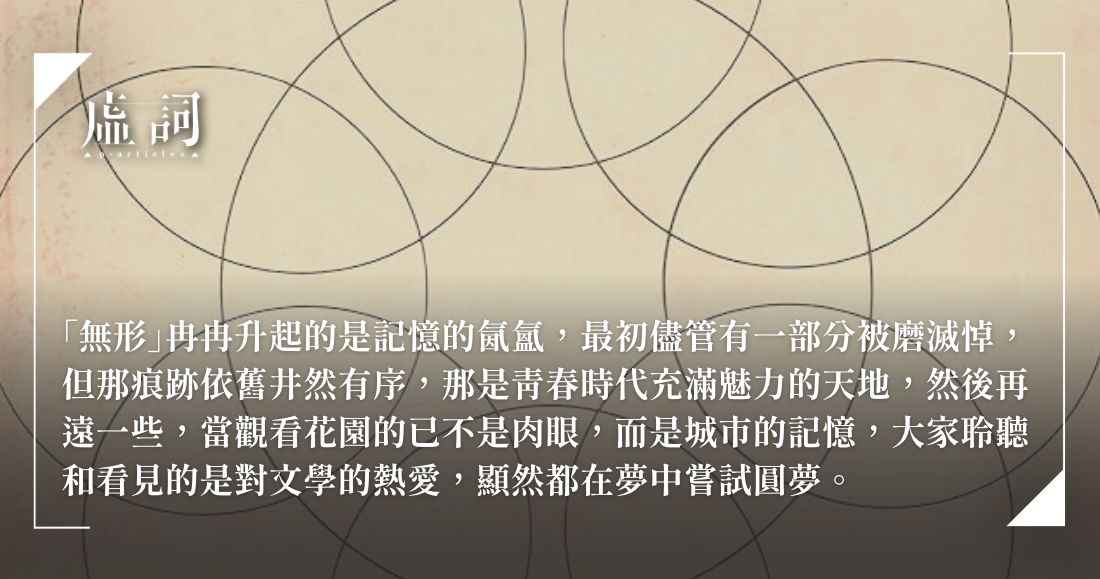當我們徘徊在過去的人和事:誰會被銘記?誰會被時空遺棄在歷史中?用什麼方式被永久懷念?當這些從記憶之書消散,是否意味著書寫終結?陳慧寧談「無形」結束,想起比利時文學批評家喬治・普萊的「圓圈蛻變」,而「無形」就像是個三重花園,從看見香港文學文化現象,城市轉變的變化,到觀看歷史,當中冉冉升起的是記憶的氤氳,可以目睹許多人在其中圓夢。 (閱讀更多)
文化交融與傳統蛻變:讀楊牧詩
散文 | by 楊小濱 | 2024-05-07
被譽為「最接近諾貝爾獎的台灣作家」的楊牧,其三十冊跨文類大全集《楊牧全集》在其逝世四週年隆重問世,當中包括全新編纂、增補逸作、未公開書信手稿等。上海學者楊小濱為此撰文,談起楊牧的不同面向,而學者王靖獻和散文家葉珊常常潛入楊牧詩歌寫作的領域,不同身分的楊牧使其詩歌體現出文化和美學的多樣性,但他依舊保持著基本一致的風格,可見他對生命與時間、人與自然關係的沉思。 (閱讀更多)
【虛詞・◯】追憶90年代香港雜誌年華
梁璇筠藉著《無形》結束,追憶90年代香港雜誌的花樣年華——我們都曾經在雜誌之中找到生活的靈感,甚或不知不覺地被薰染了屬於一個時代的美學。就如亦舒小說裏,那男的一往情深要女主角嫁給他,女主角一貫冷血,或清醒︰「養我?只為我支付每天的五份報紙,每月十幾本雜誌都做不到?」能夠有閒情看雜誌就是好的生活,80到90年代是經濟最蓬勃,香港流行文化豐沛活潑的年代,每個區每個街角都有一個大大的報攤,而那裡就是當天的世界視窗。 (閱讀更多)
【虛詞・◯】虛詞。是愛我們更多的那人。
散文 | by 張瀞 | 2024-05-04
張瀞在台灣。初次遇見虛詞,是2023年的八月夏季某日,亞熱帶無風的教師辦公室裡,同仁正管教學生。她鍵入「辛波絲卡」。螢幕跳出數個搜尋結果,其中之一是作者雙雙為「虛詞」舉辦的辛波絲卡活動而衍伸出的一首詩------《新詩課上的白日夢》,當時因而被其中幾句詩句深深地打動。 (閱讀更多)
新亞研究所圖書館的文化遺產保護
自1953年成立的新亞研究所,一直以「誠明」心性之學,作為個體道德修行的目標,逐步邁向聖賢之路。陳慧寧談新亞研究所圖書館藏書與狀況,不但保留目錄咭片的檢索系統,亦構建了新亞先哲的研究風範,而藏書空間的維護與設置,同樣足見其負載的文化和歷史的傳承。最後陳慧寧想起圖書館作為社會的反映,電子閱讀逐步替代印刷圖書的閱讀,圖書館也開始了收藏的結構性調整,感慨紙質圖書終究會變為一種遺產。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