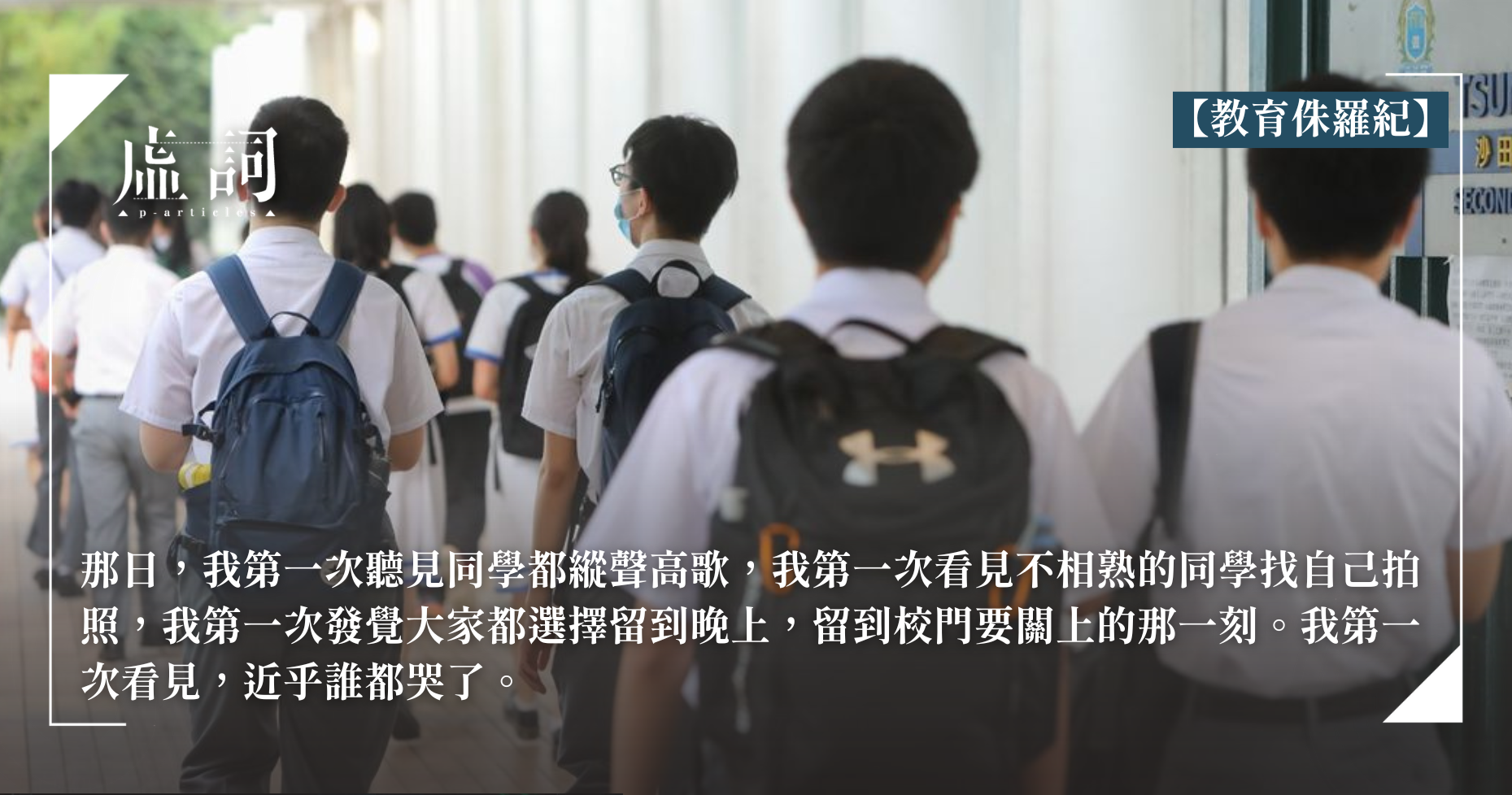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Last Day
教育侏羅紀 | by 無鋒 | 2025-05-26
假如時間就在那一剎,像照片裡的容顏被定格,我就不會再成熟地相信,我們,終究都是彼此的過客。
最近和一位將赴美國留學的朋友臨別吃飯,少有地聽到他說了一句金句:「人總會經歷不少的事,遇到不少的人。自然不全都是令人高興的,像是我,就有令人痛心的人際關係。但是我想通了。」我眉頭一挑,眼角拉開:「想通什麼?」他徐徐道:「你所經歷的事,遇到的人,不論是好是壞,那都是構成你生命的一部份,才能造就你這個人。」
老實講,這句金句少不免老土,定必不能發人深省,令人大徹大悟。不過當我回家細細思考,頓覺這句總是沒錯的。這句言下之意是,要擁抱身邊的一切,感激別人進入自己生命中吧?
「經歷的事,遇到的人……」我腦海中浮現一個畫面。我看見DSE中文寫作的答題卷上,翻開一頁,那裡,譜寫了一段平凡而簡單的故事。
我和許多人一樣,在一所中學度過了六年。然後我眨了眨眼睛,就迎來了中學生涯最後一個上課日。
那日,我第一次聽見同學都縱聲高歌,我第一次看見不相熟的同學找自己拍照,我第一次發覺大家都選擇留到晚上,留到校門要關上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看見,近乎誰都哭了。
「今天是last day,管他什麼DSE。」我被他這句話嚇了一跳,因為他成績極好,應該不是這樣的人。我卻莫名其妙地覺得很爽。「朋友最重要?」「DSE不重要。」我記得他也留到了晚上,背著書包站在操場上,看著校園的燈火。聽著身邊的哭聲,我陪着他看燈,感慨了幾句,卻沒有太多情緒,因為我覺得離別終究是人生的必經階段。他沒有作聲。於是我又胡亂說了幾句。
他依舊沒有作聲。於是我望向了他。只見他的眸子裏有一面淺淺的鏡,映著黑夜中照亮校園最明亮的燈。只是後來,當一排又一排的燈都被關上,燈光漸淡的時候,他不知是有了什麼感觸,他的那雙眼,終究溢滿了。
和他恰恰相反的,是山姆。他和我一樣,也沒有哭泣。他只默默地給予那些哭泣的人一個擁抱。「怎麼你沒有哭?」我問。「我在思考。」他說。「你有情感嗎?」我胡亂問道。「當然有啊!」他沒好氣地說道,笑了。
更晚的時候,我和山姆和相熟的一群男生到銅鑼灣吃晚飯。乘地鐵途中,我接到了一通電話,是個女同學。「……我們打算過來。你們在哪裏吃飯?」電話的的一頭這樣說。我嚇壞了,那群女生應該也都有節目,怎麼就會想要過來的呢?但剛想問一句「為什麼」,便旋即想到了一個原因。那是她的哭泣。
早些時候,校園燈火闌珊之處,我有個摯友也哭了。一群相熟的男生也算是彼此安慰,彼此擁抱,只是許多人都已泣不成聲。我是少數沒有哭泣的一個,眼睛沒有怎被模糊。由是,我看見了遠處正在哭泣的她。我走了過去。
她看見我走來,喊了我的名字,又哭了。「我本來沒有打算要哭,只是看見他哭泣的時候,我就沒有忍住……」她抽泣着說,雙眼通紅。「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說出口……」她看見我那摯友哭泣,也止不住自己的淚水,這我大概知道是為什麼。她的眼淚和在場大部份人都不一樣,更為複雜,不只是臨別不捨的眼淚。那久藏心底的心意,直到最後一日也不敢說出來,那是痛苦的。我知道,這幾年來,她的悲喜都是因爲他。但我不知道怎樣安慰,我始終沒有這樣的經歷。
也許是女生們和她決定好了,我才收到這一通電話。「好的。我待會兒告訴你餐廳的地點,你們在樓下等可以嗎?」我小聲說。「你帶他下來?」那女同學問。我答應了。
她們希望不讓所有男生都知道這件事。而我又不能事先告訴我那摯友。也許是要刻意向所有人隱瞞的原因,我心裡有點難過,腦中更是一片空白。那時候,我看見在我身旁的,腦袋還在運作的他。那個在思考的山姆。於是我把山姆喚到了洗手間。
我把那些事告訴了他,他果然極為冷靜。只是既要完成任務,又不能令其他男生起疑心,其實極為困難。於是我倆就花時間制定計劃。
「樓下有些有趣的玩意。」山姆回到座位,向我們的目標人物說道。見其他男生好像都有興趣,他又補充了一句:「只有你才感興趣的。」我在旁邊附和:「對啊!跟我們下樓吧。」
我倆和他下了樓,看那所謂「有趣的玩意」。只是當他看見那個哭成淚人的她和那群女生,他先是一愣,看着我倆:「怎麼……」我倆沒說話。在那群女生的示意之下,他走到了她的身前。
之後我就不知道他們講了些什麼了。我倆和那群女生都到了商場的另一端迴避。我們相視無言,大概是因為我們都掛心他們這故事最終的結局。
如今的我回頭望去,看見他們那不知結局的故事,只想起了那一句我認為老土的金句:「你所經歷的事,遇到的人,不論是好是壞,那都是構成你生命的一部份,才能造就你這個人。」其實不止他們,我們每個人也都如此吧。
那群女生派遣了探子出動。探子回來報告:「還沒講完呢。一個拼命的哭,一個努力的聽。」
見大家又陷入沉默,我忽發奇想,問道:「難得我們居然會在這裡遇見,可以一起照一張相嗎?」山姆和她們都沒有意見。你是我邊拿起了手機,準備和他們自拍幾張。
她們雖然都笑了,但仍能看得出,她們曾經哭紅了的眼睛。那是憔悴的笑。山姆也笑了,笑得是如此冷靜。我則沒有笑,眼睛堅定地看著鏡頭。
「那都是構成你生命的一部份。」
時間就在這一剎,像照片中的容顏被定格,我終於幼稚地相信,我們,一直都停留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