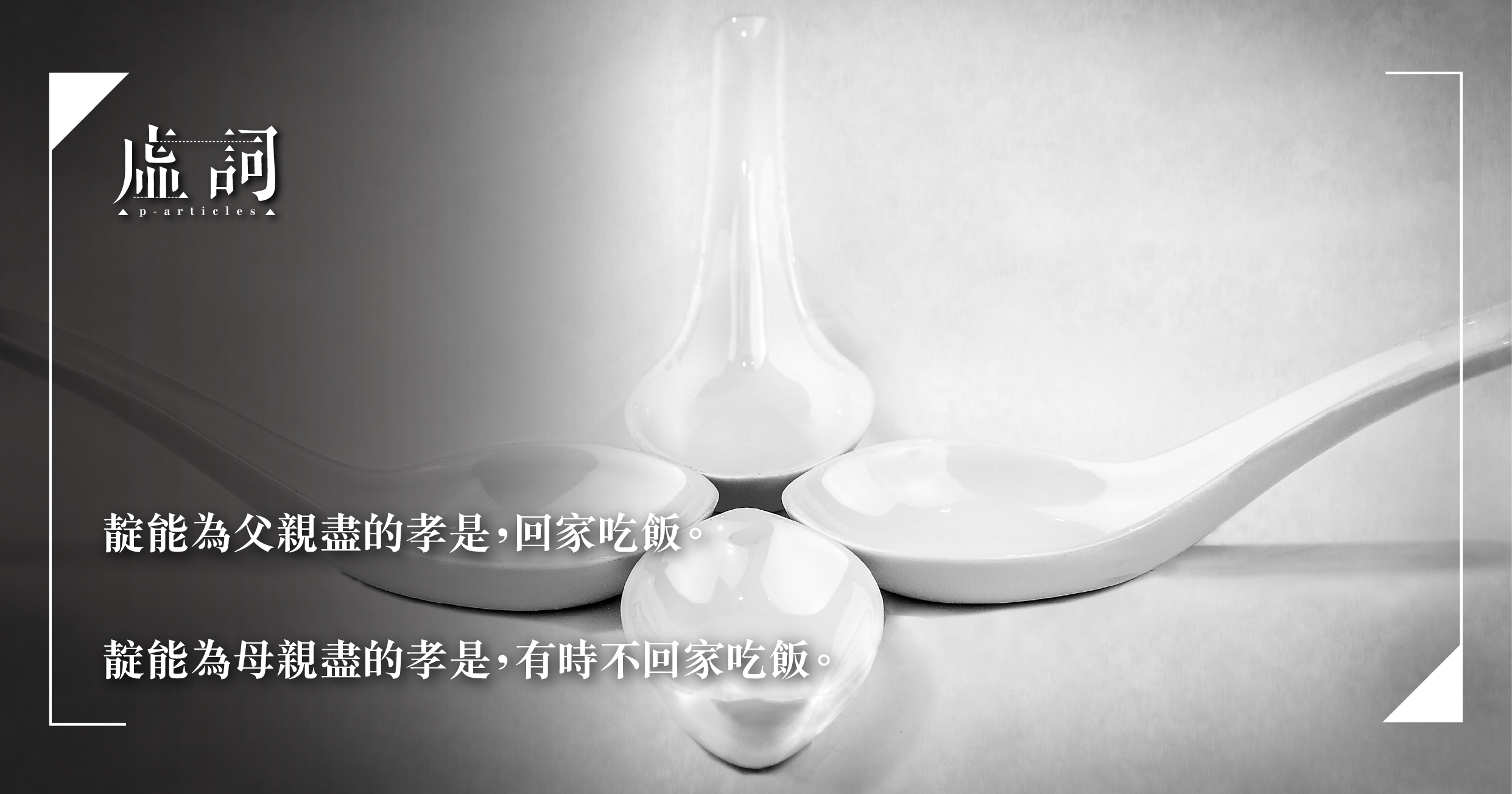起碼只是肚子,後來變成手臂、手肘,再到腳。隨著痕癢程度增加,皮膚也開始染了紅,蔓延到脖子,最後是臉。所以,她不往家中住,暫時避開。一方面是因為怕日漸失控的脾氣會嚇壞兒女,另一方面又怕裝出笑臉的可信性都失去。衣服能夠蓋住的地方,她都可以戲一句「眼不見為淨」,然而口罩以外的額頭,會使別人流露詫異的神色,她清楚看見。 因此受不來。被人看見不夠得體的話,會丢臉,既丢自己的臉,也是丢丈夫的那一張,街坊鄰居的口亦如眼睛。 神奇地,在朋友家寄住的那幾天,母親身上的紅印慢慢減退,痕癢的感覺慢慢攤涼。因此,她才回家。她如此驚訝,皮膚好了一點之後,她的第一個想法是:回家,不過,只隨便買菜。 (閱讀更多)
【無形・開門】三道門
一門之隔,引發無限想像。在余婉蘭的小說〈三道門〉,靈魂抖動,靈魂卸罪,黑夜讓萬物逐一都沉沒在意識、記憶的深淵。穿過這一道門,如像從一則寓言的隱喻裡穿出來。十支長劍立於橫陳的身體上,但沒有誰能肯定那代表甚麼。 (閱讀更多)
【無形・開門】藍鬍子與更多鬍子
光是體形就足以壓至絕望,巴掌凌亂地呼過來,摔倒,碰撞。茶几上的相框掉地,一家三口和樂融融地注視眼前黑暗。越來越多紅痕爬上妳身,妳發出狗的嗚鳴,卻於事無補。窗外霓虹燈慷慨地把妖綠塞入房間,在小沙發上映出別緻光芒。那是妳得到第一份工資後購買的家具,小巧卻剛好承載妳,以及妳的夢。 (閱讀更多)
【無形・開門】櫻桃真理奈之門
屍體乃由阿麥這些持牌醫生負責處理再交由我們運送到地底的門。醫生、軍人、殺手,業界掩人耳目的名號眾多。普遍來說,無法外洩、滯留或暴露於地面城市的東西都會被棄置於門後。經處理的屍體雖然佔最大比重,但也只是其中一種。故障失靈的電器、上一季度的時裝、或微小如不新鮮的蔬果食物以及龐大如被清拆的整幢樓宇,各行各業的門徒都在地底辛勤工作。大大小小的機構都在這裡開店,並經營各自的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