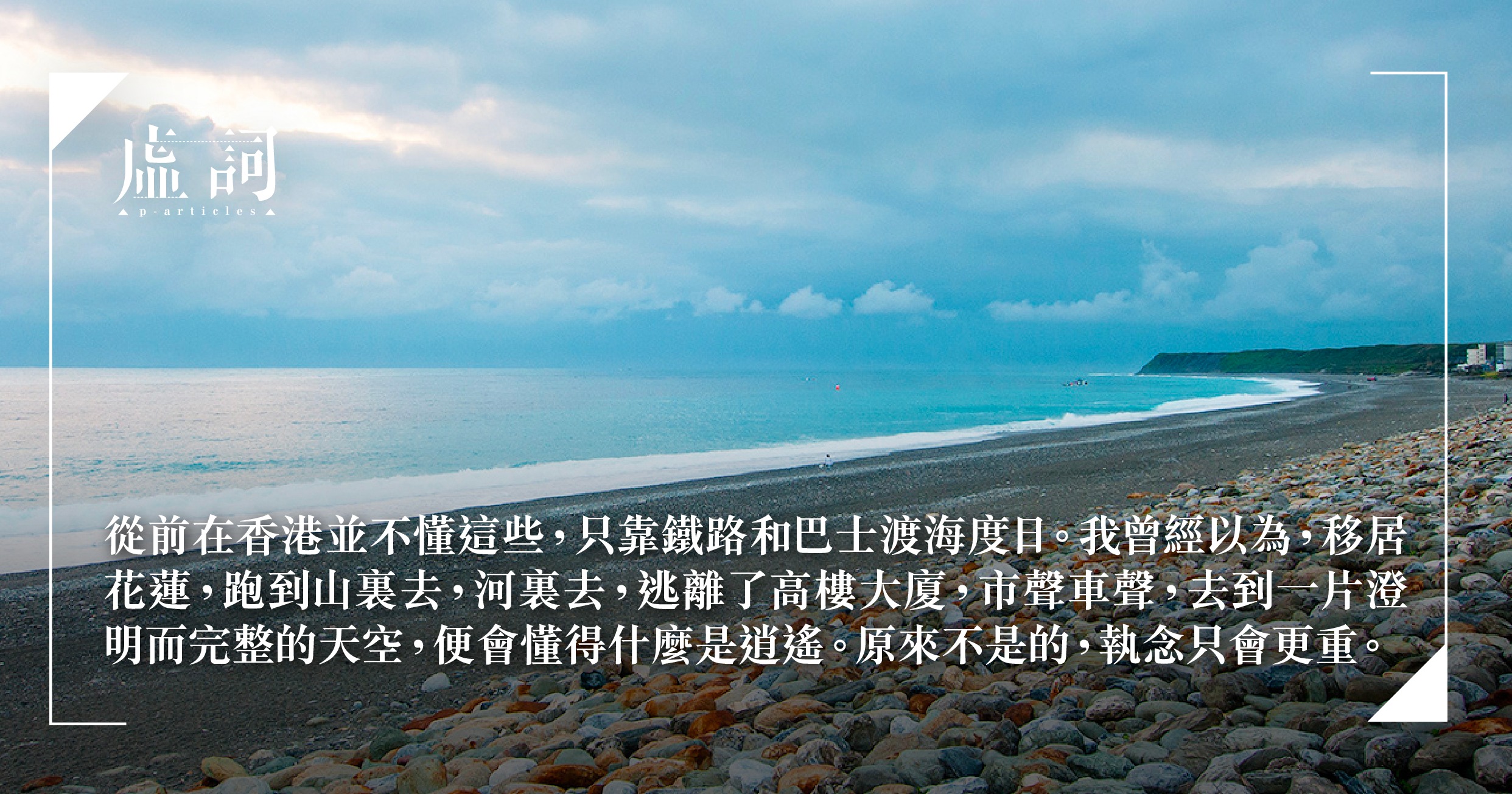河瀨直美的聖光騙了你嗎
過去從未出現過一個能將園子溫、中島哲也與河瀨直美扣連在一起的說法。但日本路邊社暨八卦雜誌龍頭《周刊文春》做到了。數天時間,河瀨直美便從一道溫暖人心的影壇聖光,變成醜出康城紅地毯的偽善女魔頭。那個在電影裡總是帶著暖光,而自己特別喜歡在背光位置被拍攝,因此總是頭上有光的河瀨直美,會否從此身敗名裂?還是放下光環,承認自己就是一個專制自私、腹黑惡毒難相處的女魔頭? (閱讀更多)
【無形.防空洞與避難所】防空洞精神:不免恐懼,與之共存
鄧正健雖沒有親身的戰爭記憶,但聽過、讀過不少。兩次大戰(尤其是二次大戰)改變了人們逃避戰爭的模式:防空洞終於被發明了。空軍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們戰爭模式,陸軍未到,空軍先至,空襲既成了軍事行動中的重要戰術,也構成了平民對戰爭恐懼的原始記憶。美國畫家洛克威爾有一幅名為《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作品,畫中有一對美國夫婦,妻子正為睡得正香的一對孩子蓋被,父親則拿著報紙站在一旁。此畫產生一顯一隱兩重意涵:顯是在沒有戰爭的美國國土上,孩子尚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畫裡沒繪出來的倫敦孩子,這種自由則被戰爭剝奪了。 (閱讀更多)
【無形.防空洞與避難所】 一路向歐
散文 | by 區區愚生及安迪 @ Gunslinger 不曾遠去的硝煙 | 2022-05-25
今年2月,俄羅斯以「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入侵鄰國烏克蘭,並快速突進烏國首都基輔,但烏克蘭政府依然不屈不降,在澤連斯基向全世界宣佈自己與首都共存亡後,揭開了烏克蘭奮力抵抗惡魔的史詩。而在彼方的莫斯科,依然繼續著燈紅酒綠,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仍在,在普京和國家機器的操持下,敢於發聲站出來的人都會遭到嚴厲懲罰甚至消失。 (閱讀更多)
【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偶像的醍醐味
初接觸防彈就注意到Jin的人大概不多,查映嵐分享自己對偶像的喜愛,由此談及這種職業的心理質素要求之高,而她對這些偶像的最大想望亦只有一個:願他們有一天能夠做回毋須被誰仰望的普通人,得到那些普通的、微小的哀愁與快樂,身邊有普通地愛著他們的人。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