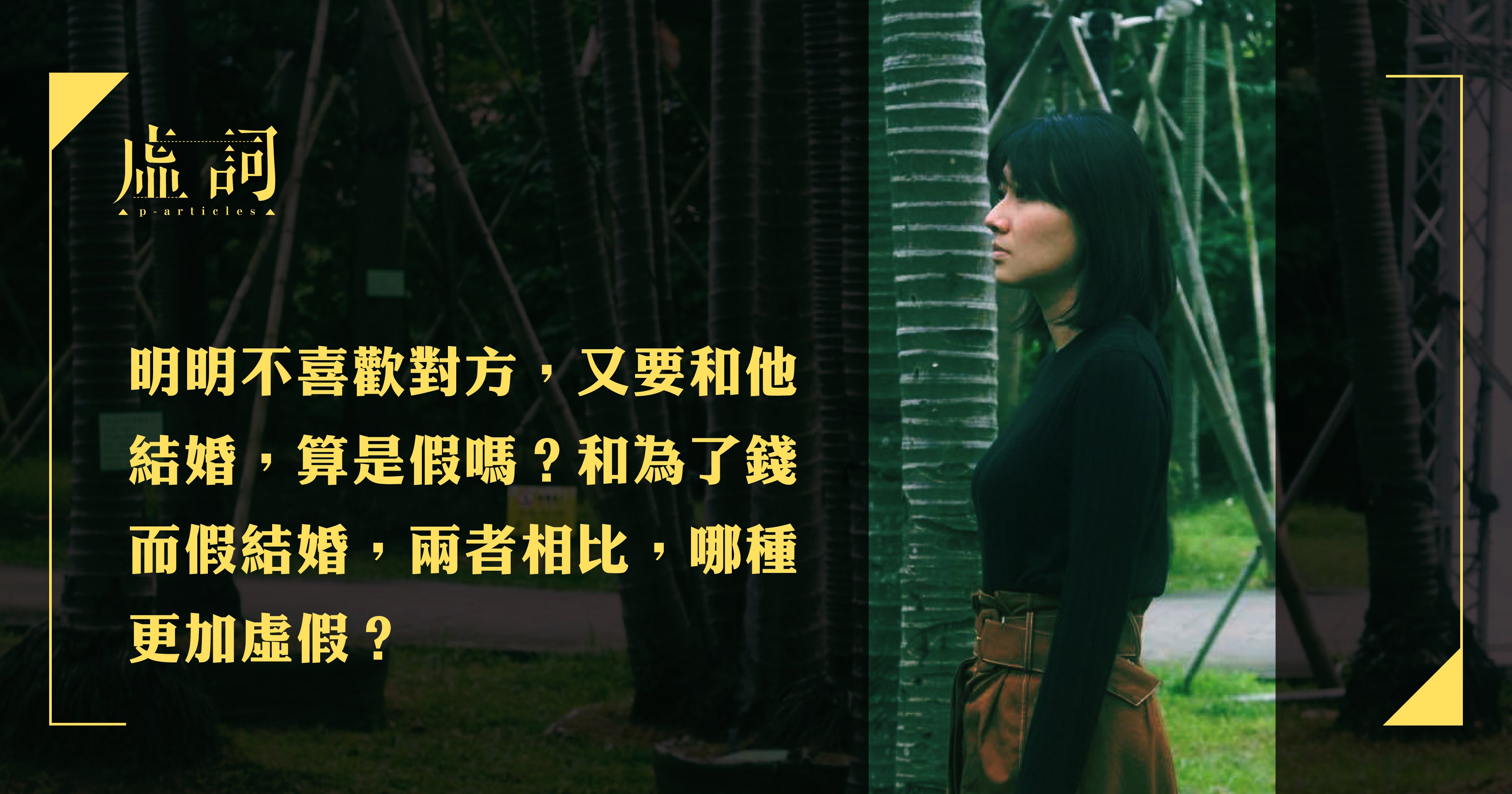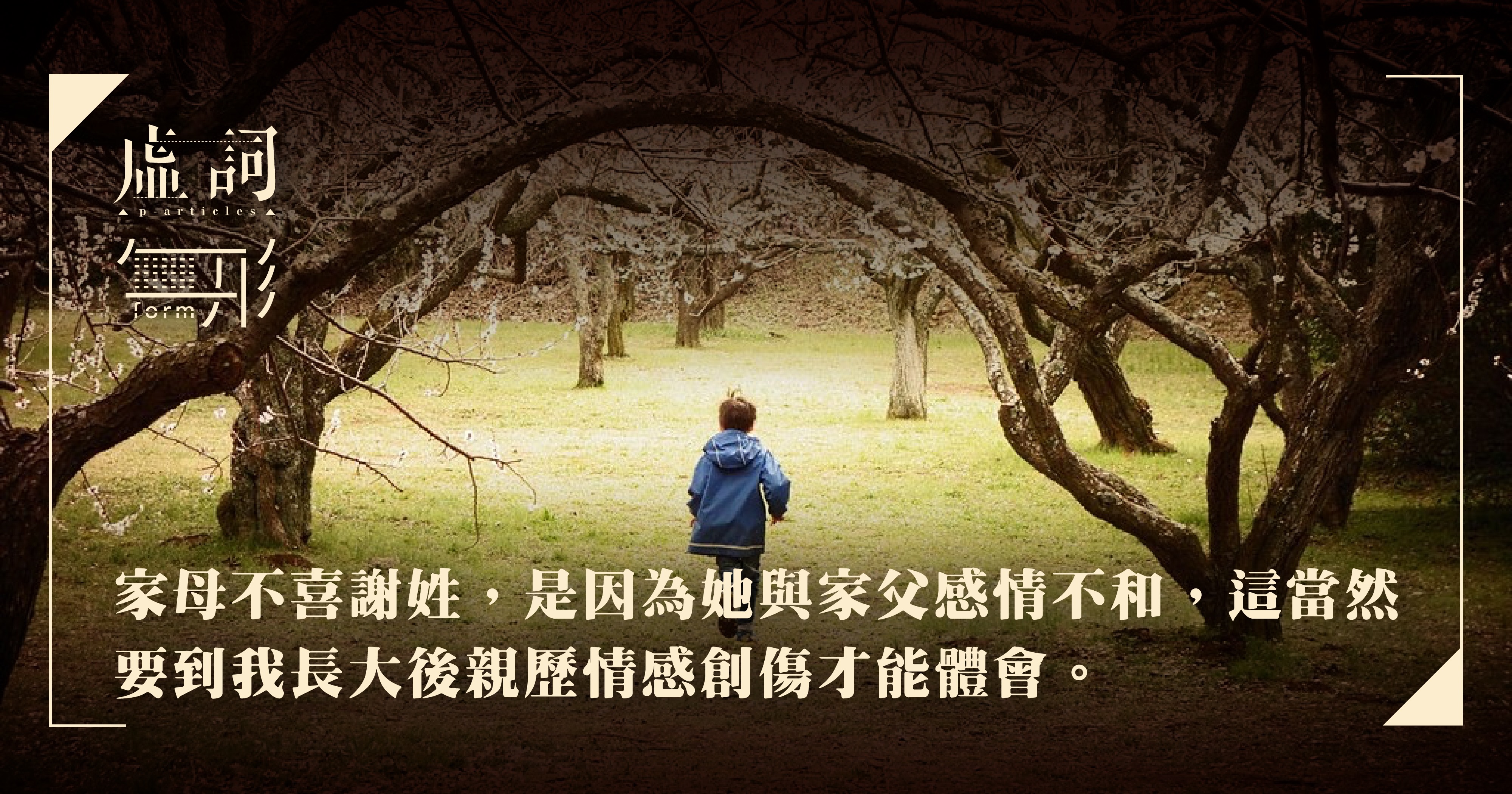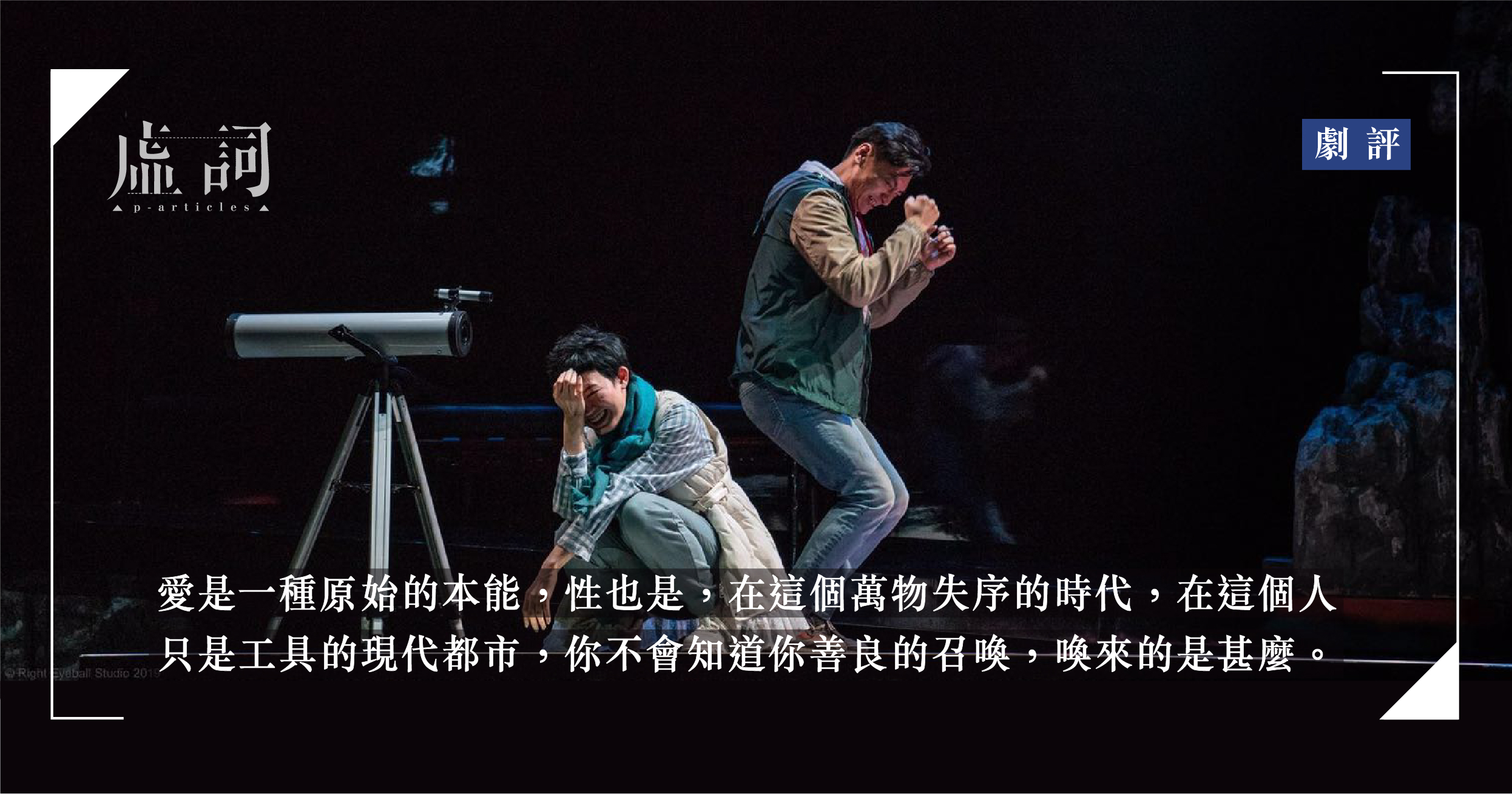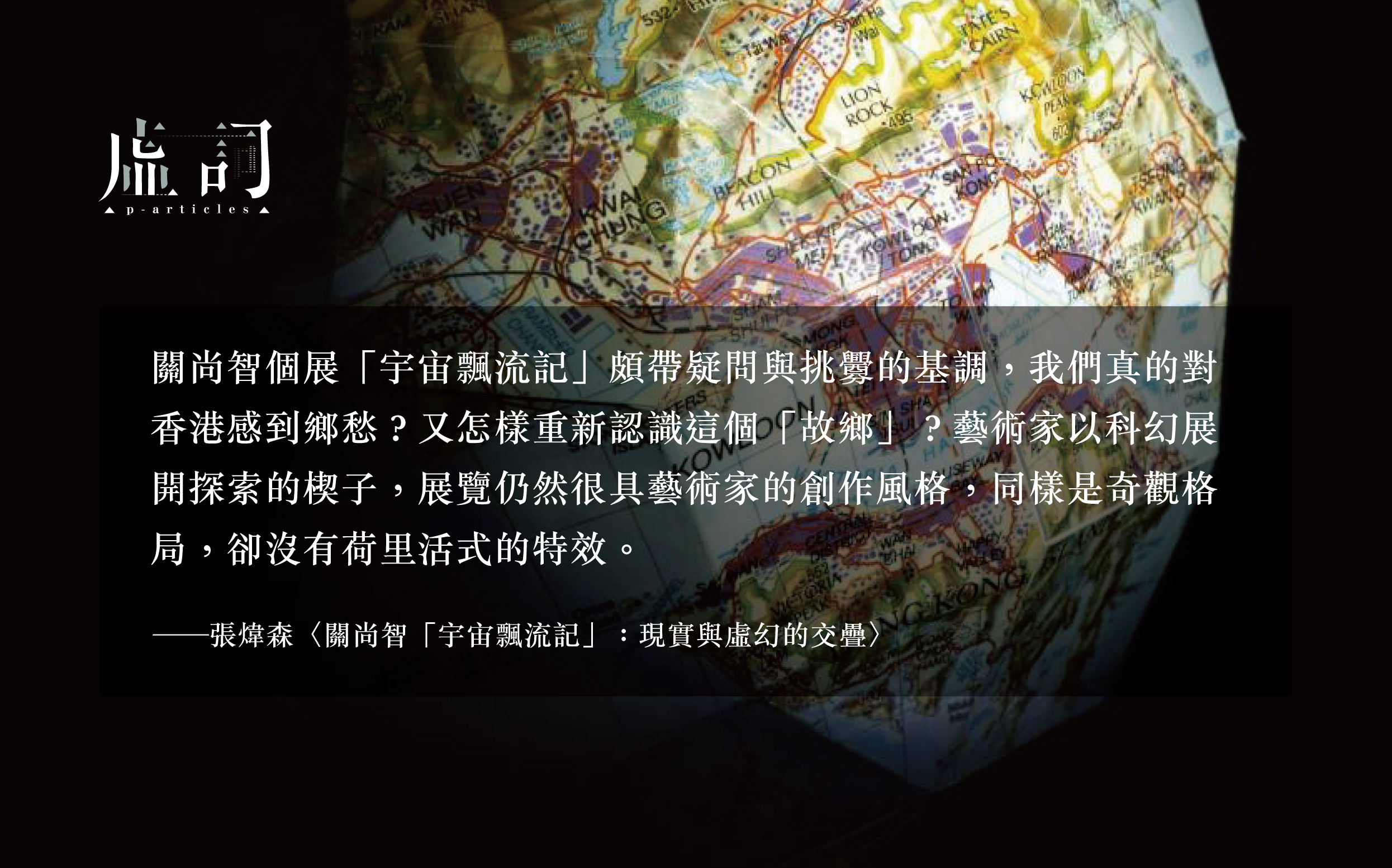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身份"

《旅行的意義》觀後感:寫一個關於幸福的故事
影評 | by 王駿業 | 2026-01-14
王駿業傳來《旅行的意義》影評,指出導演三宅唱透過「夏日虛構」與「冬日現實」的雙重結構,折射出在日韓裔女編劇的邊緣身分與創作焦慮。王駿業認為旅行作為窺探與被看見的權力遊戲,同時象徵與他者相遇的可能性。同時電影亦有著死亡(memento mori)的隱喻,透過細膩的光影與聲音捕捉「期間限定」的風景。所謂「幸福的故事」並非僅在於情節,更在於如何講述;唯有開放感官、沉浸於當下的細節,才能在虛無中體會到真正的「生存的實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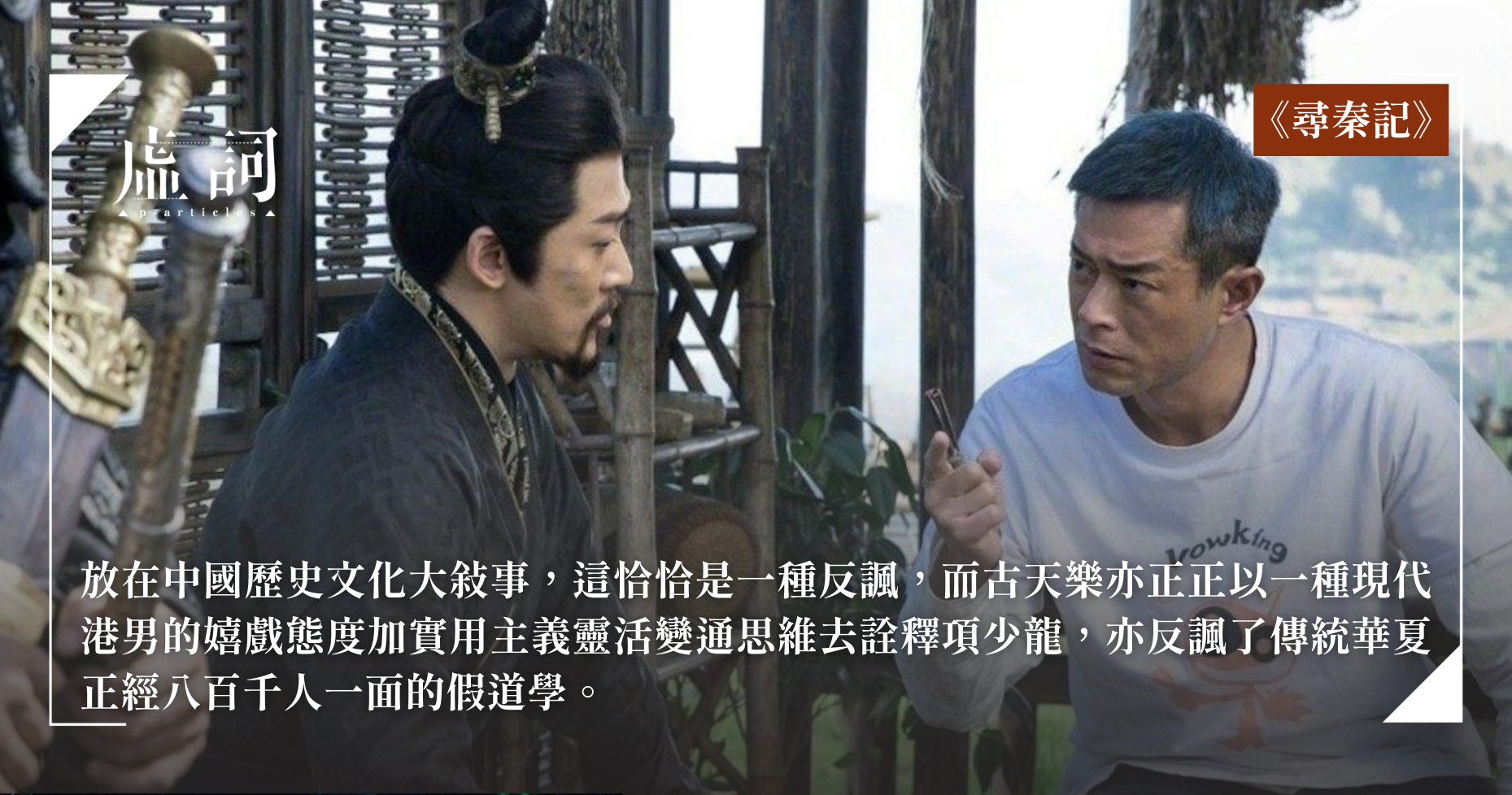
尋秦?避秦!港人視角的中國歷史
時評 | by 易山 | 2026-01-13
《尋秦記》電影版上映掀起全城熱話,令香港頓時掀起一片「尋秦熱」。易山藉此探討其超越流行文化回憶的深層意涵,包括香港人對千禧年代本土文化的懷念,以及集體潛意識中對身份認同的前世回溯。易山更從大歷史角度切入,將項少龍喻為香港:以靈活變通的港人特質介入大中華敘事,曾如太傅般傾力輔佐國家發展,最終卻由「尋秦」淪為「避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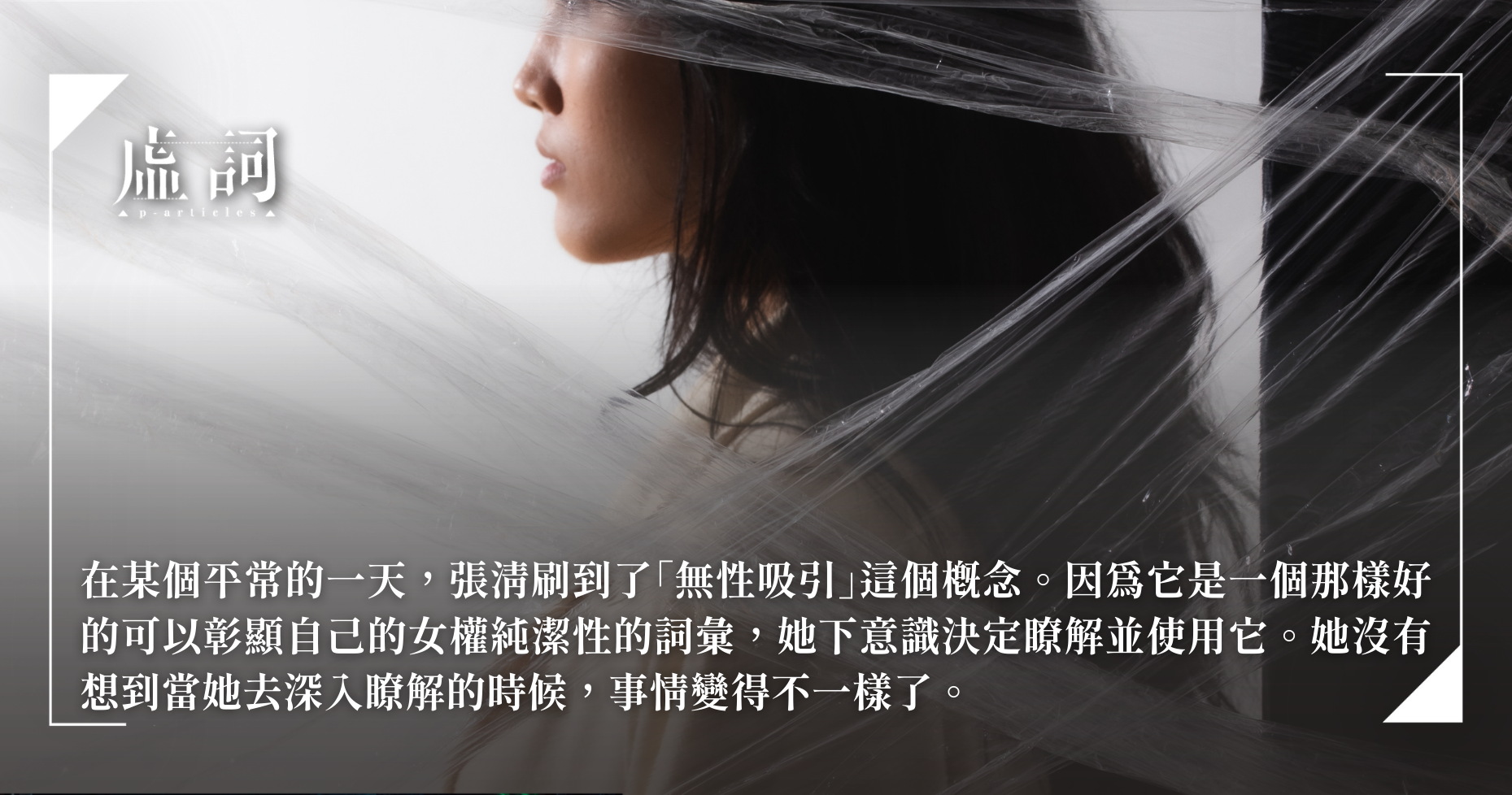
對「自我」的爭奪
小說 | by 苦橙蒿 | 2025-12-25
苦橙蒿傳來小說,書寫張清作為一名普通女性,置身於充滿社交媒體與文化活動的環境,感受到自我認同的疏離與焦慮。她從表面模仿他人姿態,逐步深入探索性取向、無性吸引及酷兒身份,經歷嫉妒、反思與混亂的歷程。張清在詞彙爭奪與身份標籤中尋求歸屬,卻面臨真實歧視、內心衝突與虛無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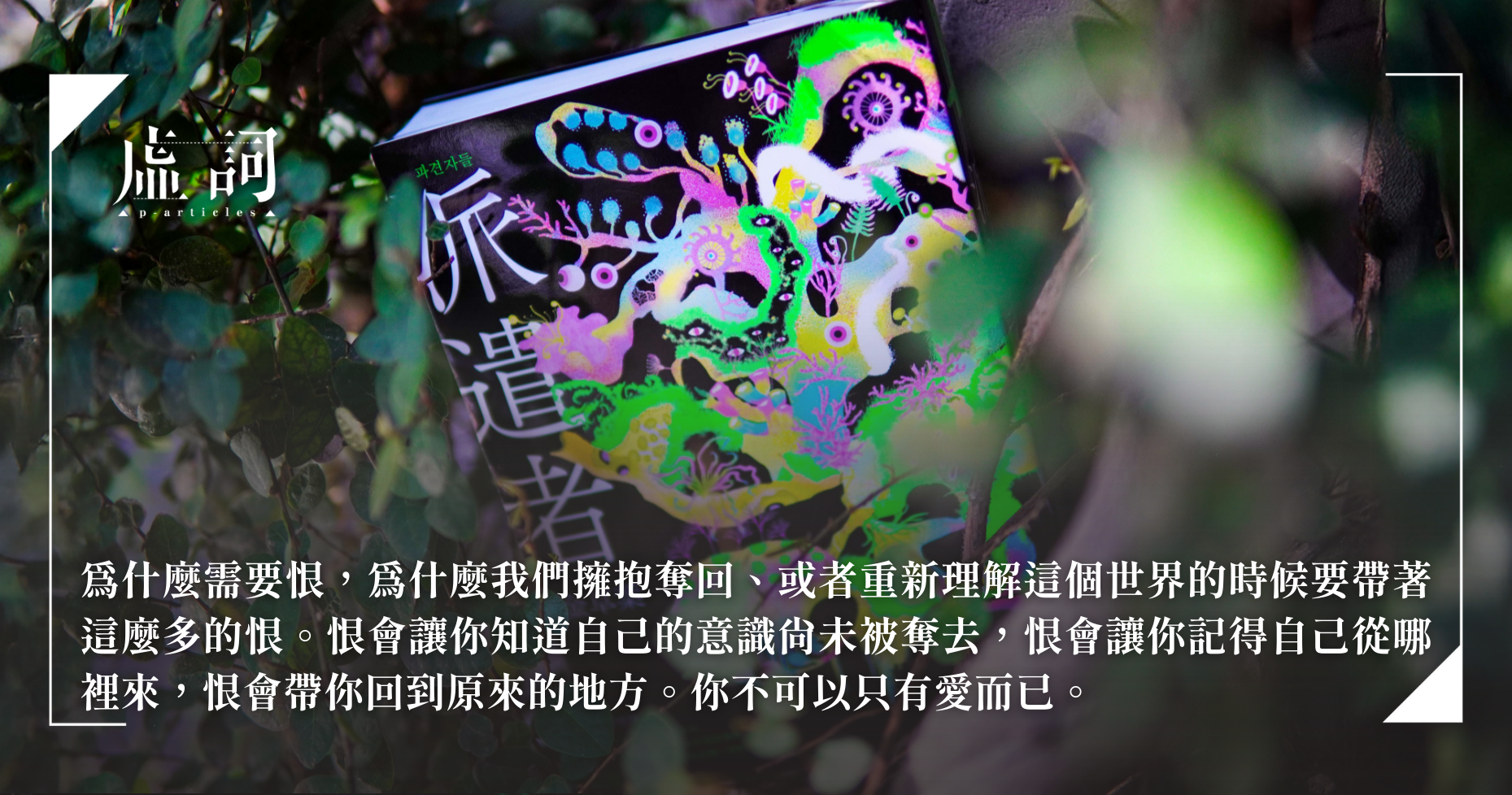
軟科幻的魅力與強悍:只有愛不夠,你必須恨——讀金草葉《派遣者》
書評 | by 郝妮爾 | 2025-11-24
郝妮爾讀畢韓國作家金草葉新作《派遣者》,認為其是她集過往靈光與意志於一身的重要長篇小說。《派遣者》雖以人類對抗外星「氾濫體」的末日戰爭為背景,實則探究著共生、身份與意識,人類何以為人的哲學命題。郝妮爾指出閱讀此書不僅需愛其強大包容,還須恨其挑戰人類個體性,皆因金草葉以小說提出只有愛不夠,人類要以恨記住自己,才能保有自我與回歸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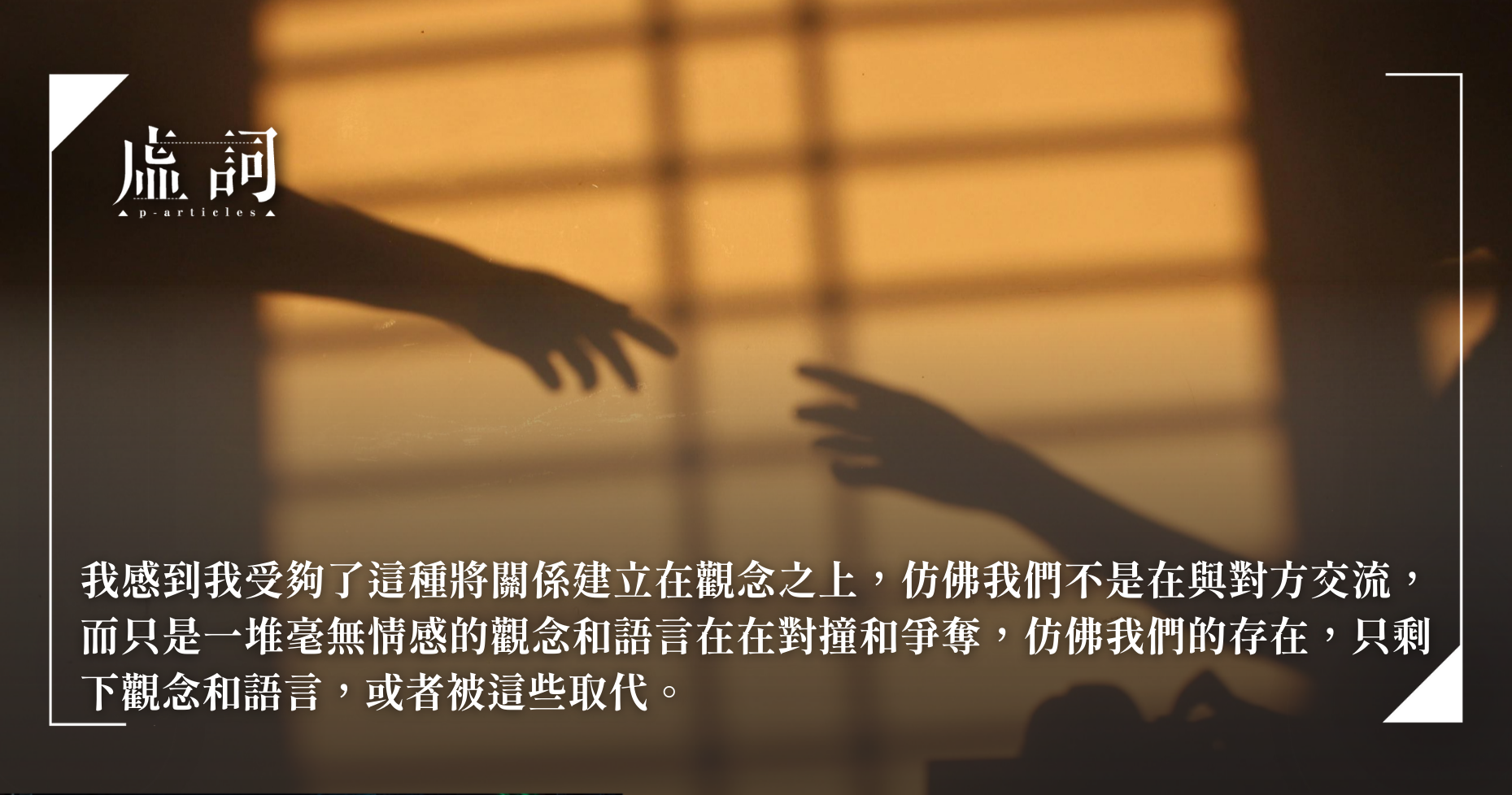
當代的某些關係
小說 | by 苦橙蒿 | 2025-09-19
苦橙蒿傳來小說,書寫「我」作為一名對外貌與身分認同感到焦慮的無性戀酷兒,身處在保守的城市中感到格格不入,既厭倦了交友軟體,也對線上社群中基於觀念的激烈碰撞感到疲憊。就在放棄社交之際,他認識了短暫返鄉的之格,在對話之中讓「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被理解、接納與溫柔。

歷久常新的經典:重新細讀也斯《剪紙》
書評 | by 陸裕欣 | 2025-05-08
陸裕欣近日重讀也斯小說《剪紙》後,認為小說透過主角喬和瑪瑤的故事,揭示香港人在中西文化交匯下的身份認同困境與回歸前的浮城焦慮。喬偏向西方,沉浸於《紐約客》與梵高裙子,卻無法擺脫不中不西的迷失;瑤執著傳統,剪紙刻畫虛幻的中國文化,卻與現代香港格格不入。兩人精神的不穩—喬與牆上紅鳥互動、瑤幻想的唐,均在魔幻現實主義的渲染下,折射出香港社會的多元與不安境況。

撓腳
小說 | by 姚金佑 | 2025-03-21
姚金佑以「撓腳」為題傳來微型小說。「他」每天都在公園閑坐,並不斷撓著的腳底的硬塊,終將成爲麻木的死皮。「他」不斷撓,撕下,就像撕下「他」的這些過往,掉在地上,混在塵埃裏。即使被人斥訓,「他」也不管,更在「撓腳」的途中,突然回憶起小時候的往事。

《看我今天怎麼說》:隨時隨地揀你舒適空氣 ——訪導演黃修平 演員鍾雪瑩 吳祉昊
專訪 | by 姚嘉敏 | 2025-02-20
以兩隻手指指向眼睛,雙手手掌向天作出上下擺動的動作,然後右手穿過呈半圓狀的左手並開出一朵小花,最後伸出食指左右搖擺,這是《看我今天怎麼說》的手語,故事以聾人的角度出發,講述三位聽障青年因生命中不同的選擇而走上不同的道路,並形成各異的生命態度,最後因手語而相聚,通過三人的相處和故事引伸出不同的討論。戲中的三位主角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群體﹐戲中的三位主角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群體﹐子信(游學修飾)以聾人為榮,以手語作為主要語言;素恩(鍾雪瑩飾)則從小被母親要求學口語,並禁止用手語﹐以便融入所謂的主流社會; Alan (吳祉昊飾)游走在兩者之間,成為兩者之間的橋樑。黃修平指在修修改改的過程中,自己盡量去蕪存菁,向觀眾呈現最好的作品,亦對成品十分滿意;吳祉昊指出現實聾人面臨的是一個魚與熊掌的局面,值得大眾關注;鍾雪瑩則透過劇中得悉:「聾人文化嘅身份認同不是單一的。你可以用助聽器、可以用人工耳蝸、可以淨係用手語、可以淨係識口語、可以對文字理解無咁深入,但都可以全部都識。」正如電影主題曲 “ What If ” 的結尾所言,相信每個聾人都只是想「可以選,我選自由自在」。

現象級小眾電影《香港四徑大步走》 熱血跑山且土地熱愛 反映港人身份認同感更強 藝術家馮美華、影評人李照興點評
影評 | by 馮美華, 李照興 | 2025-02-18
紀錄片《香港四徑大步走》於2025年1月上映,由Robin Lee執導,Lost Atlas製作。該片以全新視角拍攝香港四條主要遠足徑——麥理浩徑、衛奕信徑、鳳凰徑及港島徑的壯麗景色,並紀錄著「香港四徑超級挑戰」(Hong Kong Four Trails Ultra Challenge,簡稱HK4TUC)這項極限運動賽事。上映至今,電影票房已突破800萬港元,躍升為香港電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紀錄片。電影不僅讓觀眾切身感受越野跑手的艱辛與堅毅,更使這部原先被視為小眾的電影,意外引發全城熱議。虛詞編輯部成功邀請藝術家馮美華及文化評論人李照興點評現象級小眾電影《香港四徑大步走》。

離散時代再思香港身份:新讀李宇森,舊憶阿巴斯
書序 | by 羅永生 | 2025-02-01
筆者在2020年首次為李宇森的新書《主權在民論》寫推薦序,繼後在2022年,他接著出版了《主權神話論》。今年2024,李宇森又推出新著《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短短四年之內,作者已迅速完成了「否想主權三部曲」的系列,證明了他用功之深,涉獵之廣,實在可喜可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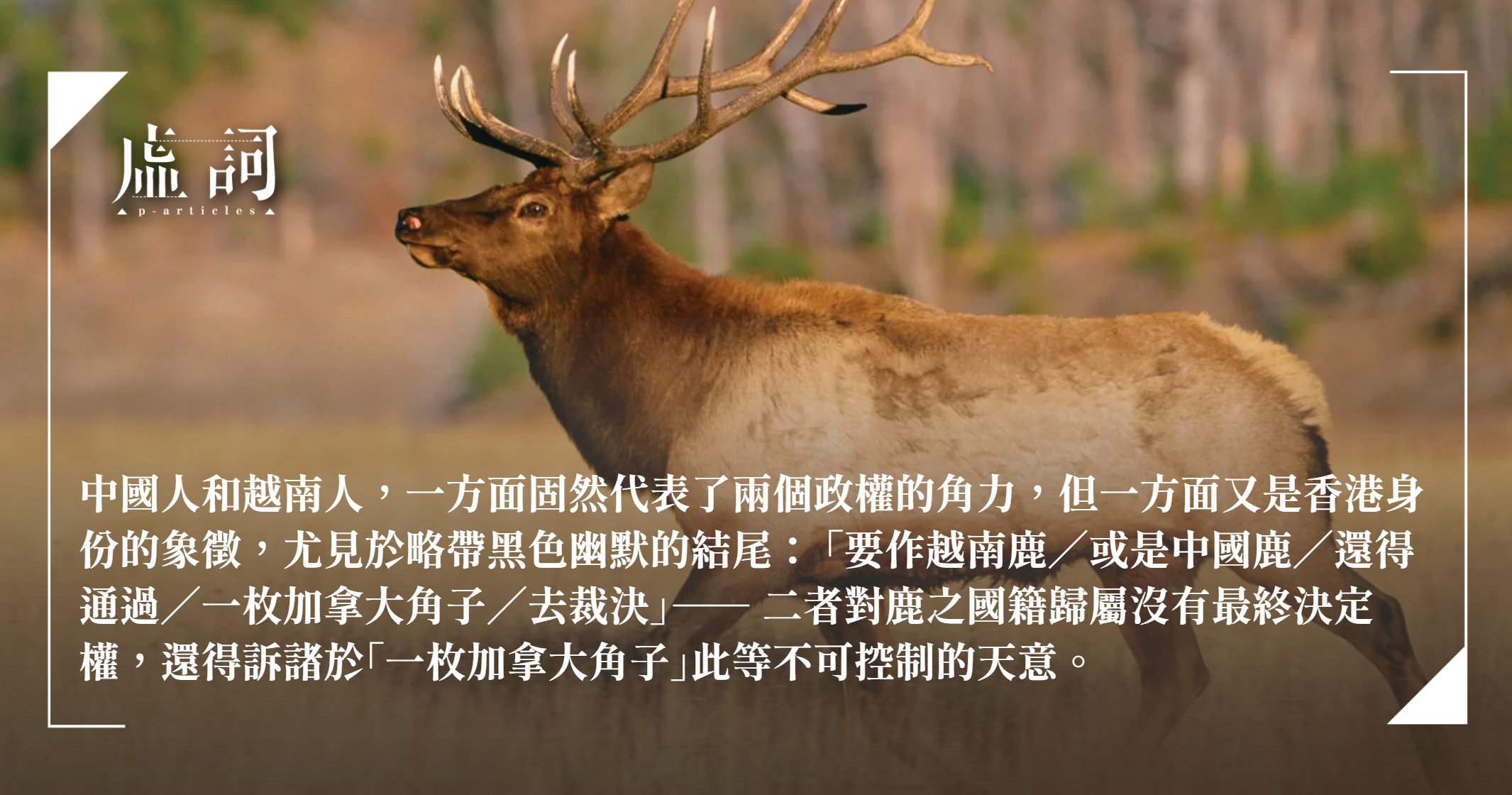
邊緣與混雜:淮遠〈加拿大鹿〉的身份書寫
評論 | by 麥子 | 2024-05-18
香港身份問題,一直是本地文學歷久不衰的主題,又以上世紀回歸前夕的80年代尤為盛行。麥子以淮遠的〈加拿大鹿〉(1983)為例,展示當中香港身份建構具有「邊緣」和「混雜」的特質,及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無力感,而淮遠對香港身份在殖民體制下的反思,為後來建立主體的文化解殖運動奠定基礎,也是一個時代變遷的印記。

訪《手捲煙》導演陳健朗:「手捲煙除了是一種態度,亦是一個情義的象徵。」
專訪 | by 姚嘉敏 | 2021-06-28
「捲一手,點一口」——比起成煙,手捲煙更為浪慢,一捲一黏,一呼一吸,在吞雲吐霧之間,可以放慢自身速度之餘,亦是情感的交流。電影以「徘徊迷陣,寄霧重生」八個大字作為口號,利用煙作為引旨並貫穿全劇,道出關超與文尼之間的情義,並透過同樣身處於裂縫之間的二人,引伸出身份認同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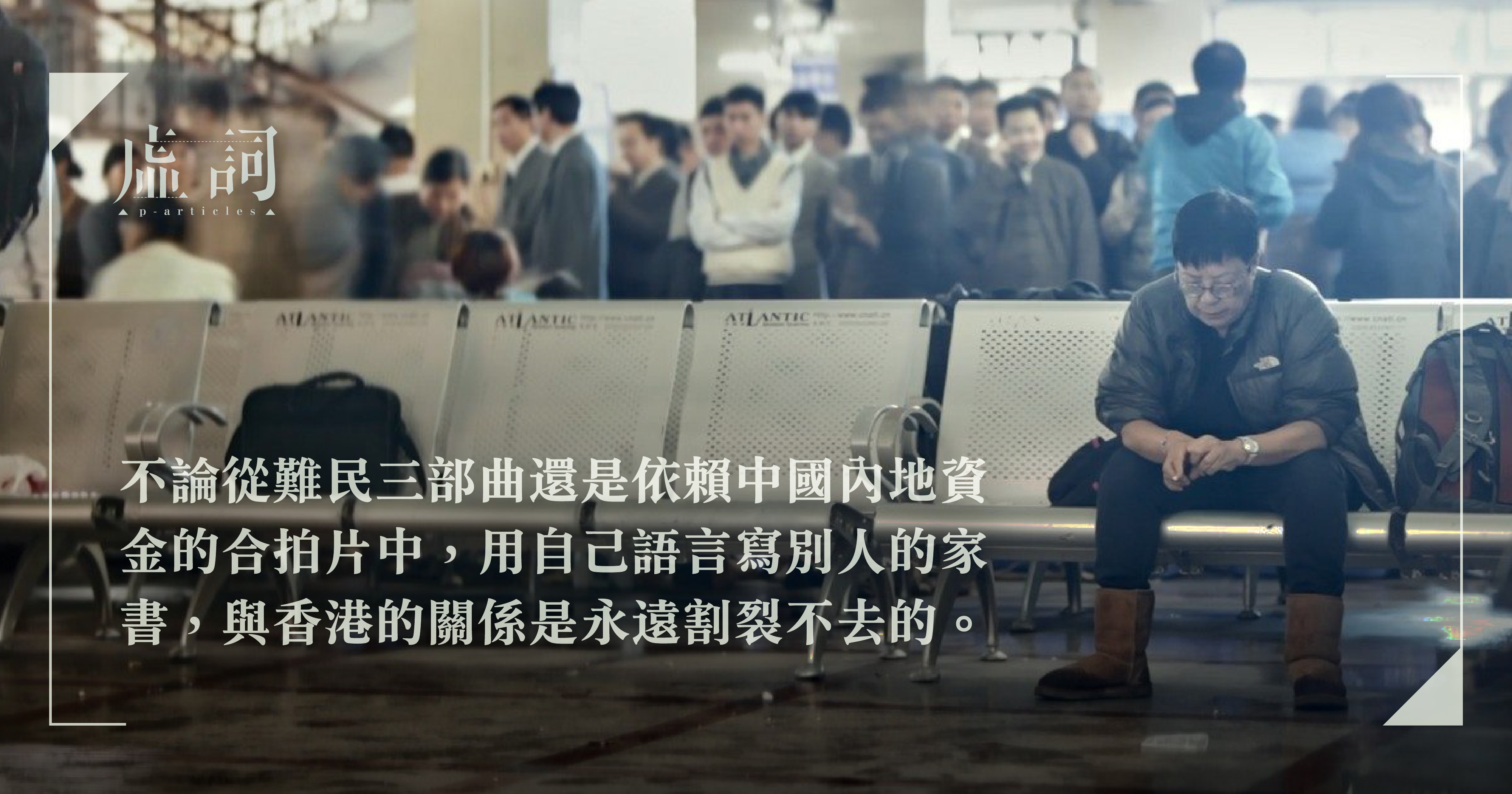
無垠的根:《好好拍電影》與香港身份
影評 | by 藍筠雅 | 2021-03-23
文念中執導的許鞍華紀錄片《好好拍電影》,正好為其四十年的電影人生作一總結。許鞍華的電影從來不易梳理,而在多年好友文念中的鏡頭下,除了關注社會議題與人文精神以外,更挖掘她在香港長大的童年,與祖父、父親、友人在於古詩、武俠電影與文學的淵源。

漂流、實地與開放,香港人未來的攻守策略——羅貴祥 X 沈旭暉「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講座紀錄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12-17
香港人近月總被移民、送機、簽證之類的事物圍繞,上月舉行的「香港文學季2020」講座,邀得身兼學者及作家的羅貴祥,與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教授,以「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為題,探討在地和海外港人,身處當前的歷史轉折位置,如何能讓身份認同得以保留並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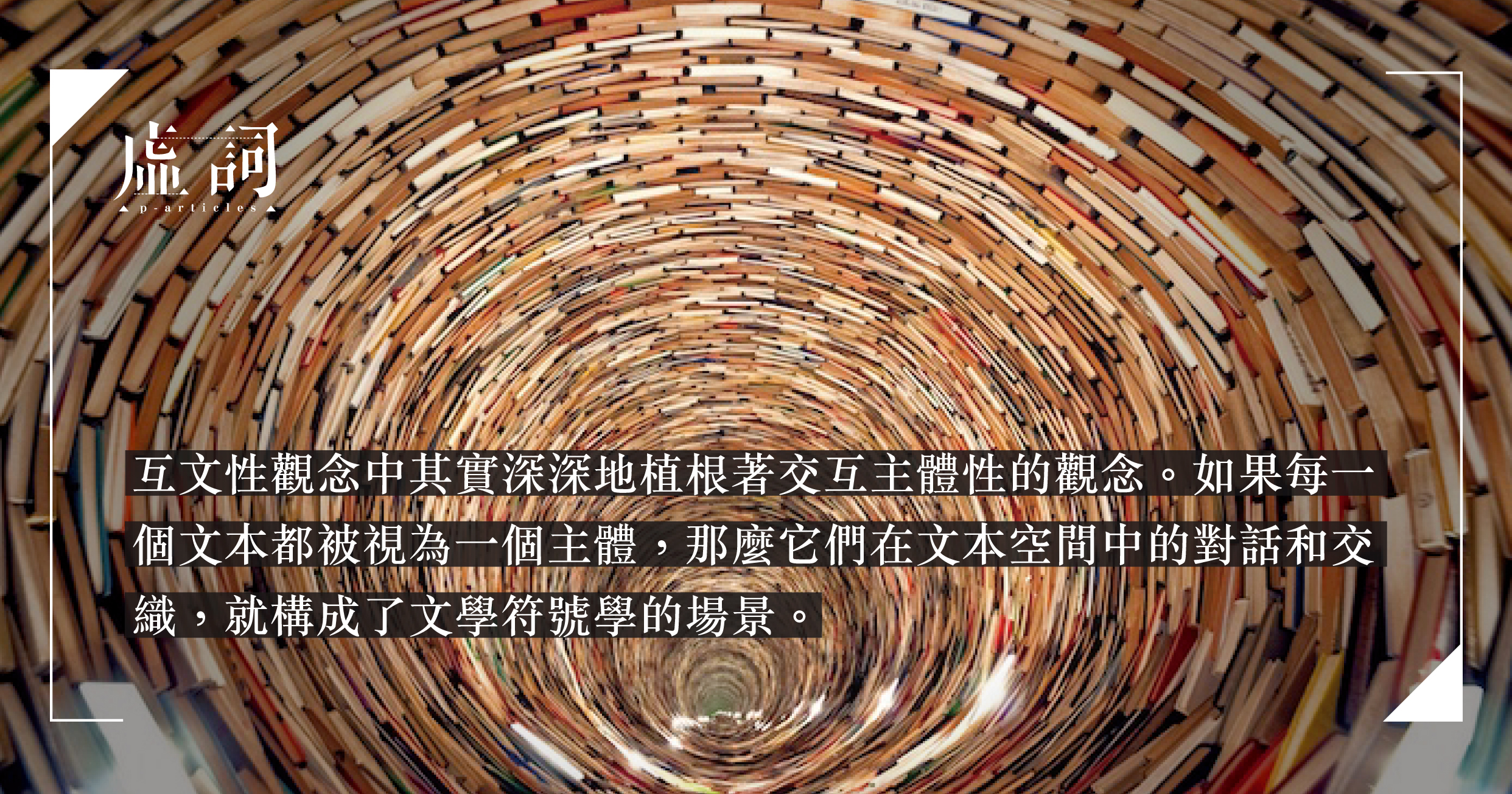
從互文性到「邊緣」文學的自主性——劉吶鷗引用穆杭的三個例子
理論 | by Sabrina Yeung | 2019-01-05
如果我們用互文性的理論來看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對法國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別是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對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劉吶鷗如何利用這些由接受所帶來的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或創造性轉化,然後再進一步思考所謂「邊緣」的文學區域,如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如何可以加強自己的著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