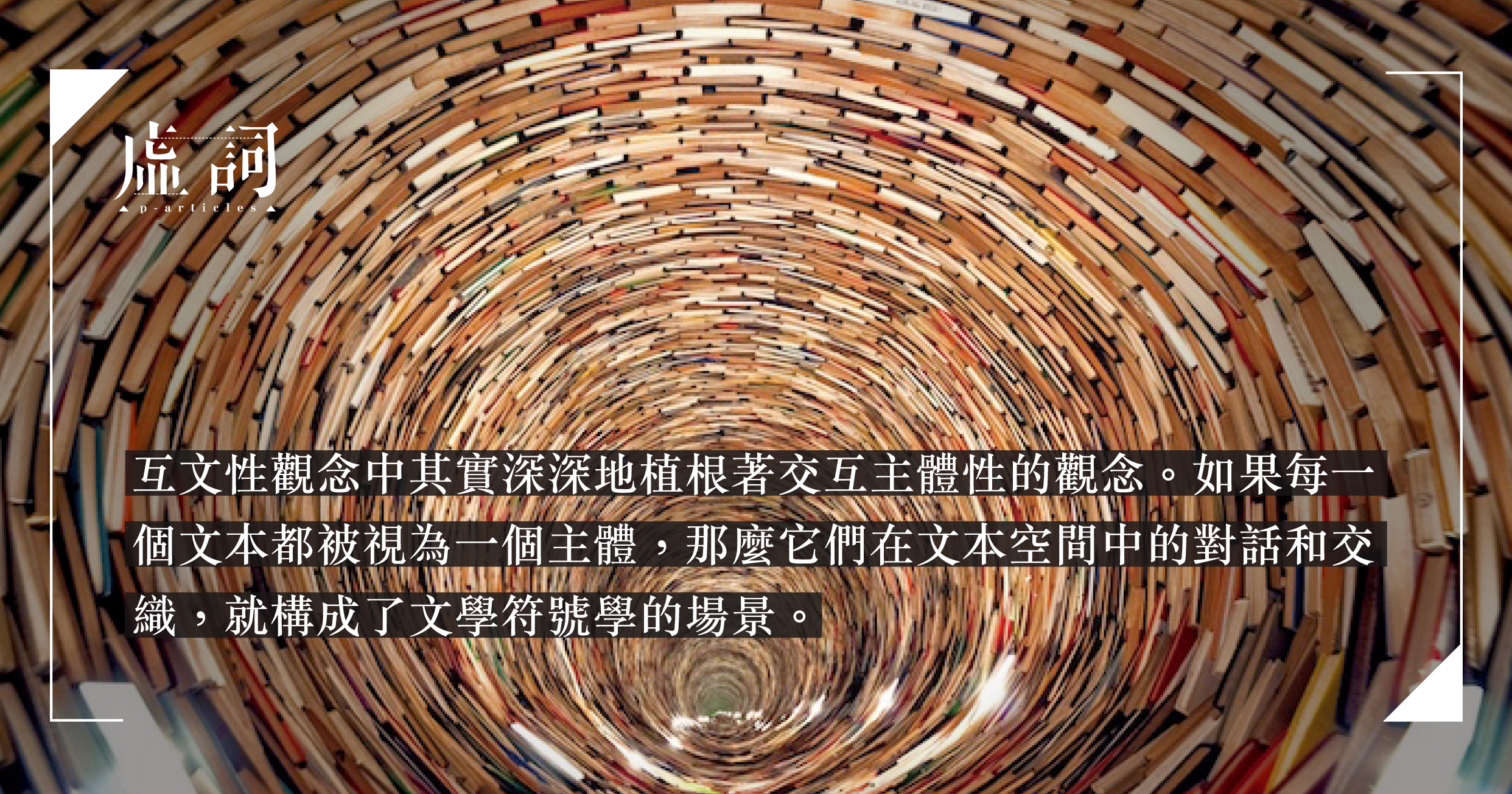從互文性到「邊緣」文學的自主性——劉吶鷗引用穆杭的三個例子
理論 | by Sabrina Yeung | 2019-01-05
透過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1960年代中一系列重要的評論文章,如〈巴赫金:詞語、對話與小說〉(Bakht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1966)和〈受限制的文本〉(Le texte clos, 1966-1967),互文性(l'intertextualité)一詞進入了法國學術界[1]。在第一篇文章,克莉斯蒂娃如此定義互文性:
橫向軸(作者──讀者)和縱向軸(文本──語景)重合後揭示了一個事實:一個詞(一個文本)是另一些詞(另一些文本)的交錯和會合,我們從中至少可以讀到另一個詞(另一個文本)。在巴赫金的理論中,他分別稱這兩支軸為對話(dialogue)和語義相關(ambivalence),但他沒有清楚地區分兩者。然而,就是因為巴赫金沒有嚴格地區分兩者,這反而令他是第一個在文學理論中提出:任何一篇文本的構成都如同一幅語錄彩圖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轉化了別的文本。[2]
互文性
克莉斯蒂娃吸收了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然後進一步發展她自己的互文性理論──「一個文本是另一些文本的交錯與會合」,用以顛覆社會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個體意識的單一性和文本內部意義自足的觀念等。[3]
其實在克莉斯蒂娃創造「互文性」一詞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論家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已運用了互文性的理論。巴特認為,雖然我們有自由選擇不同的書寫方式,但其實我們每一次寫作都是在回應以往的寫作,包括前人的書寫或自己以前的書寫。而每次寫作都令我們腦海中的某些編碼連繫著另外的編碼,寫作過程中也因而帶著文本互涉的效果。1970年,巴特出版了S/Z,於其中,他更明確地把文本分為兩類:可讀的文本(le lisible)和可寫的文本(le scriptible)。可寫的文本為讀者提供複性的意義,因此具有可寫性,因為每位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皆重寫了這個文本。相反,可讀的文本就不具有這種重新再寫(re-écrire)的可能性,因為它只停留在某一意義內就凝滯不動了。[4]
除了克莉斯蒂娃和巴特外,其他重要的理論家如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里法特爾(Michael Riffaterre, 1924-2006)、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 )、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 )、卡勒(Jonathan Culler, 1944- )等,對互文性理論也建樹甚多。雖然他們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分歧也不少,但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建構了互文性的核心思想:所有語言符號都在回應著以前的論述和已然存在的意義樣式,回應的同時,它們又擴大了這些意義樣式的內涵;所有思想和傳統都可以合法地成為文本的一部份;一個文本可以通過新的閱讀而產生別的聯想。
如果我們用互文性的理論來看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對法國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別是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對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劉吶鷗如何利用這些由接受所帶來的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或創造性轉化,然後再進一步思考所謂「邊緣」的文學區域,如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如何可以加強自己的著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
劉吶鷗三個引用穆杭字句的例子
一個文本的旅行一般要從影響研究開始,要讀者首先意識到在文本內,有一個外來元素(alien element)影響著文本的構成,所以我們先看三個劉吶鷗曾直接引用穆杭作品字詞的例子:
| 穆杭作品 | 劉吶鷗作品 |
On s'attendrit sur la vague de paresse,
〈懶惰底波浪〉 我們軟洋洋地伸在那懶惰的波浪上, |
任那車體舒服地搖動著,自己浸在懶惰的波浪裡。 |
Daniel trouvait à la Hollandaise la peau saine et
〈茀萊達夫人〉 但尼爾在那荷蘭女身上發現了一身健康的皮膚和一雙 |
(《劉吶鷗小說全編》,頁3) 〈風景〉:她那個理智的直線的鼻子 |
|
不曉得幾時背後來了這一個溫柔的貨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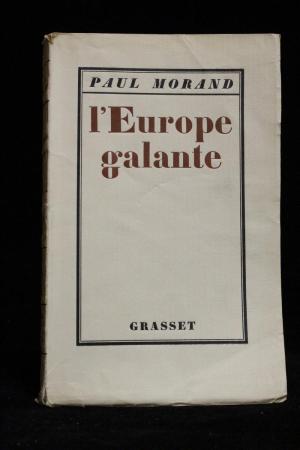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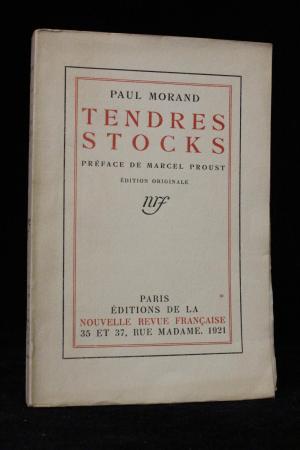
穆杭的作品《優雅的歐洲》(左)和《溫柔貨》。
〈懶惰底波浪〉是穆杭作品《優雅的歐洲》(L'Europe
galante, 1925)中,其中一篇短篇小說的標題,這個短句也曾出現在小說裡,劉吶鷗於〈禮儀與衛生〉中引用了「懶惰的波浪」這個句子。《優雅的歐洲》另一篇作品〈茀萊達夫人〉曾用「沒有理智」來形容一名荷蘭女子的乳房,而劉吶鷗就引用了「理智」來形容筆下兩篇作品的女主角:「理智的前額」和「理智的直線的鼻子」。最後,從「不曉得幾時背後來了這一個溫柔的貨色」這一句,可以看出劉吶鷗在〈兩個時間的不感症〉中引用了穆杭第一本短篇小說結集《溫柔貨》的標題。
這三個引用作為外來元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劉吶鷗作品的構成。第一個引用:「任那車體舒服地搖動著,自己浸在懶惰的波浪裡」,「懶惰的波浪」的引用只是單純地用作描述主角比較輕省的狀態,即使沒有穆杭作品的指涉參照,讀者也能明白句子的意思。
第二個引用,〈遊戲〉的「這個理智的前額」和〈風景〉的「她那個理智的直線的鼻子」兩句,「理智的」被引用來形容女主角的身體器官,但甚麼是理智的身體器官呢?這顯然不是從字面意思便可以明白的句子。讀者要回到穆杭作品的語境,才能理解到「一雙沒有理智的乳房」,表達的其實是像穆杭這樣的浪蕩子,既愛女人的肉體,又覺得女性沒有智性思考能力的狀態。根據彭小妍的觀點,浪蕩子對女性有獨特的看法,他們一邊迷戀女性的身體,一邊「認為只有男性才有智性思考及表現的能力,而女性只能縱情色慾,利用男人來滿足其性需求,毫無智性發展的可能。[5]」事實上,〈茀萊達夫人〉中的同名女主角,在奧林匹亞劇場偶遇男主角後,一直尾隨男主角,然後主動約男主角去吃晚飯,並提出性要求:「你會給我有無上的快樂﹝……﹞我住在格拉里季旅館,因為那裡可以得到一間很便宜的房間。來罷。[6]」茀萊達夫人喜歡的是一些很媚俗的東西,如人造珍珠、玩具喇叭和發聲糖果。根據男主角一句語帶諷刺的描述,這是「一個外國人可以在巴黎所要的東西」[7]。所以,於作為浪蕩子的敍述者眼中,「一雙沒有理智的乳房」正好綜合了茀萊達夫人縱情色慾,但就沒有智性、品味媚俗的特徵。然後,我們以此詮釋來看劉吶鷗的句子:「理智的前額」和「理智的鼻子」,前者是形容探戈宮中一名女子(〈遊戲〉),後者是形容火車上一名有夫之婦(〈風景〉),這兩個引用了「理智」的摩登女性,她們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智性、主導權和表現能力,至少在兩性關係的層面上。所以理智的身體器官指向的是故事中的女子打破了男子的想像,擁有一定程度的智性思考能力、品味卓越,於兩性關係中有一定的主導權。
以上兩個引用,第一個是純修辭層面的引用,第二個屬於典故,要回到穆杭作品的語境才能理解到劉吶鷗的用例之背後含意。第三個引用就涉及一個雙重符號(dual sign),即字面意思和非字面意思的指涉。第三個引用,〈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裡「不曉得幾時背後來了這一個溫柔的貨色」[8]一句,「溫柔的貨色」字面意思指向一個女性化的女子,非字面意思就涉及穆杭《溫柔貨》裡三篇短篇小說中三名女主角的形象。《溫柔貨》第一篇故事中的女主角克拉麗絲(Clarisse)是一個倫敦的年輕製帽師,她對時尚有敏銳的觸覺,是一個活在當下的女性。第二篇的德爾菲娜(Delphine)性格反叛,她要追尋一種可以概括生命是甚麼的理念,但她參與了一場又一場的革命,與一個又一個男子結合後,最終墮落於吸毒,歸於虛無。第三篇的奧蘿爾(Aurore)和德爾菲娜一樣,也是一個對抗社會舊俗的女性,不過她的對抗方法是回歸自然,回歸身體操練。她追求的是斯巴達人式的樸實。這三名女性其實象徵著現代性的三個面向:克拉麗絲代表現代主義,即是對當下(l'actualité)和時尚的執迷;德爾菲娜象徵了虛無主義,根據馬爾勞(Malraux)的說法,那是因為上帝已死的緣故;奧蘿爾代表原始主義,即是對傳統、自然、身體操練的懷舊 [9]。劉吶鷗〈兩個時間的不感症〉的女主角,當然沒有完全包辦《溫柔貨》三名女主角的所有性格特徵,否則她就成了一個性格極其分裂的人。然而,當我們細讀劉吶鷗筆下這位女主角的形象:她穿「透亮的法國綢」,拿著「opera bag」[10],在1920年代的中國,這是時尚的表現;她周旋於兩名男子之間,其中一位還是一個在跑馬場剛認識的陌生人,這顯示出她反叛的性格,對社會陳規的蔑視;她是一個「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有「彈力的肌肉」[11],這代表了她可能有身體的操練。由此看來,〈兩個時間的不感症〉的女主角其實融合了《溫柔貨》中三位女主角某部份的性格特徵:時尚、反叛、運動型。故此,劉吶鷗這個引用,不僅是字面的意思,它還有一個深層文化的指涉──一個現代女性形象的指涉。而這個指涉,如果按《溫柔貨》的互文參照,它剛好象徵了現代性的三幅面孔:現代主義、虛無主義和原始主義。
創造性轉化與「邊緣」文學自主性
互文性理論顛覆了單一文本意義自足的觀念,令我們注意到一個文本在某種文化話語空間中的參與過程,如一個文本與其他語言,或它與一種文化的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之間的關係等。因此,這種研究方式與傳統的「影響──接受」研究有所不同,它開拓了文本的詮釋空間,因為它把那些無名的話語實踐、無法追溯來源的編碼均包含在內。更最重要的是,它給予後來的文本一份自主性。就如克莉斯蒂娃在定義互文性一詞時所指,互文性觀念中其實深深地植根著交互主體性(l'intersubjectivité)的觀念 [12]。換言之,如果每一個文本都被視為一個主體,那麼它們在文本空間中的對話和交織,就構成了文學符號學的場景。因此,後來的文本──同樣被視為構成對話的主體之一,就有了自主性。而因為這份自主性,後來的文本就不再只處於「被影響」的位置,而是一個可以利用種種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的文本。就如卡勒在〈前設與互文性〉(Presu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一文中說:
對互文性的描述會涉及最普遍和最重要的考慮:一個文本和各種語言或一種文化的論述實踐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個文本與為它表達出那種文化的種種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間的關係。互文性的研究並非如同傳統看法所認為的,是對來源和影響的研究;它的網撒得更大,包括了無名話語的實踐,無法追溯來源的編碼,而這些編碼正是後來文本種種可能性的必要條件。[13]
事實上,並非只有上海新感覺派的研究者,或者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需要思考這個跨文化場域中創造性轉化的問題,其他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如非洲文學,也在思考類似的問題。歐歌德(Ode Ogede, 1956- )於《非洲當代文學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Looking Inward, 2011)一書中,以互文性理論為論述框架,希望推翻以往非洲文學研究中常有的一個假設──非洲作家完全地「忠誠於」西方經典。他指出,非洲當代文學和非洲傳統文化與經典作品之間,其實仍有很多未被發掘的連繫。甚至,非洲當代作家與作家之間,也常在作品中互相質問、模仿並修改對方的情節。於是,非洲當代文學的不少作品裡,出現大量典故、互文性回應、戲仿、引用其他媒體等手法。歐歌德因此認為,從想像力的對話和互文的角度來看非洲當代文學,才能更深入地了解非洲作家的著作身份(authorship)[14]。
[1] 這兩篇文章後來收錄在1969年出版的《符號學:語義分析研究》(Sè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2] Julia Kristeva, Sè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 146.
[3] 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克莉斯蒂娃其實也參考了其他範疇的思想家的觀點,例如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和德里達的哲學思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政治科學,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精神分析和喬娒斯基(Noam Chomsky, 1928- )的結構語言學等。請參考María Jesús Martínez Alfaro, “Intertextuality: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In Atlantis, Vol. 18, No. 1/2, 1996, p.275.
[4] Roland Barthes, S/Z, Paris : Seuil, 1970, p. 19-21.
[5] 請參考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頁62。
[6] 法文原文請參考Paul Morand,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édition présentée,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Michel Collomb,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p. 421. 中文翻譯請參考保爾‧穆杭著、戴望舒譯:〈茀萊達夫人〉,《天女玉麗》,上海 :上海尚志書屋,1929年,頁90。
[7] 法文原文請參考Paul Morand,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p. 423. 中文翻譯請參考保爾‧穆杭著、戴望舒譯:〈茀萊達夫人〉,《天女玉麗》,頁93。
[8] 劉吶鷗:〈兩個時間的不感症〉,《劉吶鷗小說全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頁41。
[9] 請參考Bruno Thibault, L'Allure de Morand: du modernisme au Pétainisme, Birmingham (Ala.) : Summa publications, 1992, p. 14.
[10] 同注29。
[11] 同注29。
[12] 見注15。
[13] Jonathan Culler, “Presu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In MLN Vol. 91, No. 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c., 1976), p. 1383.
[14] Ode Ogede, Intertextuali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Looking Inward, Lexington Books, 2011, p. I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