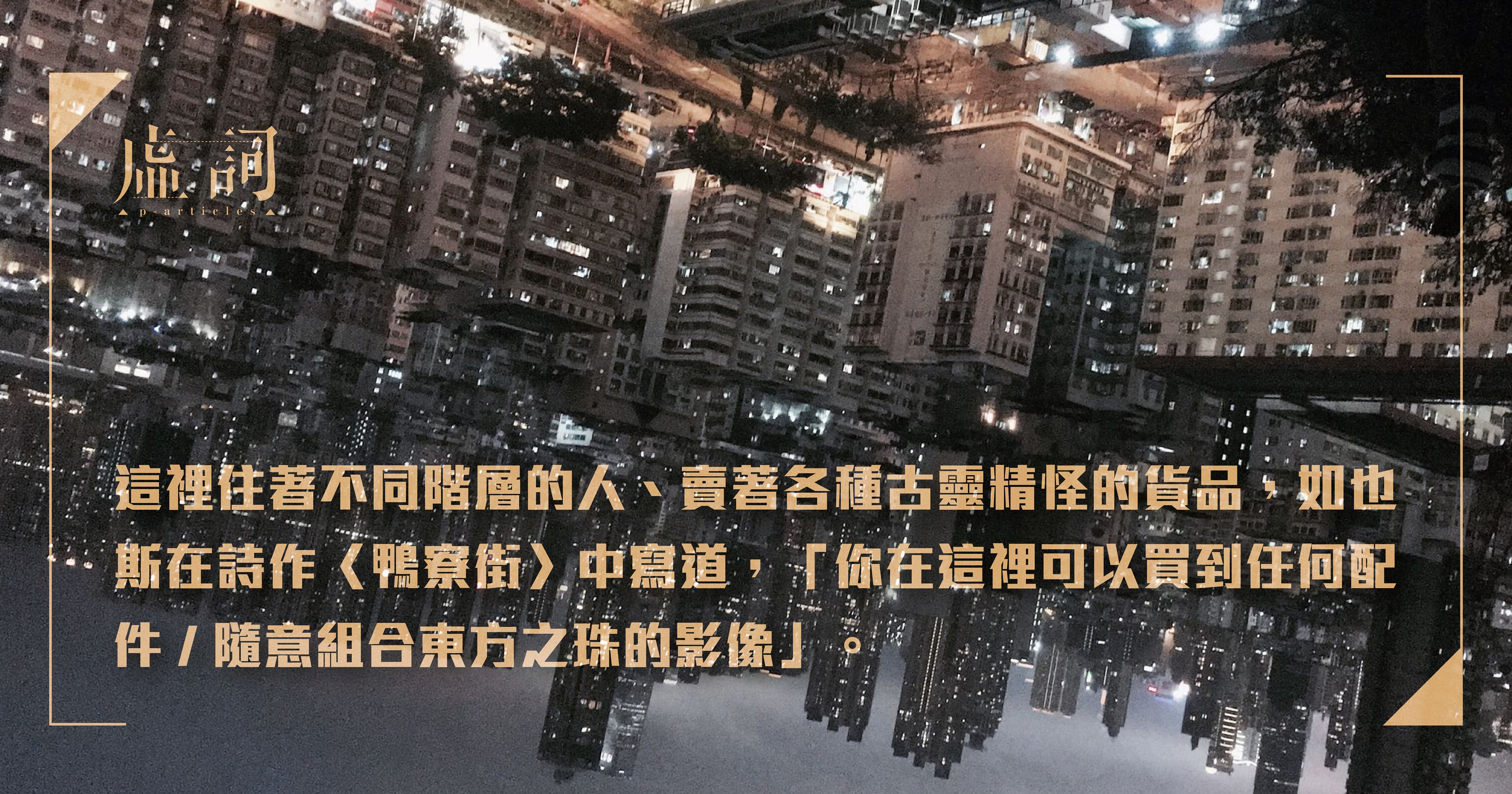【深水埗,我要進來了】居民談:Shamshuipo is the new 可能
為了避開城內沒能被消化掉的污穢,在深水埗行走時總難免注視地面。煙頭、垃圾、老鼠、路人手臂上黏糊糊的汗、或是往路邊吐痰的老頭那句中氣十足的「媽叉」:「傾偈行埋一邊啦!」,都彷彿是深水埗給人的印象。
唯獨在你抬頭時,你才會看到這是一個高低起伏的魔幻都市,在欽州街及荔枝角道交界,濃縮著數種不同面貌的樓房建築:弧形唐樓、敞廊式騎樓、私人樓宇、青年共居宿舍。這裡住著不同階層的人、賣著各種古靈精怪的貨品,如也斯在詩作〈鴨寮街〉中寫道,「你在這裡可以買到任何配件 / 隨意組合東方之珠的影像」。深水埗,本來就是一個意義繁雜的隱喻,也是一個可以說很久很久的故事。
深水埗的「非人」生活
1953年石硤尾大火,港英政府興建徙置大廈,標誌著公共屋邨的誕生,甄拔濤在深水埗的故事,便是於災後四年興建的蘇屋邨開始。出生在明愛醫院的他生於斯長於斯,一直對深水埗情有獨鍾,「蘇屋邨依山而建,自成一角,樓宇名稱清雅簡潔,一層共二十戶人家,每家每戶都各有特色,饒有趣味。」說到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小時候隔壁住著電視明星林嘉華,「當時蘇屋邨盛產明星,許冠傑、黃家駒便曾在蘇屋邨居住。」當然,不是人人都活得如明星般傳奇,但這裡的故事總是平凡又帶點奇情,就如當年每晚八時正,甄拔濤都會準時聽到一戶人家高聲叱罵兒子,原以為他會有甚麼童年陰影,但罵著罵著,又看到他平安無事地考上了大學。
四十多年前與丈夫住在石硤尾邨七層大廈的林女士,在深水埗居住的年代亦與甄拔濤相近,她的兒子亦是甄拔濤所言,考上了大學的幸運一群。她説那個年代住深水埗的人,現在大多安居樂業,「那時經濟起飛,不像現在這般艱難,全家七八口,個個都賺錢養家,生活環境很容易得到改善。」
然而新生代作家梁莉姿居於深水埗的故事,卻不如他們般美好。在深水埗住了十數年,由九十呎的唐八樓劏房到五六百呎的大單位,她都住過。唐八樓劏房是她住過最惡劣的地方,「八層樓梯全是老鼠,每次出門都會有一大堆老鼠爬出來。每逢下雨天就漏水,隔一陣子就爆屎渠。上網做功課只好到麥當勞,圍繞身邊的是麥難民,回家時又會看見滿街是露宿者,那時我便想,為何一個人會活得如此『折墮』?」
而饒雙宜在深水埗的故事雖然短暫,卻同樣「慘烈」。她只在深水埗短居一年,但於她而言已是一場心的修煉。因為每天出出入入,她看到的盡是慘事,例如道友大白天睡在馬路中心,精神病人在街上邊走邊駡,甚至在街市看到基層市民爭搶下欄貨。面對這些城市裡的血淋淋,心裡難過,她只好告誡自己:「深水埗是草根社區,你在這裡居住,就要學會接納它的好與壞。」
攝於深水埗大南街附近的小巷,梁莉姿她說頭頂的棚架及藍白帆布,也算是深水埗的特色之一。
因為加租,梁莉姿每兩年就會搬一次家,此為她曾居住的唐八樓。
鄰居是一樓一,以及一個凌晨三點找貓的人
四段深水埗的故事,既包含著美好過去,亦有苦痛經歷,然而所謂好壞只是一種角度。梁莉姿初中時曾與公公婆婆居於深水埗的唐樓大單位,隔壁鄰居是一對相熟的老夫婦,梁莉姿經常到他們家裡吃飯。好景不常,不出幾年對面單位變成了一樓一,老鄰居離世後,隔壁更改建成劏房,自此鄰里之間紛爭不斷,讓梁莉姿非常困擾。然而一年農曆新年,一直不喜歡對面鳳姐的婆婆,因不忍她們在異地孤身過年,竟為她們送上自製的糕點。這個小舉措,讓鳳姐們流露出從未有過的笑容,亦讓梁莉姿發現,「即使深水埗龍蛇混雜,但在褪去各自的標籤後,大家都只是普通人,過著普通不過的日子。」
深水埗接納著各種各樣的人,難怪也會接納一個凌晨三時蹦出來說要入屋找貓的人。饒雙宜在深水埗居住時,她的愛貓曾在晚上突然爬出窗網,從唐八樓掉了下去,嚇得她馬上跑到街上尋找愛貓,誰料卻未有發現。於是在深宵時分,她唯有逐家拍門查看,沒想到鄰居都願意開門協助,有些是穿著「孖煙通」的大叔,有些是睡在地板的一家三口,這群生活艱苦的草根階層,反過來接納了這樣一個不速之客,如要說深水埗壞,但這樣理所當然的信任,卻是在深水埗尋得。
深水埗的街道:「有求必應」的不夜城
形形式式的人,因應各自的生活需要及習慣,創造出多元的深水埗街景。深水埗最大的特色,是這裡沒有單調乏味的大型購物商場,更多的是開在騎樓下的小店,以及在街道中央聚攏的一行行排檔。甄拔濤憶述,「小時候與朋友相約在黃金商場,我多會由蘇屋邨走過去,途經青山道及元州街時會經過很多模型店、漫畫店、機舖、小食店等等,全跟當時的新潮玩意有關。」相比起井井有條的商場,在深水埗隨意走一圈,更能找到驚喜。搬到深水埗前曾居住將軍澳的梁莉姿亦指,「新市鎮的設計乏善可陳,只提供單一的配套,看似能夠滿足基本居住需要,卻又限制了一切可能。唯有在深水埗,才能真正看見一個城市的可能。」
這個「可能性」,讓深水埗漸漸由日間發展到夜晚,近十年起,北河四街一帶冒起了夜墟、天光墟的地攤。林女士形容深水埗的街道就是如此有趣,「同一條街,不同地段、轉幾個彎已有不同生態,到了日夜又彷如兩個世界。」如饒雙宜居住的成衣街晚上會關門,取而代之的卻是馬路上一架架大貨車。她續說,「每晚約十時半,你就會看到深水埗的另一面,城市人的奢侈浪費會在地攤裡被消化,基層市民會在這裡搜刮平貨,南亞人則在這裡公開聚集。」彷彿深水埗是一片魔法土壤,在黑夜裡漸漸生長出一整個地下城,暗自解決日間堆塞的、不被容許的、無法被滿足的需要。
在深水埗可看到香港所餘無幾的「下舖上居」型騎樓。有趣的是,樓上這些單位早已改建,唯獨左上的單位一直空置,原先的露台亦得以保留。
入夜後,深水埗隨街可見大貨車。
深水埗的地踎精神
基層市民以廉價在地攤中購得所需,梁莉姿卻從中覓得一點樂趣:發掘隱藏在物件背後的故事。她曾看過有人在地攤賣已喝了一半的威士忌,也曾看過有人賣一千隻紙鶴,每一隻紙鶴都寫上了字。有一次,她在農曆新年期間在地攤買了一對姆明情侶杯,後來與檔主交談才得知,這對杯子屬於他已離婚的大哥大嫂,本以為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誰料檔主卻歡天喜地的說:「計你廿蚊啦,新年快樂!」
梁莉姿用二十元買了一段感情,而饒雙宜在深水埗尋得的,就是難以複製的市井味道,一向喜歡下廚的她指,「很多深水埗的小食店都很有心,那種味道很踏實,是我無法在家裡煮到的。」笑言自己逛深水埗,從不記街名,而以美食為座標,又稱自己雖然不是咖啡迷,卻特別喜歡光顧藍山咖啡店,「其實這小店也很有趣,它既不是咖啡店,也不是茶檔,但你可以去吃一個番茄紅衫魚飯,然後點一杯咖啡。」
甄拔濤續說,「根據我的成長經驗,深水埗是一個天生天養的地方,因此才造就了它的多元。」並笑稱自己在深水埗見證了全港第一家發明炒公仔麵的茶餐廳:星仔記。除了吃,甄拔濤認為電子產品更體現出深水埗的民間智慧——與時並進的地踎文化。「很多生活裡的小伎倆都彷彿源自深水埗,如旅遊sim卡、演唱會燈牌,甚至睇波機頂盒等。以往在鴨記逛一個下午,就可知道最新的潮流。」
深水埗的夜攤。但因為疫情,很多攤檔都沒有營業。
當文青遇上地踎:深水埗是小店生長的地方
近年,文藝小店、cafe於大南街「踩過界」,並逐漸大行其道,彷彿與深水埗的地踎味格格不入。饒雙宜卻認為這才是自然,因為香港就是一個捐窿捐罅尋找生存空間的地方,而充滿原材料的深水埗,更是最適合讓創作萌芽發展的所在。梁莉姿則以深水埗歷史為例,說明這是常態,因為「深水埗本是一條明渠,後來五花八門的人臨岸做生意,共同拼貼出深水埗的獨有面貌。」
談到深水埗士紳化的問題,有時難免跌入二元對立的陷阱裡,認為小店林立令租金上揚,必然助長地產霸權,扼殺老店生存空間。總是在深水埗逛街的林女士卻不反對這種改變,反而看出了機遇,「大南街大多是舊樓及匹頭行,一向人流稀疏,近年新店進駐帶動了人流,或許會為這個本來偏靜的地段帶來新機遇。」換言之,新事物進駐也不一定是弊多於利,梁莉姿更觀察到,「現在大南街很多小店會主動與社區連結,如早前foreforehead舉行的街招日常展覽,便連結了一群深水埗的在地店家,其實已為這個社區帶來改變。」大概這就是所謂「拼貼」,意思是新舊舖之間不必然是對立,也不一定要共融,重點是保留各自的獨特性,才能產生一種新的圖像,如甄拔濤所言,「不讓一種生活模式壓過另一種,大家各取所需,自然就能繼續生存,所謂小店,就是要保留多元。」
深水埗的自成一格,正在於它一直混雜了不同階層與族群、需求與慾望,乃至於好壞與善惡,在這個擁擠得寸步難行的城市,有人從狹縫中發展出民間智慧,有人「捐窿捐罅」努力尋找生存空間,讓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不只於深水埗,也在如今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