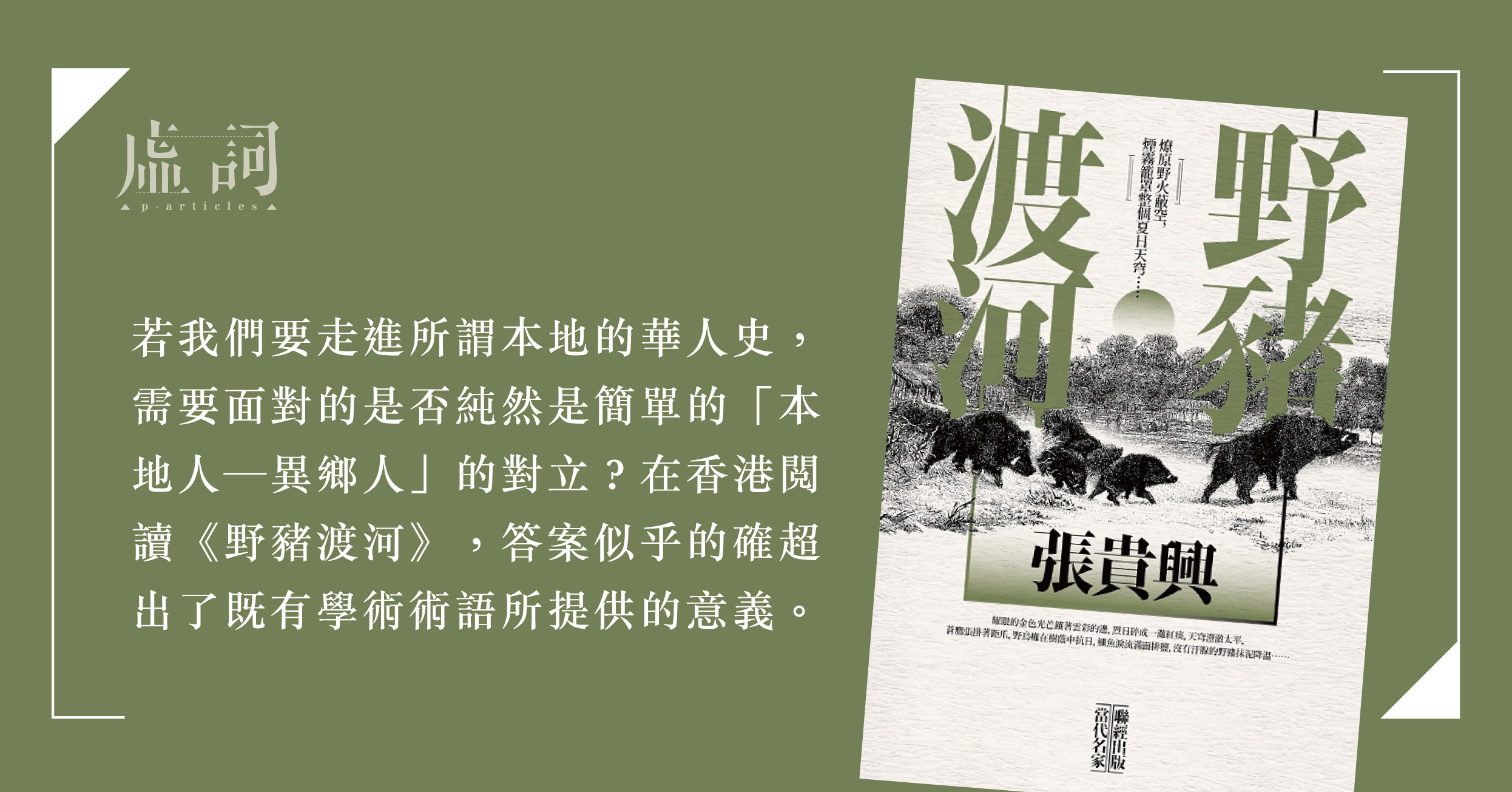暴烈雨林,暴烈歷史︰張貴興《野豬渡河》
長居城市的我們鮮有關顧香港的山林,然而對張貴興而言,雨林卻刻有砂拉越的思考方式。我並不是為了東拉西扯騙字數才寫的這種煞有介事的「香港—砂拉越」對比的,從歷史上而言這兩個地方實在是非常相似的,這使我對張貴興的雨林書寫一直有著無比的興趣。在《野豬渡河》之前,張貴興的雨林已有著沉重的歷史幽靈在背後遊蕩。《群象》試著勾出隱匿於砂拉越雨林的地下馬共足跡,《猴杯》細緻地處理殖民者與本地人的混雜關係,在《野豬渡河》之前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沙龍祖母》已經嘗試處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史。可以說,張貴興的長篇小說無一不指向重構砂拉越歷史的企圖。
砂拉越的時間,歷史的時間
高嘉謙為《野豬渡河》寫的序,題名「被展演的三年八個月」,「展演」二字可謂說得精確,不過要被展示的卻遠遠不止「三年八個月」所對應的日戰時期。《野豬渡河》寫的是日軍與砂拉越華人群體之間的軍事行為,當中包括殺戮,也包括了華人游擊隊的反抗、豬芭村村民對日戰和反抗的不同拉扯,乃至於豬芭村歷來因為野豬到村內暴虐而組成的狩獵隊內部的私事。在張貴興這部小說裡我們不難看見許多與「三年八個月」歷史相關的展示,包括各種史蹟、土產和時間標記。這些標記在小說內不斷地指涉敍事層以外的真實世界的歷史,使《野豬渡河》有著無可避免的歷史小說意味。
小說首先要展示而且頗為刻意的,是各種歷史的時間點。時間在小說內的份量,已經達到煞有介事的級數,例如〈面具〉開首便以不同方式指稱時間點:
西元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歲次辛巳十月二十八日,昭和十六年,鴉片戰爭一百年後,白人獨裁者占姆士,布洛克王朝統治砂拉越一百年後,日本突擊珍珠港九天後。[1]
敍事者特地提交出如此繁複的時間標記,就是為了透過指稱時間的不同方式,梳理一次砂拉越的宏大歷史。不過,宏大歷史滿是他者的標記,似乎並非張貴興所願,所以,在之後所有的章節,時間座標又回到了柏洋和爸爸關亞鳳的時間。在歷史時間與個人時間的有機組合下,砂拉越的歷史有兩組時間並行。這都是為扭轉所謂宏大歷史所造的嘗試。張貴興借此把「三年八個月」的歷史,乃至砂拉越的殖民史,都扭進了柏洋和關亞鳳的人生,並在內進行各種有機組合和戲謔。
物與史
除時間以外,《野豬渡河》小說劃分的小節很多,敍事結構穿梭閃藏,比起一個完整的故事而言,讀起來更像是走進一家歷史博物館,許多零星史物以及它們的文字介紹,在靜靜地等待閱讀。透過這種展示性質的敍事,把砂拉越的歷史分散地透過緊扣物來呈現。
這種展示究竟是怎樣的形式呢?熟悉張貴興的讀者一定深明他擅於把所謂有本地色彩的動、植物與歷史勾上關係。例如《野豬渡河》〈懷特.史朵克〉一節的開首,便有一段說明式文字:
懷特.史朵克(white stork),白鸛,候鳥,又名東方白鸛、老鸛,鸛科鸛屬,大型涉禽。[……]喜食異種或同種鳥類幼雛。分布於歐洲、非洲、中亞、印度、日本和中國,冬季遷徙到非洲和印度熱帶地區。在台灣和東南亞屬迷鳥。
二戰時期,太平洋聯軍以懷特.史朵克戲稱日本戰機或偵察機。[2]
這段說明與章節內由豬芭村首富黃萬青、洋貨批發商張金火、豬芭日報創辦人劉仲英、咖啡館老闆朱大帝等一眾華人組成的「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一樣耐人尋味。太平洋聯軍對日本戰機的戲稱不無關於懷特.史朵克這種鳥的特性,「喜食異種或同種鳥類幼雛」。這種西方與亞洲的對立,在豬芭村華人的眼中是一場像花果山猴眾一起抗打天兵一樣的戲碼——為了籌錢,他們在日軍入侵前三天,出演兒童話劇《齊天大聖》。一場滑稽劇把所謂「華」的認同,變成了戲謔的對象。當日本戰機「史朵克」投下炸彈時,這抗日團在做的也不是甚麼招兵買馬的事,而是正深入雨林「殺一頭年輕的豬公,給我們義踏隊伍進補!」[3]
可以說,儘管大歷史和各式國族名詞(例如「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的確在砂拉越衍生過,然而,這些與國族扣連的事物在《野豬渡河》內又顯得略有時差,甚至是歷史意義和名詞內涵上的落差。
「自然史」與「地方史」
上述種種都呈現出一個結構複雜的砂拉越史觀,也是張貴興從《群象》、《猴杯》再到《野豬渡河》的重要母題。王德威認為《野豬渡河》內「砂拉越華人的歷史節節敗退,日後種種學說,不論是『靈根自植』還是『定居殖民』、『反離散』,都顯得隔靴搔癢」,[4] 而高嘉謙也指認「《野豬渡河》鑄造了砂拉越的新『傷痕文學』,但又像幽暗大地的現代啟示錄」。[5] 配合上述一再被展示的地方歷史和時間座標,兩位學者的判斷自然合理,只是,與此同時,也勾出許多弦外之音與問號。張貴興筆下的砂拉越華人歷史退敗以後,這片土地有甚麼因此而顯現出來?是砂拉越的本地人嗎?還是說,對砂拉越而言只有原始的倫理才是永不滅的?
上述種種問題的解答方案,張貴興將之交給了雨林原始倫理,而且也並非第一次。以野豬為名的小說,自然以野豬為主角。野豬渡河是小說內的第三重時間,展現著雨林的倫理。事實上,野豬渡河本是覓食求生,一隊野豬各有崗位,跟隨季節轉換過渡邊界,行經河岸。[6] 雨林是《野豬渡河》最大的圈套。它的暴烈不在於野豬們對於人的虐待,而是它勾連著整場日軍圍殺「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的成功。黃錦樹指出《野豬渡河》設定了內鬼愛密莉,這個設定看起來略微弱,流於類型小說一般的設定。[7] 的確,愛密莉的角色設定非常有趣,也讓她超越一個復仇小說的角色設定。不止在〈尋找愛密莉〉一節內能看出她精通砂拉越雨林的一切,她一直以來在獵野豬上得心應手,穿梭雨林如無同無阻,甚至讓兩代華人都以為她是「自己人」,然後埋在她背後的卻是日華英交雜的傷痕。如果說砂拉越雨林的熟悉,以及獵豬的行為讓她成為「自己人」,那最後的出賣又算甚麼呢?這偏偏是《野豬渡河》挑戰國族、反思本土的重型炸彈。我們真能界定誰才是本地人嗎?
英殖,三年零八個月,各地華人雜居,歷史暴烈,雨林亦然。我彷彿也想起香港的華人史書寫。若我們要走進所謂本地的華人史,需要面對的是否純然是簡單的「本地人—異鄉人」的對立?在香港閱讀《野豬渡河》,答案似乎的確超出了既有學術術語所提供的意義。
註︰
[1] 《野豬渡河》,頁29。
[2] 《野豬渡河》,頁115。
[3] 《野豬渡河》,頁127。
[4] 《野豬渡河》,頁11–12。
[5] 《野豬渡河》,頁18。
[6] 《野豬渡河》,頁373。
[7] 黃錦樹:〈腳影戲,或無頭雞的啼叫:評張貴興《野豬渡河》〉,《文化+OpenBook》http://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80901w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