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離這叫香港的盒子:從幾首詩談起【2022 非家非類──游靜 影像與文字創作專題】
劇評 | by 梁匡哲 | 2022-1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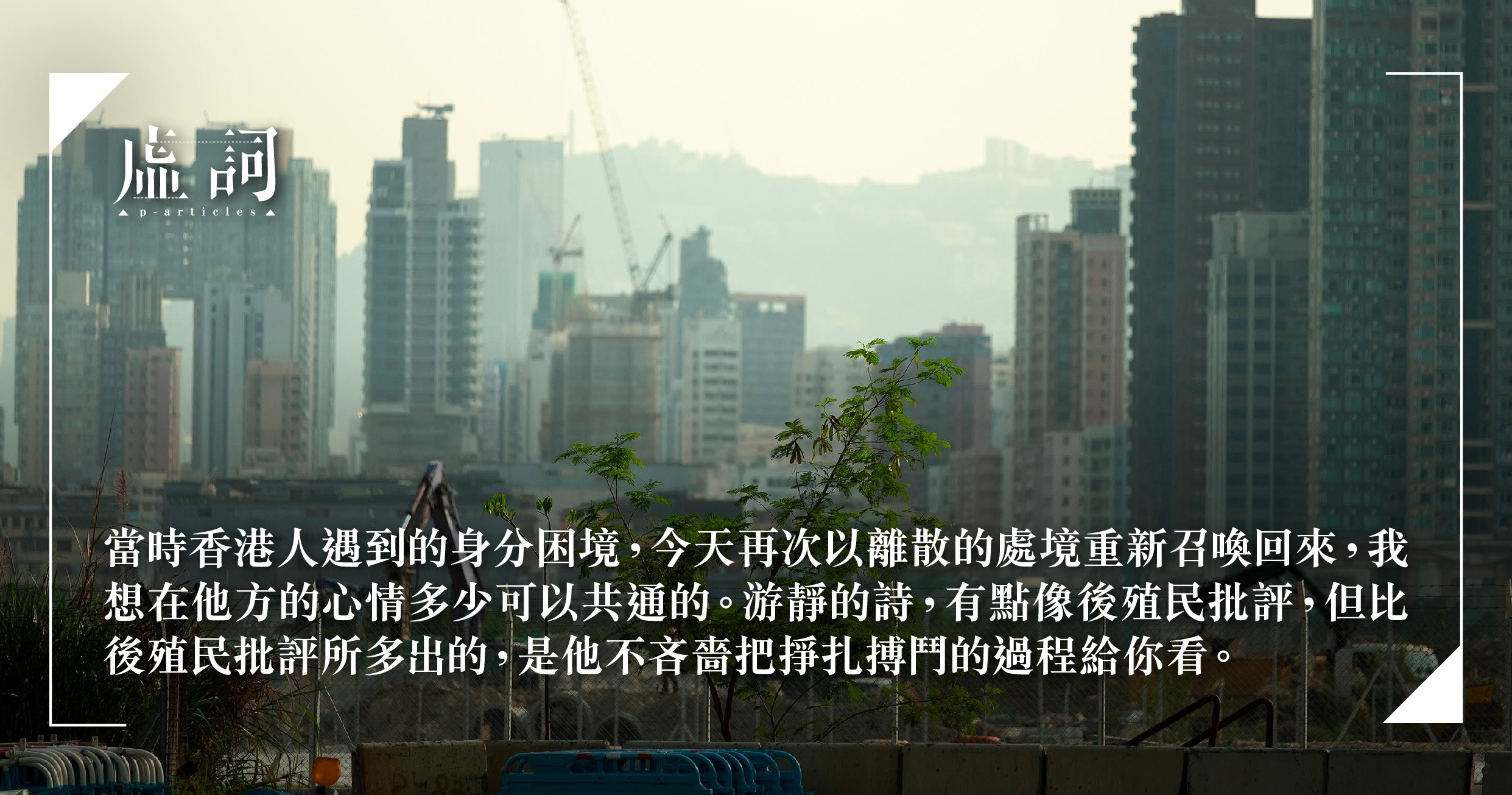
316125715_1709843526082217_5237548022784633111_n.jpg
多年以後,我才發現我讀懂了游靜多一點點。
有一點長期被我忽略的是,游靜的作品中思緒的移動是連同肉身的移動一起進行的。對於游靜,移動及其欲望幾乎可以說是貫穿在她所有的作品裡,誠如他在《另起爐灶》的新版後記自述:
我之為我,就是先與這些人決裂,才能存活。出走、離開、另起爐灶,是我整個童年以至少年最大或唯一的目標,支撐著我活下去。
關於移動,我曾經在另外一篇文章提到過交通工具是閱讀詩集《史前紀》很重要的線索。我認為交通工具是一種鑲嵌在生活場景的東西,而不只是一個把人從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的功能物。我們不應該忽略的是,交通工具本身作為「空間」的存在,這個中轉空間充滿著可能性,是一個特殊的觀察位置。可以休息,可以冥想,而游靜選擇了觀察、思考和寫作。比如他常常利用渡海小輪的航行時間書寫專欄或詩,而他把這個寫作的空間也當作內容記錄下來。
游靜在《另起爐灶》的新版後記也提到「九十年代大概四分一時間是在飛機上,大量的書寫,也在飛機上」,他形容這段時期他的文字「不在香港的地面上,而是在空中向香港喊話」,游靜自嘲這種寫作是「堅離地」,即港式俚語中的不接地氣。但很明顯他並不是俯視眾生,而是眾生之一,他的「離地」視角就是一種在升騰與著陸之間所構成的:「我走的時候,以為可以尋求遺忘。我以為,即使我回來,也已學成飛行的輕飄。跟所有人一樣,我以為記憶太重,問題是,飛行本身也構成一種記憶。」
這種記憶是甚麼呢?在美國留學的青年游靜情感就像一種飛行體驗的延長:「一個人生活在外,時刻覺得自己活在兩個不相干的世界之間,兩種文化,兩種政治,兩種性別之間」,這種移動的感覺經驗就是一種「之間」的經驗。對他方的感受因帶著此地的感受而質變,而對此地因為有了他方的知識衝擊與生活體驗而穿插著不同的視角,這種「之間」的雙重意識是游靜作品的底色。
事實上,游靜思考的問題其實承接著更早一代的作者。早一輩作家如西西和也斯在七十年代已經在創作上有著處理殖民身分問題的自覺性。譬如也斯的問題:為甚麼香港的故事那麼難說?又正如西西在《我城》提到只有城籍的人,這一種「香港」的思考位置必然有異於那些較有清晰家/國認同者的框架。如果說他們將深刻到位的身分思考用相對平和沖淡的風格呈現,那麼游靜的特點就是用銳利的愛憎交纏,以更介入的態度來說她的香港故事。
回過頭讀《不可能的家》的詩。若說《史前紀》那些更早期的詩作呈現更多的是在地的移動,寫於九十年代求學時期的《不可能的家》則是跨國跨地域的。我留意到游靜這時候寫的詩常常將「家」與「移動」並置,他通過「家」的意象來寫「移動」,也通過「移動」的過程來寫「家」,許多訊息都隱藏在這個脈絡裡。
我們先從《不可能的家》的一首點題之作談起。〈城〉這首詩雖然短,但濃縮了瀰漫在游靜不同詩作中的感受,是理解他的詩一個不錯的起點。
在〈城〉,他提到「每一個城市都是開始與總結」,對於旅居過的城市,開始與終結有清晰的分界線:「紐約總結了我的創作」、「巴黎總結了我的愛情」,這兩句都是有著非常順滑、篤定的語氣的。但是到了香港,「只有香港/永遠是開始/因為不可能/也許這便是/所謂家」短短的一句話就出現幾個斷句與迴行,這是談論其他城市時所沒有的。並且緊接著「只有」、「因為」、「也許」三個轉折,即便這看上去是一個「解釋」,卻有一種不知從何說起、欲言又止,艱難的感覺。其他的旅程有「開始」與「終結」,但是香港沒有,永遠是開始,因為「不可能」終結或總結。所有的「離開與回來」都與「家」構成新的連結、構成說不完的愛恨。對自己熟悉的地方,也許是最難說得清楚的。
〈城〉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狀也在〈港台中飛機詩〉出現。此詩是一個充滿著瑣事的搭機漫想,穿插著當下的經驗、私人的記憶與公共的歷史。游靜在移動的過程中嘗試把這種「很難說得清楚」展開,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他將搭飛機所象徵的移動,從個人選擇的層次提升到歷史的層次,並思考一連串的極其偶然與必然的軌跡。
在詩中的第二節,提及兩岸分斷的時刻,身為國民黨員的父親遷移到香港是因為台灣拒絕了他,故遷移到香港是個「偶然」。而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以後,又成為了一種「偶然」中的「必然」,讓游靜不得不去在一次又一次的飛行中面對身分的問題:「如果我沒有BNO 我會在這裡/飲你 而且把你/寫在一首 我想是關於身份 的詩裡面去嗎」
此詩的精彩處,在於游靜反思了移動之為「自由」的表象,道出怎樣移動往往有著歷史的制約,不論是自己與父親也如是。他誠實地直面了自己對歷史的也是家人的片面理解:「我寫 從來不寫他們/我的自由 來自唾棄他們/唾棄一個階級 一段歷史/一種創傷 後的中國人」而也以略帶幽默的日常道出其父親「不移動」本身也是一種沉默的政治選擇:「我爸爸拒絕拿BNO/……/我爸爸認為/到對面街的大排檔吃飯是/太遠了 即便是我付帳」,個人的選擇離不開大環境所賦予的選項,這是誰也無法逃避的。
前面談到的兩首詩都是從移動的經驗寫家,而透過家的意象來寫移動的,則有〈香港病〉。此詩的主軸貌似只是抒發對於香港的感覺,抱怨住在此地的經驗。但若我們細心留意,這首詩也有涉及「移動」與「家」的關係:「捱到搬離這叫香港的盒子/我的敏感自動麻木下來/健康原來是一種麻木」,其實「搬離盒子」,意味著從香港這樣一個狹小擠擁的空間,去了更大更自由更廣闊的地方,理應是快樂的。但游靜的反思正是從這裡開始的,這種不舒服感的消失,他稱為敏感的「麻木」、「健康原來是一種麻木」。由此「健康」的褒義被顛覆了。我們不禁會問,這是甚麼意思呢?「不感到活著是難」的美國相比於那個使他「頭痛發熱、呼吸困難」的香港不是更值得嚮往,更值得留下嗎?
詩中的感受,正如他在散文〈迴航〉裡寫加利福尼亞的環境的時候,他身上的「香港」就浮現,提醒他將當下的「美好」經驗與此前的「匱乏」狀況對照:「最有效的麻醉不是來自盲目的物質主義,而是垂手可得的,解決你各種需要的自由和充裕」,對於游靜來說,香港所不具備的文化與物質條件,也許都在美國輕易得到滿足,但游靜視這個「不用追求」為一種怠惰。
這種對於香港的追認遠遠不是那種「本土主義」的美化,而是坦承那個「不好」也構成了他敏感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份。詩中的不舒服可以理解為「自我」與「社會」的不諧和狀態,這種「不舒服」譬如是文藝創作沒有足夠的支持,性別概念的僵固,或者一種短視投機的心態,然而種種不舒服卻恰好也是開啟思考的觸發點。「在香港/我從沒健康過」,因為「懊惱納悶的心情大量發售」,可是梳理這種壞情感也反過來成為「難怪寫作」的源頭。正如他在散文〈給May的信〉寫香港:「我勉力離異,又戀戀於它(它是我的一部分)。我無法架空地憎恨這城,一如憎恨地中海貧血,憎恨我自己」,細膩地表達他既愛且恨的複雜情感。
從這首詩,我們看到一種雙重意識的情感結構。如果只有第一部分的抱怨,很多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並不稀奇。但是游靜詩最獨特之處,在於他除了移動,還會回望,能夠再退一步去看自己的權力位置,並在最合理,最常識的地方進行反轉。由此,我們無法從游靜的詩作辨識出名為「立場」的東西,不是他沒有看法,而是他總是不斷切換著觀看的視角,拒絕給出過於輕易的、選邊站的答案。
多年以後游靜在一篇回顧自己學習電影製作的文章說:「誠實包括不斷叩問自己的局限,不希冀衝破(那是狂妄),而是如果能努力不懈增加對局限面對面的檢視,作品才有介入社會的可能。」〔註〕
我覺得,游靜多年來在作品中的思考在今天看來之所以仍然具有批判力,正是因為他的這種態度。,而且也跟歷史當下機緣有關。當時香港人遇到的身分困境,今天再次以離散的處境重新召喚回來,我想在他方的心情多少可以共通的。游靜的詩,有點像後殖民批評,但比後殖民批評所多出的,是他不吝嗇把掙扎搏鬥的過程給你看。他不願意抽離,居高臨下地說話。這也許就是詩的無可取代之處。
而這些,我想是我讀懂的部分。
(本文為作者應國立清華大學藝術文化總中心主辦「非家非類──游靜 影像與文字創作專題」之特別邀稿,收錄於影展專刊,蒙作者同意轉載。游靜的創作面向包括文字與影像,作者本身亦寫詩,以詩人角度看游靜的詩與文,文字中的家與國與自己。影展於2022年11月8日至26舉行,詳細資訊請參考清大夜貓子電影院部落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註:游靜,〈電影練〉(https://www.mplus.org.hk/tc/magazine/yau-ching-on-film-studies-and-yvonne-rainer/?fbclid=IwAR10sAh0ng4p59n6i8RTTdU3LHgqTwyoJ_iSosQX99RmI72Y4UzR9soTk0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