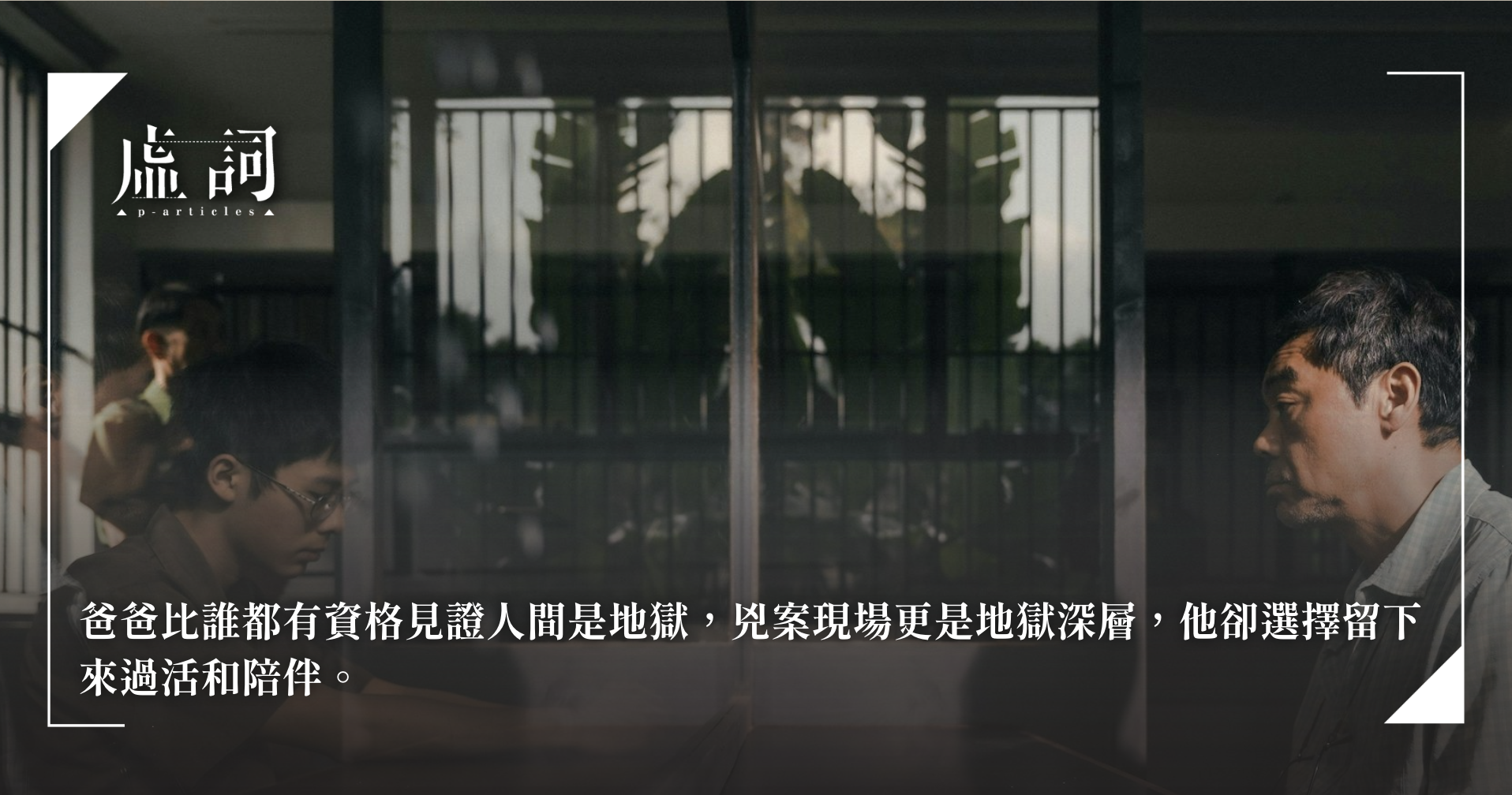道聽途說的經典累積成幻夢,一趟打破生死界限的旅程:澀澤龍彥《高丘親王航海記》
書評 | by 瀟湘神 | 2025-02-06
9世紀中葉,已入佛門的日本皇族高丘親王來到中國。當時距唐武宗滅佛才經過十餘年,慘遭挫敗的佛教尚未恢復。或許正因如此,高丘親王未久留中國,而是前往佛教的故鄉天竺。然而,他卻從此踏入神祕,渺無聲息,有消息指出他在馬來西亞南部逝世,死因成謎。幾百年後,日本民間流傳一種說法:親王的下場並不尋常,據稱他遇到猛虎,遭虎吞食而亡……這短短一年間,高丘親王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程?為何最終死於虎口?這份謎團無人知曉。但正是這懸於遙遠時空外的未知,封存了無限可能,才為澁澤龍彦創作《高丘親王航海記》提供了想像空間。《高丘親王航海記》並非解謎之作,而是一部想像力豐沛、異國情調濃厚的小說。高丘親王行經的古代諸國,皆採用當時中國譯名。然而,9世紀離大航海時代尚遠,即使是中國的記載,也多半是道聽途說,或原本有根有據的事物,在口耳相傳中失真而變得荒謬。作者無意描寫真實,不打算宣稱那些遙遠國度真有如此妖艷獵奇的風土民情。親王彷彿從未離開日本,只是一頭撞進那些道聽途說的經典累積而成的幻夢,經由幻想的濾鏡朝內在自省。作者為親王虛構了前往天竺的理由,這份虛幻的追尋不斷在旅程中閃現,他根本無暇「發現」,因為無論遇見什麼,都會透過那些異象與怪物回顧自己的人生。 (閱讀更多)
重讀《安提戈涅》
趙遠重讀《安提戈涅》。《安提戈涅》是古希臘索福克勒斯的悲劇,講得是安提戈涅違抗忒拜城國王克瑞翁的旨意,執意要埋葬自己的哥哥而被治以死罪的故事。在文學課堂裏,《安提戈涅》通常被當作經典教材,講授人的律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矛盾。知道天律是智慧,但遵從天律卻需要莫大的勇氣。當人人都唯唯諾諾順從人的律法之時,一句大聲的「我敢」就是最大的美德。人的律法的審判不是真正的審判,身體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審判是道理、歷史、甚至信仰、真理的審判。安提戈涅不害怕觸犯人的法律,這才是對「生」有足夠的信念。她相信即使她的肉身滅亡,她的靈魂還會因爲公義而存在,她的「罪」還會被世人紀念。 (閱讀更多)
隱世生活不隱世
書評 | by 亞C | 2024-12-02
香港作為一座公認的高密度城市,其實尚餘很多自然和鄉村散佈在高樓之外。自然書畫家葉曉文搬進了位於香港東北角落的荔枝窩,這幾年內,她獨自在這個藏身於自然的原始客家圍村裡生活,並一直保持創作,將居於此處所經歷,所體會的種種,寫成了自己的新書《隱山:山居日月筆記》。亞C傳來書評,指出此書不只有「寫」,更有「畫」。「書」與「畫」都是兩種十分重要的藝術創作形式,並且兩者編排在一起時,常會蘊藏著某種特別的聯結,產生各自單獨「存在」時所沒有的藝術效果。書中一切都是淡淡的,那份細緻與用心,並且配上與之呼應的文字,更為傳神地抓住那位於自然深處的日常所滲出的有趣細屑片刻。 (閱讀更多)
方方與新寫實小説
書評 | by 黃子平 | 2024-12-09
每一部作品都是「單子」式地自成一體,評論界或文學史家卻想方設法將它們分類組合,藉以生產學術話語。黃子平指出,評論家公推武漢的方方是扛起了「新寫實」這面大旗的四位作家之一。他認為,「新寫實小說」無非是說老老實實地寫了中國老百姓過往幾十年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方方自己不承認自己曾「倡導」新寫實,但覺得這個名堂用來概括自己的寫作不無道理。新寫實小說始終關注現世社會最普通的人。它秉持著人道精神,對生活中普通人充滿同情和憐惜。同時,它對現世社會也秉持著不合作不苟同的態度。何為「實」,如何「寫」的問題,歸根結底要追問到「文學何為」的層面。文學即自由,即掙脫現實的束縛,將詞語和想象審美化,直達人心的深處。這就是「新寫實小說家」的異類方方的意義。 (閱讀更多)
last but not least, shall WE dance?──評《破‧地獄》The Last Dance
電影《破・地獄》開畫三天的票房已超過二千萬,成績卓越。葉嘉詠傳來《破・地獄》的影評,認為電影的中英文名字都改得好,既指人生的最後一舞,也是電影的最後一個靈堂場景。她從「給文玥的信」和「The Last Dance」兩方面來討論,最後一幕如何達至「破」地獄的主題。首先,她指出,最後一幕以書信呈現,認為書信是一種儀式,由寄信人用文字表達想法,並由收信人閱讀文字和理解意思,過程中除了人,還有時間。信雖直接,但不直接文哥、志斌和文玥又無以理解。同時,信也是打破傳統的關鍵,信中不只是一字一句解釋,清楚地向女兒道歉,還有他要兒子承繼衣缽的原因。其次,The Last Dance指的是人生最後一程,既是死亡,也是「破地獄」儀式。這最後一舞也預示我們的最後一程,只是有的早一點有的遲一點,但永遠不會不到。破地獄一幕破除生人的地獄,解開生人的心結,但她說,我們並不需要到最後才跳這支舞吧,last but not least, shall WE dance ?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