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進表皮下的矛盾與吊詭:讀韓麗珠《人皮刺繡》
書評 | by 劉綺華 | 2021-0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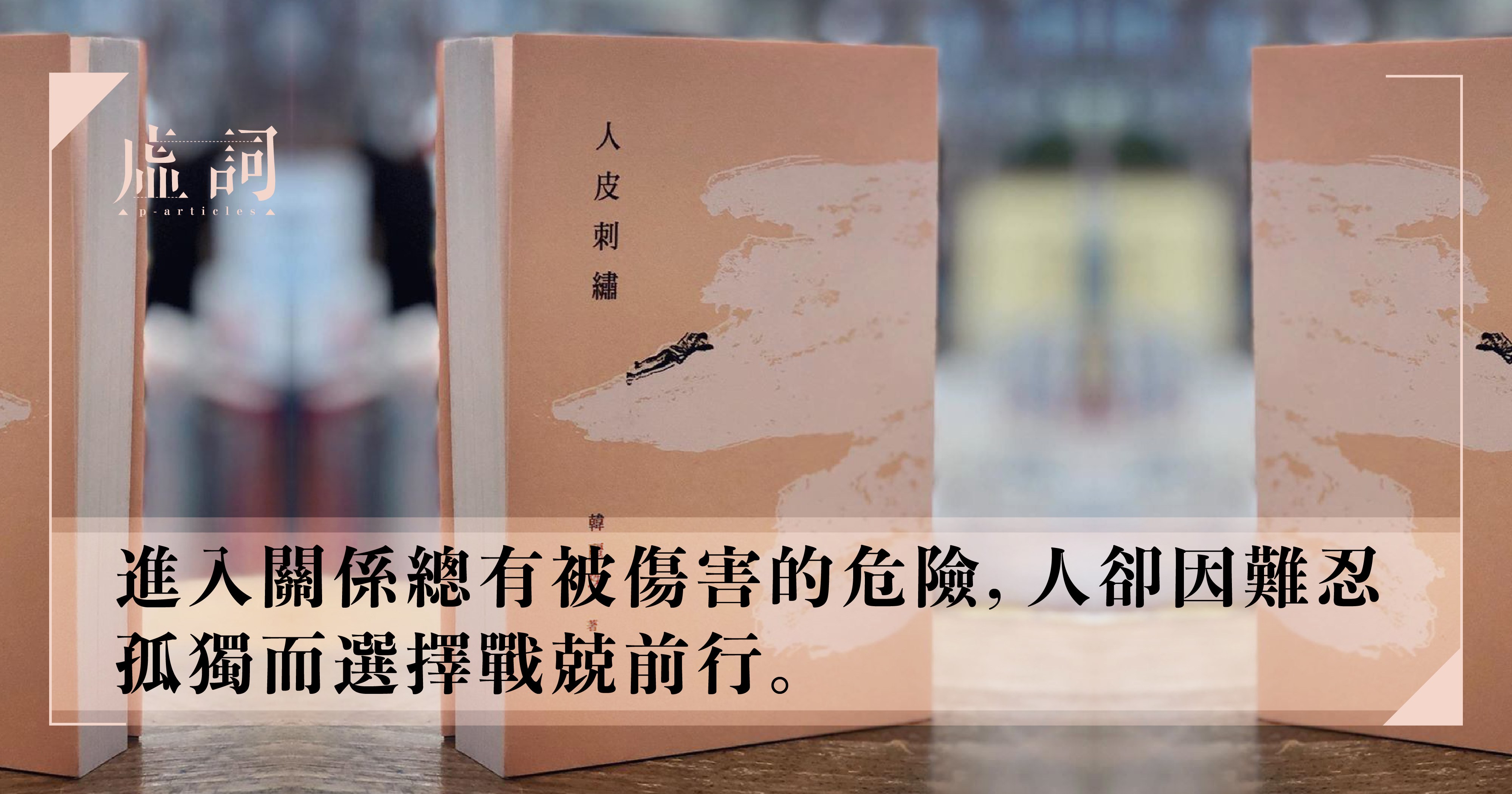
93702675_1771257686377558_7711972899363487744_n.jpg
一直覺得韓麗珠的小說不易讀,看《空臉》時像走進臉譜的迷官,起初翻開她最新作品《人皮刺繡》,心裡是有點疙瘩,沒想到是四篇清新可人的短篇故事。說是易讀,也不完全正確,情節是易懂,人物也清晰,有典型小說的輪廓,但沒有近乎透明的自省,沒有看清關係本相的能力,是難以進入她的世界的。
開始接觸韓麗珠,是讀她的《寧靜的獸》,當年蘇童稱她比殘雪寫得更出色。我也喜歡殘雪,想起《殘雪文學觀》裡殘雪反覆提到小說家應解剖自我,呈現人性的矛盾。無獨有偶,《人皮刺繡》最閃閃發亮的,正是作者對內心矛盾一層一層的剖析。
早前聽朋友談起沙特,沙特把語言分為「詩」和「散文」,前者指文字的物質性,即語言的的形式、排列等,後者以語言作為溝通傳達的工具,指涉具體事物。作為小說作者,我私下想,出色的小說家必能以最好的「詩」,寫最好的「散文」,文字的物質性,必能跟其主題相輔相承,成為不可劃分的整體。在《人皮刺繡》裡,最令我佩服的,是作者能用矛盾的修辭,把人性的矛盾揭露出來。
矛盾的修辭與矛盾的人性
全書充滿看似自相矛盾的句子,例如〈種植上帝〉裡火認為灰灰愛他,是因為「在他身上,她才可找到安全感,只有在夢想破滅的現實裡,她才能毫不愧疚地安於其中。」(頁20)相愛本應實現夢想,但夢想破滅灰灰反而安於其中。又如火跟灰灰說:「愛的意思就是,我可以任意傷害你。」(頁14)愛意味關心,但這裡愛等如傷害。或在〈灰霧〉裡,火餵灰灰吃飯,灰灰吃得多,反而「體態輕盈窈窕」,但她離開火時,不吃了,身體卻「一直膨脹,面積一直蔓延,整個世界的力量也無法干擾她運行的軌道。」(頁31)。及〈以太之臍〉裡,以太在醫院裡很口渴,但「她甚至不敢開口去討一杯水,雖然她需要的其實是一個綠洲。」(頁65)她看到每個人都身處海市蜃樓,根本沒有水。
從矛盾的修辭裡,我看到人性自相矛盾的邏輯。〈種植上帝〉、〈灰霧〉和〈以太之臍〉三篇互相扣連,反覆述說著「入侵VS 不入侵」的矛盾心理,當人被入侵,會感到不安全,容易受傷,但這是人的念茲在茲的,因人不能承受孤獨。不被入侵,人很安全,不被傷害,人卻活得空虛,這種空虛是難以承受的。這三篇小說裡,三個主角都在被入侵與不被入侵之間拔河,互相拉扯著。
〈種植上帝〉是開章,男主角火是操控女人的渣男,他自認是上帝,認為自己在「創造女人」,充滿男性沙文主義似是而非的歪理。火的內心有兩個上帝,一個是批判他的,另一個則是無論他做錯什麼,都會原諒他。所以火是個不會自省的人,比起兩位女主角,內心矛盾不多。不過以太看到他的歪理背後,是源於對愛和關心的慾望(頁52),他看不到這點,只停留在意識表層。
作者命名男主角為火,意指火的慾望,燃起女人們對愛的渴望,也燃起她們的內在矛盾。〈灰霧〉裡火不斷給灰灰餵食令她皮膚敏感的食物,讓她愈來愈瘦,失去自己,但這挑起灰灰的「慾望」:火能傷害她,即表示火最了解她,人總渴望被理解而放不開對方;灰灰當初被火吸引,是想佔據火的影子,其實跟火相似,都是想吞吃對方,「人要是沒有吃下對方的衝動,就不會走近彼此」(頁28)。進入關係總有被傷害的危險,人卻因難忍孤獨而選擇戰兢前行。火懂得製造罪疚感,不斷吞吃她,她本想反咬一口,但只能一直被吃,遍體鱗傷。不過離開火後,灰灰愈來愈胖,不再受傷,但心裡充滿虛空,永遠得不到完滿。
〈以太之臍〉探討渴望進入又害怕進入的矛盾。走進別人內心,本應像回歸母親的腹,感到安全自在。無奈關係充滿刺,走太近就充滿不安。以太想好像打開物件一般打開木的內心,但木未能了解她,她也不能跟木對應。他們的關係,就像木送的指環,是中空的,填不滿的;但因有著距離,她感到很安全,不怕受傷。相反她跟火,她自覺能跟他對應,他也明白她,也因如此,他可輕易傷害她。以太想利用跟火,避開進入與木的婚姻。這是另一層的矛盾。以太逃避婚姻,是想保存自我的完整,就像不受精的肚腹,但心底卻想進入別人、被人填滿,渴望潛進母腹的安全。結果她受盡了傷,拿掉火的孩子,回到虛空但安全的婚姻,所付出的愛都徒然,彷彿什麼也沒發生。
謊言的吊詭
第四篇〈人皮刺繡〉對應此書的後記〈謊言學〉,呈現「謊言」的種種矛盾。關係的「謊言」不是故意說謊,而是人與人相處時所說的「故事」。人所說的話,都是人對世界和自身的詮釋,而凡是詮釋,都是「故事」。詮釋與所指永遠無法觸碰,因為人必須透過語言來了解世界,既然無法繞過語言,人說話時,都得帶上自我的濾鏡,帶著虛構的成分。
人與人相處,潛意識為了維護內心的完整,使人不自覺說了謊。不過謊言既是虛構,看似不好,但正正如此,人才能承受彼此的關係。小時候「我」能說出家人的夢,但家人潛意識的謊言被說破,引起家人的憤怒,於是「我」明白到本相令人難以承受,學懂不識破別人的本相。謊言除了使人保持距離,也是「我」自我保護的機制。「我」被傷痛所困,無法說出來,身為人皮刺繡師,也不敢描畫自身痛苦的形狀,「我」以為出走,就能離開自己,其實是逃避,猶如活在自我的謊言裡。
另一方面,如果關係是故事,人與人相處,就是一起創作「故事」。雖然「故事」有虛構成分,但這正是人與人重疊的部分,沒有這一點,每個人都是無法抵達的孤島。「我」是人皮刺繡師,要以空蕩蕩的狀態,聽出客人的潛意識,然後以針刺的痛,把人的痛楚描繪出來。過程中,創作者自身要有體驗痛楚的能力,才能進入別人。身上的圖案是人皮刺繡師對客人的詮釋,也是客人自己對自己的詮釋,大家一起創造「故事」。
不過,創造「故事」不是心理治療,而是透過痛來描繪痛,讓人能安放痛苦。人天生趨樂避苦,寧願逃避內心的傷痛也不去接觸,但創作「故事」,就要必須接觸痛楚,這是「故事」吊詭的地方。教授M對「我」說:「人一旦立心要創造什麼,就是在每一刻之中削自己。」(頁144)創作者的「削」,就是感受身上的傷,使自己更銳利。與此同時,被繪畫的人也要開放自己讓人傷害,亦充滿著危險。例如失去帽子的男人邀請「我」一起找帽子,他的顯意識認為帽子不見了,但潛意識裡帽子仍隱隱作痛,這裡「帽子」可理解為內心的傷痕。他邀請「我」跟他找帽子,是開放自己讓他人進入的脆弱狀態。「我」在他身上看到創作的可能,「我」進入他,把他的潛意識「創作」出來,他沒有因此得到療癒,反而全身發癢,感到遺失的帽子愈變愈大。而當「我」為他紋上帽子時,他內在的痛被尖銳的針描述了,雖然很痛,但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結尾:男女之別?
編輯邀請我為《人皮刺繡》寫書評時,我好奇問為什麼找我,他說因為想找女作家來寫。我在網上看過關於此書的評論,也是女性所寫。而小說裡的男角,無論是〈種植上帝〉的火、〈以太之臍〉的木,還是〈人皮刺繡〉的保文陳,都是近乎空白、單向、無法理解他人的人物。難道男性就無法了解關係裡的糾結和矛盾?或選擇把這些都略去,視而不見?事實上,無論男女,都有想被他人理解、或理解他人的渴望,人人都會在關係裡受傷,這是近乎人性本質的東西,值得每個人,不論性別,都認真審視。所以對任何人而言,無論男女,《人皮刺繡》都值得大家細讀。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