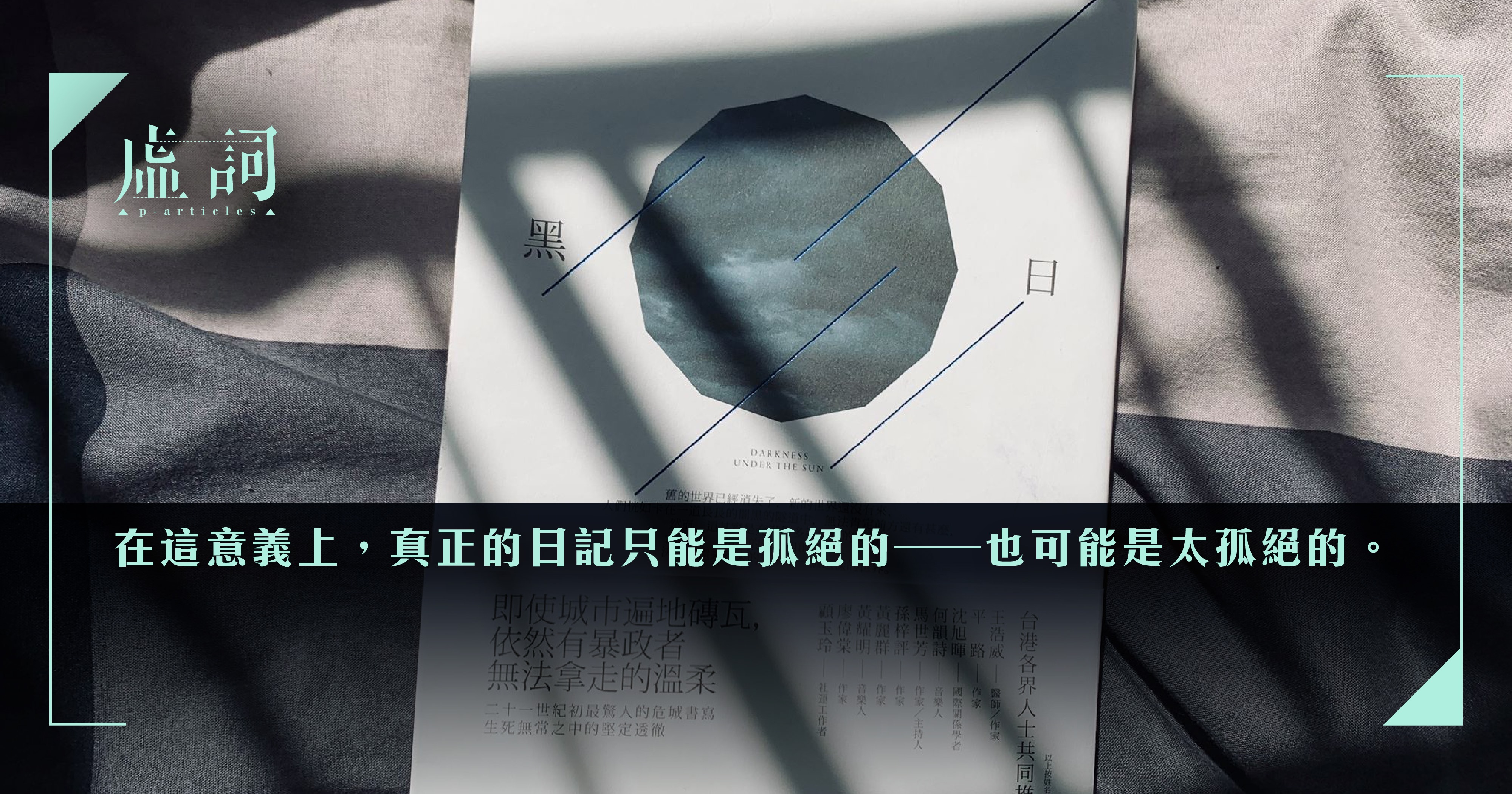日子的肉身:讀韓麗珠《黑日》
作為一本文學書,《黑日》是奇怪的。我們通常認為文學乃慢,文學寫作由於其手工藝性質,它的產生總是難能(也不必)追上外部世界的變化,更別說足量以出版。在這個時代、在這個震驚成為日常的香港更尤如此。當(後)雨傘文學仍在緩緩積累——五年之於文學的可能生命其實還很短——香港再度爆發一場革新人們想像的社會運動。它的規模更大,曝光更嚴重的濫權濫暴,亦引發了更危迫的出版回應。這批新近的專書包括報導結集、視覺藝術與各界合力的資料爬梳,《黑日》是唯一一本文學散文,以日記的體例,歷時載錄作家在2019年4月至11月期間寫下的文章。
一個恆久而難解的問題是:面對重大的歷史時刻,文學何用?在並不遙遠的二十世紀,戰爭刨出文明的野蠻根柢,災難降臨以後,文學成為艱困近於不可能的見證。納粹大屠殺超出人們理解的惡,壓垮倖存者心靈的界限,當記憶無法負荷,只有透過否認、遺忘來偷換劫後餘生的殘存秩序。《黑日》中幾次引述的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是奧斯威辛第174517號囚犯,被關押十一個月後,活著走出集中營,用兩年時間寫成第一本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在後遺一生的抑鬱與羞恥中,作家以文學轉譯巨大的歷史創傷,成為對那個時代最有力的證言。
《如果這是一個人》如今已是經典,但當初出版其實並不順利,曾被多間出版社退稿,理由包括時機尚早(換做今天的語言,可能是「題材敏感」),直到十幾年後再版才廣獲追認;而《黑日》的成書,除了是言論氛圍的體現,亦要感謝港台之間的文化紐帶。它得以來得更迅速,在事件的現在進行式中隨之誕生,對記憶的危機意識,即兌現為一種素樸而急迫的文體:日記。
日記作為一種敘事裝置,將時間與經驗的本真置於寫作的核心。日記寫作的機能比起手更傾向心,它的奧義不在技藝,而來自把現場經驗及時存續的一種衝動:趁日子未遠、記憶的強度尚未盡數流失,文字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皆挽留於一種鮮活時態。這近乎某種古老的寫作存有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而當身處危難,那進而成為生命的銘刻。二戰浩劫的另一座標原爆,在日本戰後文學嵌入一道血痕,代表作井伏鱒二的《黑雨》七成篇幅動用日記體,其原型的確是親歷原爆者的日記、手記。由此,小說召出存活於官方敘事外的庶民聲音,日常往復的凡人瑣事,歷歷照見災難的波幅。
《黑雨》的日記體畢竟有其後設維度,身為散文的《黑日》,則更趨近日記的原生態。文類的區分實際上有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它的形構。根據黃錦樹《論嘗試文》裡的多篇雄辯,散文的形式化程度屬諸文類中最低,這不僅是個技術的問題(例如相比小說的虛構工程要求更多設計,或詩對語言的高度自覺),而關乎其倫理預設:散文應該恪守真實性的契約,那是它文學效果的緣由。也可以說,散文的審美價值,生發自某程度上的「修辭立其誠」。
也許可以回到魯迅——那藉日記體宣告中國現代主體的誕生與壞毀的悲哀的父親——對當時起風的日記文學,他對真實性有嚴厲的堅持。〈怎麼寫〉批評不少日記體文章虛有格式,因其一旦意識到讀者的存在便容易粉飾、隱諱、裝腔作勢;「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但求心之還原,一種無中介的絕對坦誠。在這意義上,真正的日記只能是孤絕的——也可能是太孤絕的。我們會留意到,一個世紀後的社交網絡深深改變了寫日記的前設與型態,它的物質性、及其影響下的心態習慣已不是同一回事,而更可能向預想的讀者開放;《黑日》的關鍵,也正在私人和公共的交匯點。更重要的,是血與墨的倫理交織:比起真實的苦難(血),寫作(墨)毋寧過於輕易,總已是虧欠甚或背叛。災難以後,寫作怎樣才能不淪落為野蠻,或自絕於沉默?如果「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花的薔薇之二〉),那麼文學唯有回應倫理的內在之聲,以墨的流傳逼現血的真實——即使那終歸不可能,並因對不可能的承擔而可能。
循此邏輯,日記對真實的迫切感受,構成文學作為見證的條件,而這正是《黑日》背後的那種倫理性衝動,正如作家在後記中的自白:「當我寫小說的時候,為了尋找更新銳的敘事方式,常常刻意迴避『故事』,然而,當現實前所未有地鋒利,〔⋯⋯〕自六月以來的每一天,當我坐下來寫字,從空蕩蕩的身子裡搜索,那裡只有一些接近故事的『敘述』瓶子,我只能把所有難以言說的傾倒進去,它們便有了自身的形狀。」在亂世中行動與目擊的焦慮淹沒了寫小說時去故事化的形式追求,美學考量只得向現實肌理的感觸退讓:讓生命自己成為形式,文字乃如肉身。
於是寫作或閱讀《黑日》,是一個簡單亦難的過程。它的修辭並不繁異,但寫下來只是寫作的最後一步,在那之前的準備更具決定性:「寫作看來像是主動發出聲音,但如果要寫出真誠的作品,必須先要無條件和不帶立場地聆聽。」書中對聆聽作為真正溝通的條件的強調,顯現一種邁向他者的願力,而使日記的私語心緒與公共生活的理想互涉。九月十六日的日記,認真挖掘了「離地」此一貶義潮語背後的空間喻說而有深刻反思:「離地」「貼地」的語用總是太快地預設一種割據領土、畫地為牢的敵意,因而阻隔了交流的管道。這種耐性,作家從佛家思想中浸潤而得:感悟因緣業報的深邃流轉,超越俗世生命單位而升向更廣大的默想宇宙,由此迴照一種艱難的修身之道:時刻同理共感他者——不論是弱小如流浪動物,或權勢如黑警——以作為關心自己的技藝。生命與世界遭遇之處,情感自裂縫而生;換句話說,情感的流轉乃是他者進入視域的效應。通過代入他者的處境、反芻其引發的情感(而非被駕馭),得以安撫受傷的內心且尋找連結的機會,從而強韌公共行動的基礎:堅定清晰地發出聲音、要求對話與尊重,建立健康合理的關係。
當被網民質疑不應以未經證實的事件為創作素材,作家的回應是:「世界已碎裂,每人的視線所及,都只是最靠近自己的碎片。或許,只有當每個人都誠實地描繪自己撞上了的那塊碎片,所有的碎片才有可能在未來拼湊成失常時期的城市全貌。」面對危機,作為對真實——包括社會的和個人的,如果兩者真的能夠分開的話——的執著,誠實成為一種抵抗權威操弄的行動意志。一種可能的疑問是:在資訊發達以至泛濫的年代,聲音畫面皆在網絡隨手可及,還需要依賴文學來保存真相嗎?正是在這裡,我們也許能夠窺探那難以捉摸的「文學性」的其中一種意義:不限於客觀紀錄,主體的敏銳之心捕捉到某些難以被正統化到大歷史裡的剩餘物,那或許是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或許是對個體生命經驗的尊重,見證如此而成。由此,我總是發現自己在閱讀過程中勾起回憶或陷入沉思,一頁頁揭過書頁好像重新經歷同一段日子,以另一顆心靈;我感到憤怒、遲疑、被明白、悲傷、平靜、愛。
因為文學本身是對他人的應答,而終將成為贈予他人的禮物。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