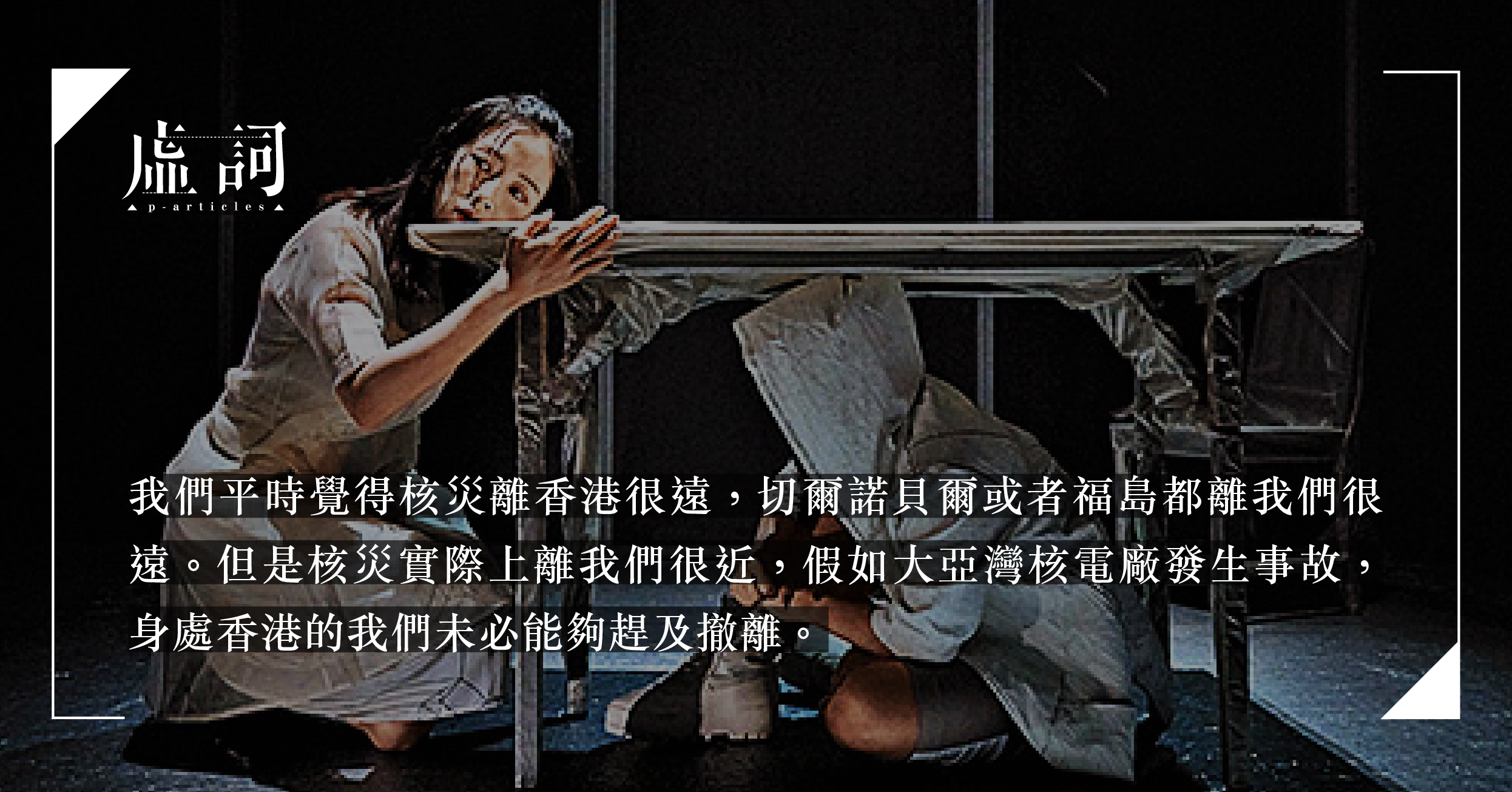因為災難,所以樂觀——評《核爆後的快樂生活》
人類自毀能力在當下迎來高峰,毋庸質疑。當日常生活籠罩在滅絕的陰影下,那麼在災難過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或者,這是在甄拔濤新作《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環繞不散的問題。核爆是一場災難,揭示人類的脆弱。在最近HBO短劇Chernobyl中,無形的恐懼猶如核塵埃一樣覆蓋城市每個角落。所有關於核災的描述,主旋律是悲劇。
但是,萬一,核災已經發生了呢?
已經過咗一段時間,所以我可以話俾你聽發生咗咩事
甄拔濤的前作,例如《灼眼的白晨》及《未來簡史》,多數聚焦於可能的危機。然而,他的新作卻換了個角度,詢問危機後的可能。
我在評論《灼眼的白晨》時,曾經以青春的痕癢為題,指出甄拔濤如何展開眾多尚未發生的可能;而在《未來簡史》中,我們亦陪著演員探討「未來1.0」、「未來2.0」等等眾多版本的未來世界。這些都與可能世界有密切關係,事件尚未發生,我們沙盤推演著事件發生的可能。但是,《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的女主角Charmaine第一句台詞,已經點出此作與前作在時間上的不同之處:「已經過咗一段時間,所以我可以話俾你聽發生咗咩事。」換言之,事情經已發生。不單止已經發生,而且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夠回溯性地指稱當初已經發生的事件,「所以我可能話俾你聽發生咗咩事。」
災難席捲生命的所有領域,包括語言。例如,德國哲學家阿當諾指,「自從奧斯辛威後,寫詩是野蠻的。」然而,齊澤克卻反指奧斯辛威慘劇後,如實記錄才是不可能。事件的後遺不在於敍述之中,而是在於言說的形式之中。按此推斷,當我們見到Charmaine的弟弟Kenneth因目擊一名男人嘔出自己內臟而失語,我們很容易便會認為這是一種創傷後遺症,彷彿Kenneth是因為無法好好梳理事件帶給他的衝擊,所以失去組織句子的能力。但是,劇情繼續推演,Charmaine與Kenneth離開了政府安排的遷徒地,回家。回家之後,他們過著某種意義上的快樂生活,那麼Kenneth理應痊癒,理應重拾說話的能力,不過他沒有。他依然不能說話,劇終之際當他想向觀察開口說話時,結果又再一次嘔吐。
也許,我們必須重新理解嘔吐的意義。嘔吐並沒有窒礙他的表達;相反,嘔吐本身正正就是他所欲表達之物。Kenneth並不是患上創傷後遺症,而是基於事件發生,他的表達方式從根本上改變。問題不再是:如果他沒有嘔吐,他會說些甚麼?而是:他的嘔吐本身表達甚麼?儘管他嘔吐,但是從來沒有嘔吐物,只是純粹的嘔吐本身,讓觀眾直接接收一股「未經消化」的感覺。Charmaine的情況也是相類近:巧合的是,解釋完Kenneth為甚麼失語、只能嘔吐後,Charmaine語鋒一轉便提起自己是畫家,是一個讓世界穿過自己的畫家:「呢個世界當我係一個過渡。每一件事物都當我係一個過渡。我裡面係空嘅。」或者,Charmaine的過渡之說,以及Kenneth的嘔吐其實都是同一回事:經歷事件後,世界與自我從此便不再一樣。
因為災難,所以必須樂觀
但是人未必敢於承認改變,人始終有某種惰性,我們總想好好維持日常生活,就像Charmaine所說,儘管災難發生,「一晚之後每樣嘢都回復正常好似無嘢發生過咁。如常咁過日子係最優先處理嘅。」人對於日常生活的執迷,彷彿是一架筆直前進的火車,即使路軌早已轉彎,但是仍然繼續盲目衝撞,鋼鐵鑄成的車輪生硬地與地面磨擦,直至車毀人亡。直至突破某個臨界點,事情才一去不復返:政府宣佈撤離,全部市民被迫遷到另一個城市。
遷移到另一個城市、母親因故離世⋯⋯儘管如此,Charmaine與Kenneth依然想回到日常之中。只不過,事件爾後,生活注定脫軌。他們在新城市所經歷的一切,不正是證明了這點嗎?他們被安置到某條屋邨之中,而只要他們一向別人提起他們的住處,便等同於向他人揭露自己的過去,沒有人再夠膽跟他們交談。所謂如常生活,頓成泡影,「我覺得我哋變成咗另一種物種。」
因為災難已經發生。正如我於文初所述,甄拔濤這套新作與舊作的最大分別在於,他不再詢問有多少種或然,而是詢問人應該如何面對確然。當事件發生後,我們缺乏的不再是可能性,而是確認的勇氣。我們需要勇氣確認自己處身已然的當下,承載著所有過去的當下。Charmaine與Kenneth回家,未必因為想回到過去,這很明顯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城市已經幾乎空無一人,升降機不再運作、商舖不再營業。他們很快便認清這一點。所以,他們選擇以另一種方式在沒有人的城市中生存下去。
有觀眾在演後談中表示,演出完結後覺得很悲觀。這可能因為災難的發生,也可能因為劇中的城市最後幾乎抹殺了文明。我們平時覺得核災離香港很遠,切爾諾貝爾或者福島都離我們很遠。但是核災實際上離我們很近,假如大亞灣核電廠發生事故,身處香港的我們未必能夠趕及撤離。本來從大陸遷徒到這個海岸城市的我們又能往哪裡去呢?我突然想起蹈海的陸秀夫與宋帝昺。
但是,《核災後的快樂生活》真的想呈現出一股悲觀的氛圍嗎?事實上,此劇在逼迫觀眾思考一條問題:拋棄災後的城市就等於能夠重拾日常生活嗎?消去種種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後,Charmaine選擇了面對確然的過去。災難、事件發生的強度可能擊潰了她,但是她卻看到另一種態度:「我變咗碎片。但係我同時同呢個世界分唔開。」零碎的自我,反而能夠時刻與世界同在。將近尾聲之際,Charmaine慢慢走進昔日的地鐵站,裡面全是當日犧牲了的亡靈,地鐵站已經成為歷史的載體。要走進歷史絕不容易,Charmaine必須承受著所有亡靈的呼喊,但是她日復日、慢慢地愈走愈深,直至黑暗擁抱著她:「黑暗係呢個世界最溫柔同柔軟嘅嘢。最黑嘅黑暗。無終止,無開始。」她終於擁抱著一切過去。
沒有隨時間掉淡的,是歷史。我們必須努力尋找可能性,只不過歷史未必存在選擇,轉左的人不會知道右轉的景況。因為選擇不在歷史之上,而是在於我們:否認然後歸於太陽照常升起的平凡,抑或承認然後開創新的日常生活。
因此,這是一種災後的樂觀,樂觀在於相信自己,相信世界。這是一種信念。也許正因為災後,人們才能夠確認災後的快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