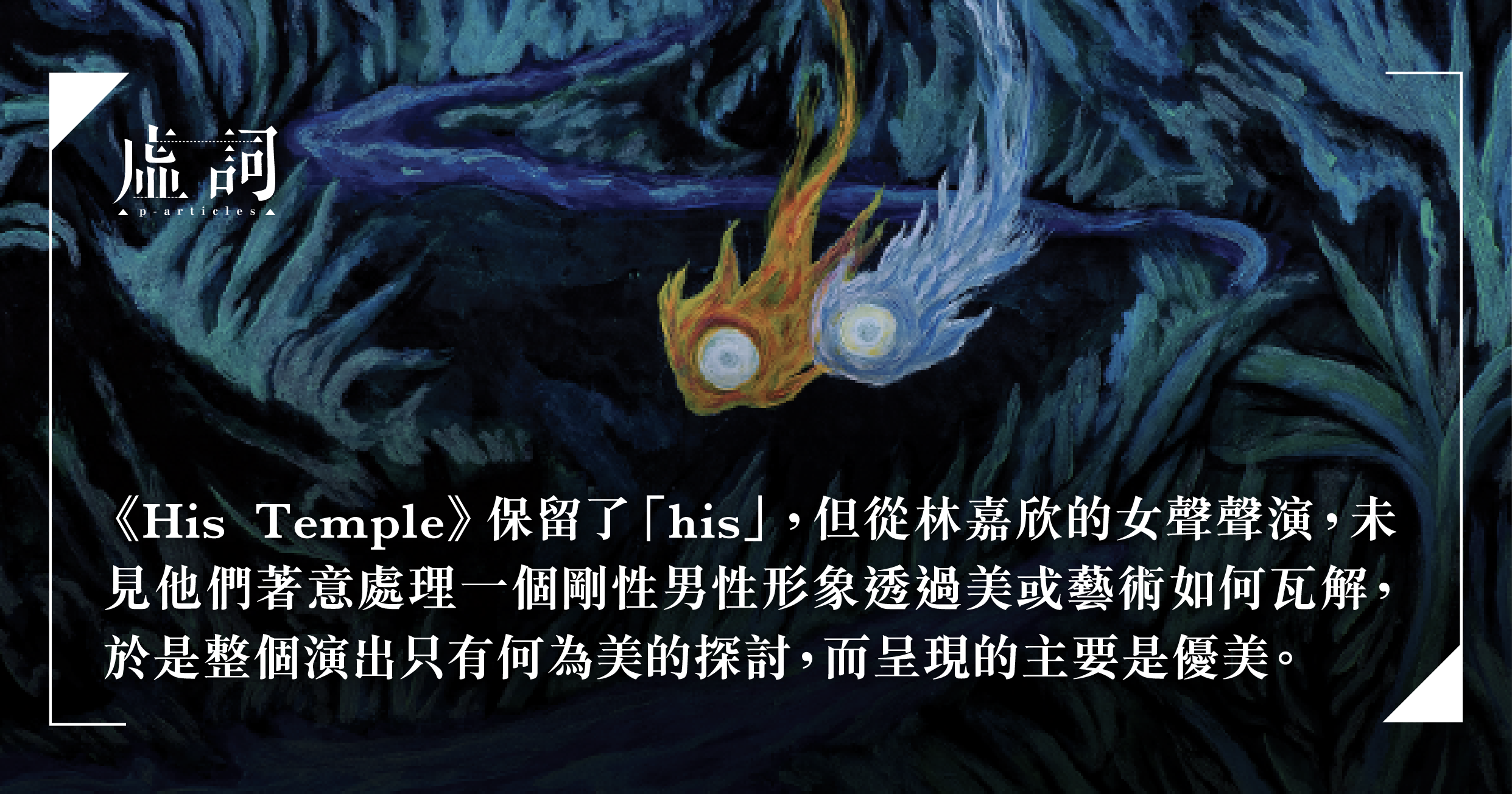暴力、性與死亡下,扮演不知悲傷為何物的小孩:讀安西水丸《青之時代》、《東京輓歌》
其他 | by 翁稷安 | 2023-08-25
在這靜謐、甜美的表面下,似乎隱隱潛藏著某種難以言說的陰暗。畫面之下佈滿著近乎與現實斷裂的縫隙,是安西水丸作品給我的一貫感受。這種張力隱匿在安西的插畫乃至文字作品中,多半處於模糊的樣態,在看似恬靜怡人的畫面、表現出大叔趣味的字裡行間,提供著無聲卻深沉的厚度。然而,翻開安西的短篇漫畫集《青之時代》、《東京輓歌》,卻能見到他在早期作品中,卻毫不保留地完全展露。 (閱讀更多)
吳煒倫、何爵天畢業作品8月放映:在電影理想中摸到臉黃肌瘦的真實
吳煒倫的畢業作品《転生 = Metempsychosis》(2000) 講述冷色系格調的頹廢都市中,人們都用機器幫自己洗去記憶、免除痛苦;至於何爵天的《FOUL》(2012)就藉一個中學生與其他同輩及師長的對抗,反思權力社會的種種弊病。如果說兩者都有甚麼共通,可能是有關自殺的情景,並獲電檢處評為「兒童不宜」。 (閱讀更多)
怕神仙眷屬也要歷興亡:電影《李後主》觀後感
影評 | by 戴侶 | 2023-08-23
任劍輝、白雪仙主演的電影《李後主》面世五十五週年,片主廖先生以最新技術修復本片,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再度放映。戴侶分享觀後感,圍繞其歷史與愛情的主題、于粦作譜的插曲,以及任劍輝把亡國之君的複雜情緒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演技,藉此追憶和悼念五、六十年代的明星,感歎他們巨額斥資的傻勁,只是一切已成追憶。 (閱讀更多)
【新書】《文學看得開(作品篇)》:短篇小說:因為短而產生無限可能
短篇小說作為較親近日常生活的文學類型,到底是如何興起?又有何特徵使然?鄧小樺在新書《文學看得開〈作品篇)》一一拆解,徵引中西作品,疏理其發展脈絡,指出短篇小說的核心在於結構和人物,但是作品的短小不能規限其詩意、深度及時間跨度。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