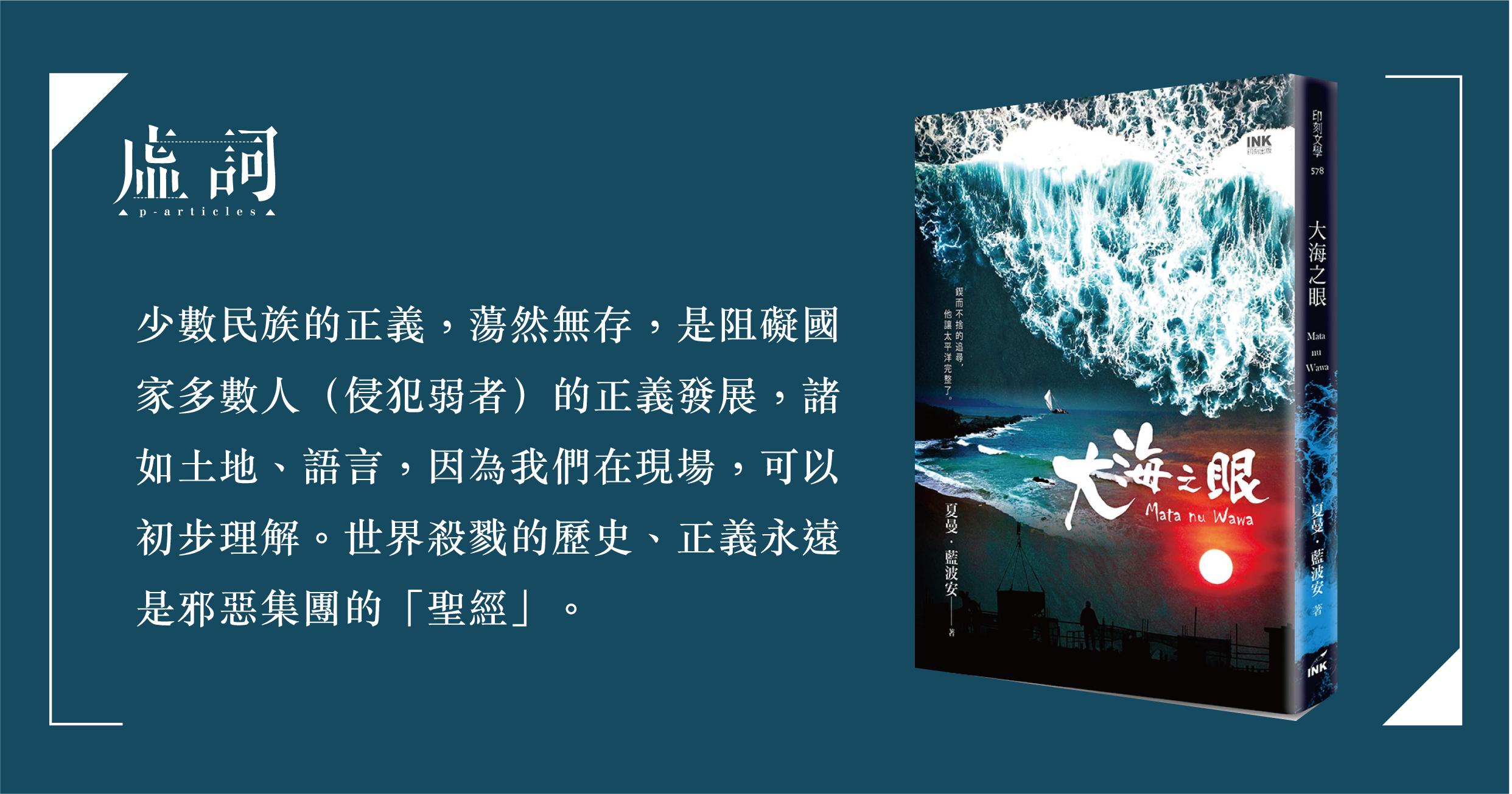【《大海之眼》自序】尋找生產尊嚴的島嶼——我在現場
「哇!真的厲害。」我們一群當時的蘭嶼國中的男同學在現場,目睹「這一幕」,我們共同發出的驚嘆號。
從1967年到1973年,我們認識了356「登陸艇」(軍艦)。356真的是勇猛的鐵殼船,它讓我們大開眼界。它的到來,我們的島嶼變成「國家」的土地、我們民族變成山地山胞,我念大學的身份後來變成邊疆民族。它的到來,帶來了漢族歷史上對少數民族不滅的暴力,阻斷我們海洋民族的對他者的友善。
《大海浮夢》(2014,聯經)、《大海之眼》(2018,印刻),都是我在蘭嶼國校、國中時期,就已經在腦海裡幻想可以實現的願望。這個想像,就是356,「我在現場」給我視覺上的震撼,透過視覺的想像,轉換孕育成我個人的「夢之旅」。本書的序文,不是要探索356登陸艇帶給蘭嶼島整體性的劇烈變化,而是從世界殖民史的角度,理解一個殖民者的國家武力,透過其自我圓謊的行政網絡的「哲學」,合理化了國家暴力的圖章,以及更多的「歧視政策」,國際化的正義。少數民族的正義,蕩然無存,是阻礙國家多數人(侵犯弱者)的正義發展,諸如土地、語言,因為我們在現場,可以初步理解。世界殺戮的歷史、正義永遠是邪惡集團的「聖經」,血淋淋的雙刃寶劍,何來轉型?
我想說的是,356每一次在我部落灘頭登陸,每一次都會讓我浮現「消失在人世間兩次」時所見到「單桅帆船」的幻影幻象,彷彿是我自己命格的預兆,為甚麼?為甚麼會實現呢!
我不知道我蘭嶼達悟籍的同學,或者是你(妳)是否曾經有過這個「困擾」?蘭嶼國小辦公室裡的世界地圖,太平洋(大洋洲)是被切一半的,我看不見完整的太平洋,我要問的是,「太平洋」為甚麼會被漢人學校切一半,關於這一點,一直很讓我難過,從我十歲開始,真的一直很難過,極為困擾我。直到我人類學研究所畢業,去了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國,在拉洛東加島(Rarotonga,從紐西蘭的奧克蘭機場向東飛五小時)的小書店,買了一張屬於大洋洲的世界地圖,赫然看見了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完整版的世界地圖。
對我而言,才遇見了「太平洋的尊嚴」。我心魂真的才回到喜悅,才解開太平洋被切割的疑惑、痛苦,是漢人不喜歡太平洋嗎?還是因為台灣、中國大陸在太平洋的邊緣,才把太平洋切一半嗎?這是答案嗎?我不知道。當我打開了那張世界地圖,我高興得哭了,我問自己,我為何如此在意太平洋被切割呢?那時我已經48歲了,難過了38年,原來我屬於這群人,這群島嶼,這汪洋一片的海世界,海洋民族。我也才頓悟,在蘭嶼國校念書時,老師極力嚇阻我們去游泳的理由,就是那群被放逐在蘭嶼的漢族老師,他們恨死了海洋,「鄉愁、鄉仇」。
對於居住在太平洋上的任何一個島嶼,大航海時代,殖民者的降臨,無論是麥哲倫[1]在1521年來到了關島(Gua Ham),揭開了藍色水世界的謎語,或者是,一次、二次大戰之後,所有的島嶼開始被洗牌,包括語言加入殖民者之語彙,所謂的與原始環境共生的「尊嚴的活著」的文明,瞬間轉化為殖民者飯後叼根雪茄的「笑話」,運用356「刪除民族記憶的圖騰」。
西方來的神父來到我們島嶼後,他的「上帝」解構了我們的「天神」疼愛環境的潔淨儀式,說祭祖儀式是上帝不允許的活動,我於是開始質疑所有外來者來我們島嶼的目的——來歧視我們的,我也失去了童年知性記憶的美麗,不可能再複製的環境潔淨(驅除惡靈)的儀式,外來宗教、殖民國帶來愈多「東西」,包括政策(全球的少數民族),帶給許多許多弱勢民族內部的分裂離子愈複雜,部落民就愈不幸福。在所有我走過的少數民族的領土及海洋民族的島嶼上,都獲得一模一樣的答案。這是不需爭辯的事實。
我在現場。「興隆雜貨店」也因國家的「行政轉型正義」登陸到我居住的部落,搶地開店,不僅來了許多比我頭髮多的雜貨,也帶來了詭譎的空氣氛圍。胖胖的、十分肉感的閩南女人,化解了中國國民黨黨員與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她店裡飲酒解鄉愁,為了自己的「黨」爭辯到動干戈的剎那間,她以女性的「雙峰」瞬間融化大陸來的「雙黨」深深深的鄉愁,再次讓他們坐下來暢談中國人民歷史的偉大。我在現場,當下無法理解雙峰的「解藥」在哪,但我開始預感356以及「興隆雜貨店」將帶來遮蔽陽光的烏雲,模糊了我們民族的視覺判斷,但也啟發了我,讓我立志靠自己考高中、大學。
高中時,我寄宿在天主教在台東培育偏遠學子念大學的「培質院」,高二升高三的輔導課期間,神父跟我說:
「我要訓練你成為蘭嶼島上的第一位『神父』。」
我聽了差一秒就暈過去,於是哽咽地回答:
「我要當漁夫,不要當神父。」
「沒出息。」神父怒道。
許多「文明人」喜歡以她(他)們的核心認知當弱勢者的「馴化者」,無論他們說當飛行官、當律師、當醫師、當牧師、當老師等等,我的心魂絕對是拒絕的,後面這四個「師」,在我個人的認知皆歸類為騙人的職業。漫漫之路,不長也不短,當我大學畢業,回到蘭嶼定居,寫了一本《冷海情深》給神父,神父當下題字寫道:
「返璞歸真。」又說:「神父看不懂你寫的書。」原來神父也看不懂海洋,我說在心裡。他把書退還給我,歧視我的眼神依然銳利。
2005年一月,我在南太平洋庫克國的首都拉洛東加島的市集與我的房東閒逛,那兒有個開放式的搭篷舞台,給不同宗教信仰的牧師、神父傳誦西方上帝的教義。我看見的結論是:西方白人牧師或神父,並不因為當地人的改信,當了神父,當了牧師,即使是穿著共同的宗教褓衣,白人眼裡高高在上的傲慢依然滲透著很深很深的種族歧視。我信仰多元的神,但我更厭惡歧視眼神背後的傲慢,畢竟那絕對不是上帝的旨意。
我不是在緬懷逝去的童年,緬懷在台東中學,青少年的美好滋味,也不是在抱怨在台灣西部、北部的苦力生涯,而是在喜悅自己迸出的血汗生涯,許多的際遇,許多的故事,是自己感受,自己承受,也自己感動。
當下,我書房隔壁住著帶我去嘉義做苦力的,帶我進入水世界獵魚的堂叔,老海人洛馬比克,他深夜每一次自己灌醉自己的生活模式,我看在眼裡,叔叔生活的循環模式,我跟他的數字距離約莫是二十餘公尺,然而他幾乎每一次對著米酒瓶,用力大聲嘶喊叫道:
「你把我灌醉、你把我灌醉……你最壞,你最毒。」事實上,是他自己灌醉了自己,每一次臭罵米酒瓶,每一次的深夜,每一次深夜都讓我哭笑不得,然而,這句話,卻讓我身為作家有更深的人生感悟,這樣的人,你在台灣、南北美洲、格陵蘭任何一個原住民族的部落都有,我都遇上了。我是作家,我喜歡探索「尊嚴還活著的人」,實寫真情探索者,努力中。
我在現場。興隆雜貨店,那位十分有肉感加性感的老闆娘,1971年,洛馬比克每一次幫她搬運台灣來的貨輪上的雜貨,老闆娘都給他啤酒喝,每一次他都拒絕。1984年,他從台灣回蘭嶼定居,開運送核能廢料的聯結車,開始喝一箱又一箱的B魯(啤酒),到現在喝一杯20CC的米酒就醉了的他,「你把我灌醉、你把我灌醉……」,我不敢尋找「那個」答案。那是我們集體性的長篇小說。
他每一次心情好,在午後,腋下便夾著會自動變調的吉他,自彈自唱,唱著他40年前,拿吉他教我們唱的歌「海~鷗~飛~翔,潮起、潮落……」。我自己終究又被他逼著笑了,但他不曾知道我笑了,因為他是一個人的世界,不是世界裡的一個人,他的黃金歲月被遺忘了,被遺忘得非常乾淨,但我忘不了他,幾年後,我或許會親自埋葬他的肉體,但我不會土葬他給我的傳統性的海洋知識。
當我一個人站在格陵蘭努克市某個大賣場的角落,觀察幾位依奴依特人兜售簡陋的二手三手貨,他們相互傳送一個杯子,從1000CC裡的保溫杯倒進一個鋼杯,那是黑咖啡。每一次每一個人接過鋼杯,雙手掌首先是揉一揉鋼杯,因為鋼杯有溫度,可以溫暖他們乾澀的手掌,也溫暖他們的心肺。我靜靜地觀察他們的表情,那個景致際遇,在台灣的冬季,你也可以在阿里山、新竹五峰鄉、宜蘭大同鄉,任何一個山裡的部落,可以發現圍著火爐的一群人,在火舌上摩擦手掌來保暖,我們不知道,他們討論的世界是甚麼?但是,我很肯定的說,他們的世界距離冰川浮冰、高山地表的感情最近,尊嚴的活著是我們這群人的「聖經」。
我在現場,我淺淺的微笑了,終於把太平洋的完整容顏,懸掛在我獨立的書房,告訴我的航海家族之魂:「我們的世界完整了」,我是世界島嶼作家,海洋民族的海洋文學家。
完稿於蘭嶼島
2018年8月17日
[1] 費南多.德.麥哲倫(葡萄牙語:Fernão de Magalhães;西班牙語: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葡萄牙探險家,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險。1519至1521年率領船隊首次環航地球,死於與菲律賓當地部族的衝突中。雖然他沒有親自環球,但他船上餘下的水手卻在他死後繼續向西航行,回到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