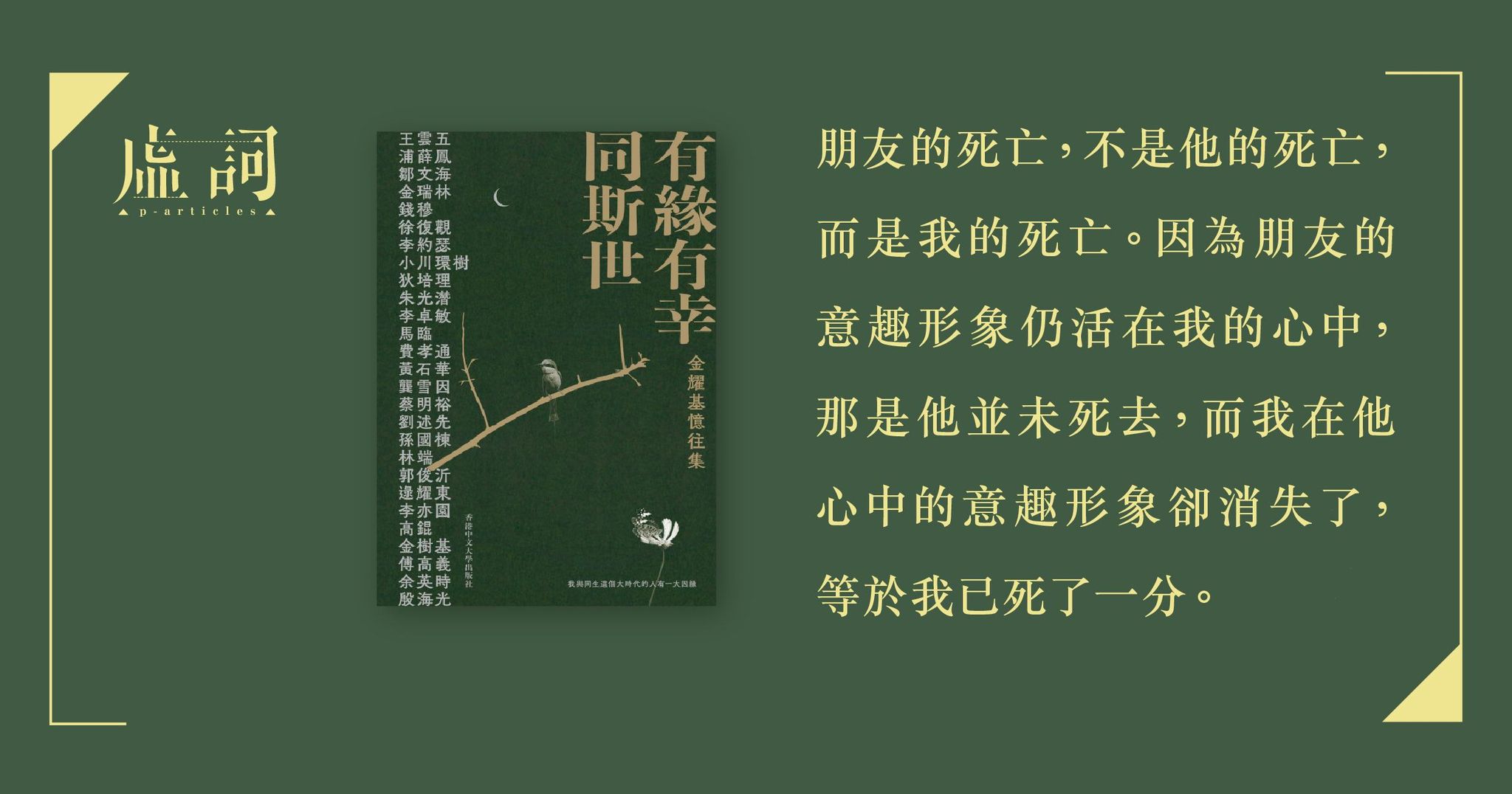【新書】有緣有幸同半世——追念一代史學大家余英時大兄
其他 | by 金耀基 | 2022-04-18
8月5日上午十時許陳方正兄來電,說余英時先生走了。他說是剛才余夫人Monica(陳淑平)通知他的。Monica打電話給金耀基,電話不通,接著就致電陳方正。我聽後震撼難過,隨即打電話到普林斯頓余府,Monica電話中平靜地告訴我,余英時於8月1日晨(美國時間)在睡夢中安詳去世,火化後已安葬於普林斯頓他父母墓園之旁(墓碑待立)。她說,7月31日午夜我與余英時通話是他生前最後的說話了,內子元禎在身邊,黯然無語,我也只說了要Monica保重的話。Monica是名門淑女,在我夫妻眼中是一位堅強明理能幹的女性,余先生入土為安後,她已收拾心情。她說余英時是「無疾而終」,是有福氣的,在居留海外的學者中,他是幸運的。
掛了電話,元禎靜默地看著我,我歎了口氣,沉沉痛言:「這就是人生!」是的,8月1日近午時分(香港時間)我與英時大兄有一次通話。近月來,我們有幾次通話,每次他都會說,疫情不寧,老朋友見面已難,多通通電話,大家保重。這一次通話,說的也是些保重的話,我覺得他很疲乏,有的話也聽不太清楚,我也不忍要他說大聲些。通話後,我對元禎說,我覺得余先生有些無力,說話也不似平時般清晰,我說我是有點擔心的。但是,我是絕想不到這會是我們最後的訣別,我是絕想不到他當夜上床後就在睡夢中離開人間了。
8月7日,Monica來電,說普林斯頓大學為余英時降了半旗,一代學人余英時已走進歷史。
意趣形象仍栩栩如生
這幾天,有不少日常事務要做,生活與往日無異,但獨坐書齋,每想到我再也不能拿起電話與英時大兄有那怕是一分鐘的交談,我感到的是無比的失落與自哀,這使我記起錢穆先生的一段話:
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那是他並未死去,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消失了,等於我已死了一分。
英時大兄走了,人天已經永隔,但英時大兄的意趣形象在我眼中栩栩如生;他贈我的書,他給我的信,稍一翻閱,便覺他的言行容貌如在面前。余英時長我五歲,高我小半輩,我常以先生稱呼他,並尊其為大兄。余英時專志於歷史學,我則以社會學為志業,但因余熟悉社會學,我喜歡歷史,而彼此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與中國發展,故我們的興趣時有交集,且多共同語言。原來我們有各自的人生軌道,但我們的人生軌道卻在香港中大的新亞書院相接。1970年我自美到中大新亞執教,余英時在1973年自美回港,擔任母校新亞校長,1973年我們在新亞由彼此有所聞而成為相識(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語我早就看過我 1966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一書),1974到1975年,我們共同參加中大成立以余英時為主席的「改革小組」(全名「教育方針與大學組織工作小組」)。小組成員有馬臨、邢慕寰、陳方正、傅元國等人,小組的任務是為大學的未來發展提出具體建議,重中之重是要對大學本部與書院之關係作新的定位。
無疑地,小組的改革任務不止是技術性的,它涉及到理念、價值觀以及權力與利益,故小組成員(特別是主席余英時)從不低估任務的艱難,但各人都覺得義不容辭;並且深深以為可以為大學(當然包括各書院)做一件極有意義之事。是的,小組工作初起之時,校內校外,已是風聲雨聲不絕於耳。小組主席余英時對於新亞書院的感情是眾所周知的,而他確也沒有絲毫輕忽書院的訴求,自始至終,他與小組成員都以達到大學整體發展最大化為思考的依歸。當小組工作完成時,余英時的心地湛然,他確沒有料到小組報告發布後會引發校內校外如此激烈的批評與爭議,尤其是新亞董事會的強烈反對,新亞廣場上甚至出現了道德性的言詞譴責改革小組,特別是小組主席余英時。無可諱言,改革小組的工作是失敗了,余英時個人更受到極大的誤解與委屈。但我必須指出,改革小組的重要建議,後來為第二個《富爾頓報告書》所接受,實行以來,中文大學近四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發展。改革小組解散之時,我並無灰心,只對古人「理未易明」的道理深有體會了。而在改革小組所經歷的煉獄式的過程中,我有機會深刻貼近地認識了余英時這個人,他的公心、正直、寬厚及與人為善的處事作風,我是由衷地欣賞與敬佩的,我們由「戰友」變成了「無不可與言」的知己友好。新亞三年,我們由相聞而相識,由相識而相知相重。工作小組結束後,我與家人去了劍橋大學(我以訪問學人身分在英國劍橋十個月,在美國的MIT二個月)。安定後不久,余英時大兄與Monica及兩個女兒來劍橋看我與元禎,余金二家頗得共遊劍橋之樂。在天清地寧的劍橋,余英時已把改革小組的事置諸腦後,心安理得地回返美國劍橋的哈佛,做他喜愛的教研著述。
上世紀七十年代劍橋別後,余英時與我,雖然相聚時少,分別時多,但七十、八十、九十年代,記得我們在美國緬因州、紐約市、新加坡等地數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碰面,在台灣則多次在各種會議中歡談,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之十餘年,更定期的在院士會議(二年一次),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會(每年二次)見面,會後聚晤都在酒店客房品茶吹煙(我未見余英時吞煙,暮年之際他已遵醫戒煙),傾懷暢談,餘念不已。2014年,余英時獲第一屆歷史學「唐獎」,我與元禎受邀出席頒獎盛典,那一次是英時大兄最後一次去台北,記憶中也是我與他在東方最後一次的歡聚。
長年以來,余英時在美國,我在香港,但憑著「見信如面」的書信和萬里聞聲的電話,兩地雖大洋遙隔而愈覺友情之可貴。2004年3月他在信中說:
弟年歲愈高,愈覺人間最難得者唯親情與友情耳,其他皆為浮雲過眼,不足惜懷。
暮年之際,彼此關懷,益增思念,今年英時大兄九十一歲,我八十有六,真是「老友」了。7月31日午夜我們的最後一次通話,正是友情老了後平淡的關懷。
我與英時大兄半世紀的相知相交,是有緣,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深感「有緣有幸同半世」。
師從錢穆的史學之路
余英時在第一義與最後義上,是一位歷史學家,英時大兄之走上史學之路,與他在新亞書院師從大史家錢穆是一決定性的機緣。上世紀五十年代,余英時在香港五年,正式在新亞上錢先生課不過一年半,但課外請益小叩大鳴,啟發最多。之後在新亞研究所仍以錢穆為導師,遂得深刻了解錢穆的史學道路(「以通馭專」),窺見了治史門徑,並體認到錢先生一生治史的終極關懷(中國文化的存亡),余英時得之於錢穆夫子者實多,他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之悼錢穆文中有言:「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入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余先生對錢師的尊崇,終生不渝,師生二人最後都成史學大家,可謂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美談。
余英時新亞畢業後,因學識俊秀,被推介到哈佛深造。在哈佛,余英時又進入一個新的學術世界,他飽讀西方史學,直探西方史學堂奧,又旁及哲學、社會科學,眼界更為擴大,在有西方漢學「看門人」之稱的楊聯陞先生指導下,完成〈漢代胡漢交通史〉博士論文,奠定了他在史學上的地位,相繼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常春藤名校執教。數十年來,春風化雨,培育了無數史學人才,不少學生才華縱橫,已成中國史學界的領軍人物。余英時到了晚年,隱然已是新一代中國史學的北斗泰山。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余英時之成為名重海內外的當代史學大家,與他七十年代重返香港,決定此後以中文著述一事有關鍵性的關係。他曾語我:「我寫的是中國史學,做中國研究的外國學者應該會讀中文的。」余英時自認用中文書寫遠為舒暢稱心,他的文才與史才都是第一等的,與錢穆一樣,他倆都是文史雙修,相得益彰:自七十年代後,余英時的中文著作如井噴式的出現,一部接一部,不但史識亮卓,而且文彩煥然,無一部不風行於華文世界,他的重要著作:《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以及鉅製《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與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的思想史扛鼎之作。讀者可以見到他治學方面之廣、深,可謂通古今,兼中西。難能可貴者,他在思想史上,每每有意無意中開闢了研究的新領域,並對歷史的老題目,以當今的學術觀點作全新的現代詮釋,這當然顯出他的書寫與五四時期的學術趣旨有所別異,與乃師錢穆的著述也有不同的史學風貌了。在根本的史觀上說,余英時是傅斯年的科學史觀外,別開生面,治史之目的不求歷史的「規律」,而在深探歷史的「意義」。他的百千萬言的史學論述,不啻為現代詮釋學史學開闢了一片漢學的新天,這就宜乎余英時在2006年獲美國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終身成就獎」及2014年獲頒台北的唐獎第一屆「漢學獎」了。
胡適、殷海光、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筆耕一生,終老不止,在我眼中,他是「我書寫,故我在」的一位學者,英時大兄的書寫多彩多樣,最可見他的人文興趣之廣、人文關懷之多與人文修養之深。他能寫《朱熹的歷史世界》這樣的皇皇巨制,也會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這樣的紅學文章,而最令人驚艷的是他寫《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余英時以他特具的詩心詩才,一一破解了陳寅恪所寫一個典故包著一個典故、充滿隱喻的詩文的密碼,一一呈現還原了這位近代大史家九曲迴腸的心理世界。余英時之能寫出如此石破天驚的名篇,是因他有寫詩的「別才」(他曾語我,錢穆夫子就曾說他有此「別才」),我記得科學與人文雙修的陳之藩兄,不止一次對我表示,他真羡慕余英時寫古詩的本事。
當然,在諸種書寫中,余英時最風動當代的是他一篇篇彰揚、守護民主自由的凌厲文章。在這方面,他頗像胡適。胡適終其一生,從沒有動搖他對民主自由是文明社會基石的信念,余英時是「後五四」時代的「知識人」(他不喜歡「知識分子」的稱謂),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批判,也有繼承。他批判的是五四反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他繼承的是五四倡導的科學與民主,民主、自由是他一生信守的基本價值,余英時與五、六十年代台灣的殷海光一樣,都是真實的自由主義者。胡適、殷海光、余英時是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具標桿性的人物,他三人都是學者,都不從政,卻從不忘論政。這是現代知識人的公共關懷,也是中國讀書人「為生民立命」的偉大傳統。我生也有幸,與這三位非凡人物都曾在這世上遇見。我不識胡適,但我在學生時代,讀他與梁任公的書最多,並親耳在台北聽過他兩次演講,一派學人風範,依稀可見五四當年光采,他去世後,我曾撰長文悼念;殷海光先生是我台大老師,但未上過他課,殷先生晚年因看了我的論現代化之文,囑陳鼓應、陳平景到商務印書館邀我到殷府喝咖啡,自此與殷先生成為忘年深交,殷先生於我是平生風儀兼師友。余英時未見過胡適,因寫《重尋胡適歷程》,成為胡適的隔代知音,余英時也未見過殷海光,但他曾在以殷為主筆的《自由中國》發文,對殷海光自有會心。與英時大兄相處時,我們多次談到胡適、殷海光兩位前賢。
翰墨之緣
我與余英時先生的半世交往,可記之事甚多,但就我個人來說,自2004年中大退休迄今的十七年中,最難忘的是他多次對我書法的評論和鼓勵。
我退休後第一時間就拿起毛筆,重新踏上少青年時代開啟的「翰墨之道」。一年後,自覺我的書法已有些「書趣」,遂寫了一幅送贈英時大兄,因為我一直認為他與錢穆夫子都能寫一手好字,並且也喜愛書法。2005年8月他來信說:「前日收到墨寶,暢酣淋漓,既感且佩,弟早知兄深具文學與藝術秉賦,今稍稍臨池,書法天才即破繭而出,誠所謂賢者無施不可也⋯⋯」英時大兄這樣的話對我是很大的鼓勵。2007年2月英時大兄來信:
今天收到賜寄我筆四枝,感激之至也歡喜之至。兄是最可靠的真朋友,一托便立即勞神費力,以最高速度辦成。弟在今日亦唯有得之於吾兄也。前承賜墨寶,已見兄法書遒勁,前幾天又看到兄為《香港近代中國史學報》署簽,龍飛鳳舞,不勝欽羨之至。細看筆法,又無意中發現兄所用之毛筆似亦不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人誠不我欺也。筆史有一說,王羲之所用之筆,後世亦失傳,故後人不能追摹,此未必可信,然亦未可忽也。近來弟頗有人索書,向來所用之筆已舊,故為此不情之請,尚乞勿罪……
2010年余英時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化史通釋》,要董橋兄作序,要我題簽,我們當然遵囑。英時大兄在出版後記中說:「慨然接受了我的懇求,董橋兄的序文和金耀基兄的題簽不但使本書熠然生輝,而且讓我深切感受到數十年友情的溫暖。」余英時心中最重的就是友情。
我八十歲之年(2015)寫了一幅李白的〈贈孟夫子〉寄給萬里外的英時大兄,蓋欲借李白詩以表我對「余夫子」(是年他八十五歲)之遠念也。他收到我書之長卷時,他在越洋電話中說:「兄書有一家面目」,並說,「我雖不善書,但我是懂書的」。其實,英時大兄絕對是「善書」的,看他贈我的書法條幅,圓勁秀挺,有「讀書萬卷始通神」的筆墨,他的自謙自信,一如東坡居士所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
2017年3月,香港集古齋的趙東曉博士為我舉辦一場「金耀基八十書法展」,是年我八十二歲,是我父親逝世之年齡。父親是我書法的啟蒙師,他對我是有期待的,我之舉辦此次書法展,實有對父親作一交代之心。開幕式中,萬想不到在董建華先生致詞後,輪到主禮嘉賓董橋講話時,他從口袋中緩緩取出一紙,竟然是宣讀了余英時託他宣讀的一封賀書:
耀基兄的書法是他藝術人生的最圓滿的體現,卻一向為他的學術志業所掩蓋,退休以來十餘年間,書法竟成為他的生活中心,勤習之餘,卓然成家,海內外雅好金體書的人,於是也越來越多,但是我不願將書法從他人生中完全孤立出來。藝術精神貫穿在耀基兄的全部生命之中,書法不過是其中的一環而已。事實上,不僅他以「語絲」為名的所有散文是藝術的化身,而且他在百萬言的學術論述中,也時時流露出藝術的光芒。我們相交四十多年,在記憶中,每次晤聚都自然而然地引出我發自內心的愉悅,好像經歷了一次藝術欣賞一樣,我在室中走動,偶爾看到他贈我的條幅,但我所見到的卻不是書法,而是書法家本人。賀 金耀基兄八十書法展,敬煩董橋兄代為宣讀。
余英時
2017年3月14日
余英時先生對我的為人治學,特別是對「金體書」毫不保留的讚譽,詞真而美,意深而切,非深知我、厚愛我者,不能有此文墨。英時大兄這篇從天而來的賀書,非我事前所知,特別令我感動。其實,他對我之厚愛,常不語我知。1994年,我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事前他與許倬雲、李亦園等院士聯名提我為院士候選人之事,我卻全不知情。
今年(2021)新春時節,我寫了一幅蘇東坡的《蝶戀花》贈英時大兄,3月15日,他寄來一短信和一本英譯本《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信中寫道:
耀基兄元禎嫂:
恭賀新年,英時淑平同拜。
承耀基兄書贈東坡蝶戀花名幅,不勝驚喜。耀基兄已成書法大家,真所謂「一字千金」,弟得此榮賜,不知何以為報,唯有置之案頭,時時賞玩耳。寄上英譯本拙作一種,聊以為友情之紀念……敬祝
撰安
弟 英時手上
2021年3月15日
這是我收到英時大兄的最後一信(平時多用電話,4月18日給我的是唯一的「傳真短簡」),摩挲手跡,滄然無語。我們相交四十八年,有過無數次的歡快之聚、有緣有幸同半世,何其美哉!但如今英時大兄已駕鶴仙去,走進歷史,融入星空。我再無與他論書談天樂,問蒼天蒼天不語,何其痛哉!我不由又想起錢穆夫子之言:「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那是他並未死去,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已消失了,等於我已死了一分。」有緣有幸同半世,畢竟也帶有我無比的遺憾和自哀,這就是人生。
2021年8月
《有緣有幸同斯世:金耀基憶往集》
作者:金耀基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