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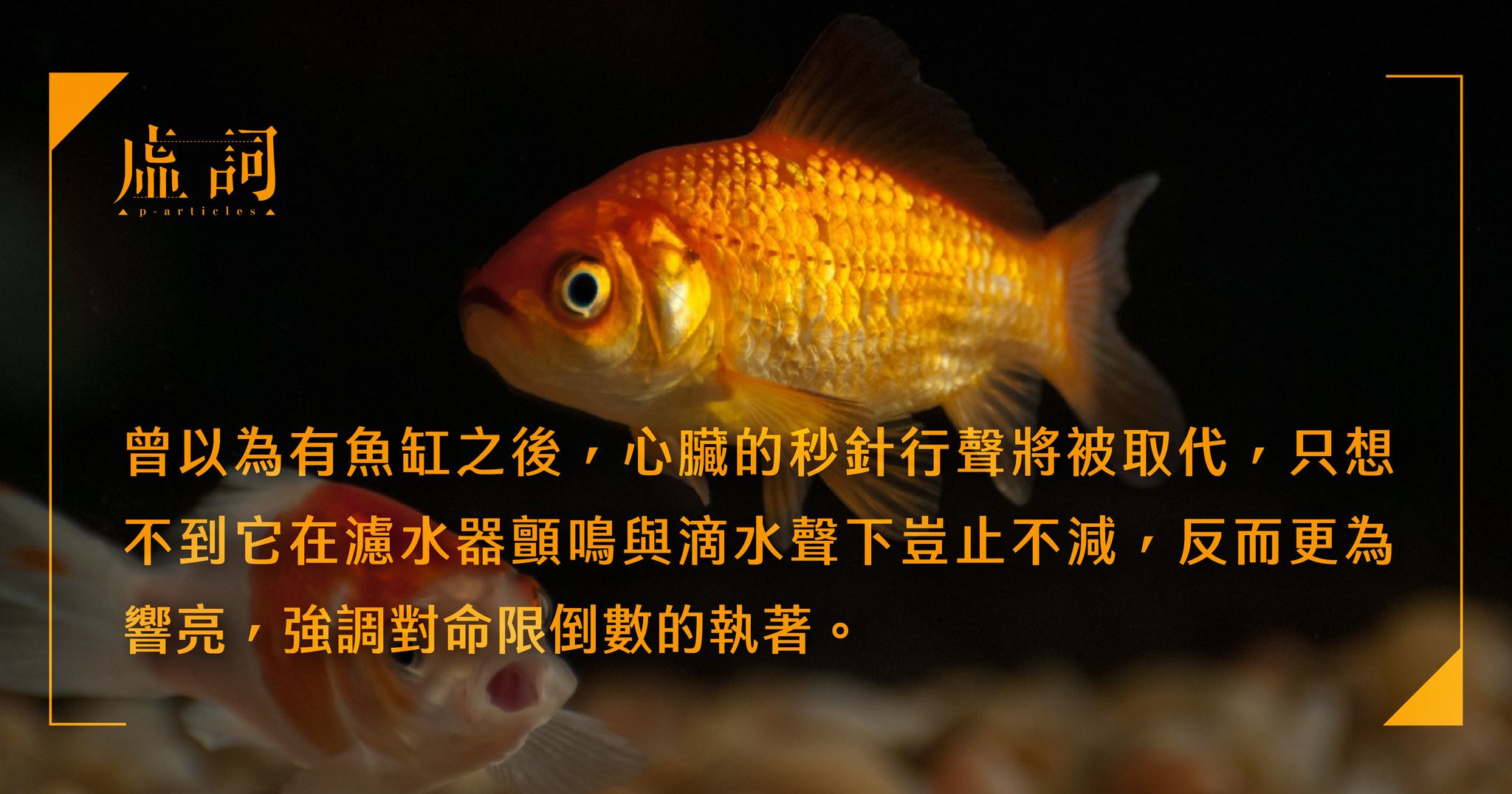
240400864_4283402115089573_3229718199629461229_n.jpg
在那些仍未置放魚的日子,夜晚,我合上缸蓋、滅缸燈,垂聽氣泵在混凝土的空氣中吞吐泡沫,揚起兩串上溢的水鏈。近入睡時分,便以重複的掌姿,掩上房門、熄燈;以相應沉緩的節奏,闔眼、凝視眼臉下幽深茂密的血管叢林。如此一層復一層,俄羅斯套娃似地,閉上某層空間,迎來黑暗那禮袍般的環形幕降。
魚缸囚困的水,房間裡折疊的我,眼眶中埋伏的黑珠子,因著被包覆,而處於相似的位置。
我們是三個秘密,在黑色裡蹲下來捲縮自我。
後來有了魚才發現,我和魚大概才是同質的。至於水,它們同空氣、聲音一樣,處於施力一方。對於我來說,魚不是有腮無四肢的脊椎動物亞門,卻屬物的一種。物,是超白玻璃缸的內部寄生物,與藻類、爬螺同階,其重要性低於玻璃缸,略高過底部紅砂,與人眼、與我混黃的血絲眼珠呈水平關係。
在有魚缸以前,閉眼後,側壓在枕頭上的右耳,常聽見秒針倒數。睡房沒有鐘,我始終深信那是一隻無人可見的手錶,埋在床褥深處的纖維組織裡,如海床的沉船殘骸,因鏽跡與青苔而年老。直至把手貼在胸口上,形成一個環,才發現心跳的脈壓沿路一躍一躍蕩至耳膜,發出滴答均衡的,富有情緒與肉體溫度的聲音。我於是把它命名為心跳的耳鳴。大概是身體內在有其一套完整的意志,擅自計算餘命。這樣輕聲的呢喃,在那些遺忘生命的夜晚,顯得格外清晰。
是第一次認真養魚才耳聞「養缸」、「養水」的概念。養魚的老手,會買幾條易逝的品系,作開缸試水之用。買回魚缸後,消毒乾淨,鋪平底砂、倒入經正午太陽暴曬的淨水,按時注射硝化菌、除氯劑,依次安裝加溫器、水泵、過濾儀、開缸魚,讓水以一種存活的姿態,如一頭會呼吸和流動,懂得親近與邪惡的活獸,在缸裡緩慢成長。魚的糞便和餌食將成為菌類溫床,死魚可作測量儀警惕水質不穩。一至兩星期後,缸內的細菌將以極其繁榮豐盈的面貌填滿水怪內部,建立近乎人體內部的血管通道。待水草、益菌、酸堿度及含氧量平穩和諧地鏈接扣合後,才放魚,將那種可堪稱作寵物的魚,與玻璃石頭一起倒進去。
小時候養魚,是祖母推卻和敷衍的手段。既不能養貓狗,便退而養可存放在小水瓶裡的生物。從不認為養魚有何可喜,亦不覺牠們張嘴獲食的姿態可愛。神仙魚細看會暴露皮下骨骼與內臟的紫紅,無鱗表皮像蒸熟的鯧魚,具銀白泛亮的滑膩觸感,彷彿在警告,如此膚色構造不應在燈光下袒露。
我和嫲嫲都沒有聲張,或早已默認養魚,是一星期內便結束的枝節意外。證據是,我已不能記起牠們活著時做過什麼,露出怎樣一副呆滯或怨懟的顏面,以什麼姿態游動、操控尾部肌肉、蠕合嘴唇。
我只記得牠們死了的樣子。
死透頂了的,發霉繼而腐爛溶解,支離破碎的樣子。
那是我活著以來最接近死的一刻。沒有布帛、花、四方盒的封閉和裝飾,一個停止運作的機體在水底逐漸分崩離析,熏臭的體液被水流沖刷乾淨,硝化菌分解淨化。留下視覺記憶的,是那從活體變成殘屑,進而被扔掉而深化象徵的過程。
嫲嫲眼睛看不清楚,我曾目睹她替一個已無活魚的缸投食,缸角邊沿漂浮著數天來吸水泡發的魚糧。一尾卡在濾水器吸頭的死金魚被水流來回吹拂,濕爛的尾巴靈活而富生氣地擺動,鱗片已稀疏發白,逐片豎起像剖絲的刀器。是那些排洩物深綠,肥胖笨拙的凸眼金魚。在疏於照料的綠色缸水裡,它恐怕不是最後死去的一條,因那顆裹在透明果凍裡誇張的巨眼已被啄食無幾,剩下洗刷得純白浮腫的凹陷洞口。
很久以前,我已驚異於魚尸的銀光與潔白。彷彿他們才出生已是冰塊的質地,為躺在街市冰床上的命運複習。這種對死的自覺使我凝視它們時,總似中年婦女買菜,抓起魚尾,瞇眼掂量其肉質。
我有長年透過書寫屠殺魚類的自覺,視魚為實驗體、肢解成鍵盤聲與黑白方正的筆畫結構,作為譬喻物、情感觸動儀、一顆遙控上慣用的按鍵。書寫它們,已像復刻木版畫,流暢滾過凹凸面的染色轉輪,其下木紋縱橫的硬底部上,一隻紋理粗糙、眼球破損的無品系平面魚,圖鑒一般,永恆被印刻和複製、如標本如擺設徹底冷卻生命。
這恐怕是我最後一次撫摸魚的尸首那滑膩的表皮了。我嘗試溫和的目視。這是一篇對於一切從不活著的魚物群體哀悼懺悔及告別的文章。
這次,我給水族箱裡,每一尾形跡相似的熱帶魚命名,以山河與家鄉作牠們的依歸。死了「北歸」、「三峽」、「南渡」,逐一刪去名單上的蒼白詞彙。浸在水中數天的尸體腹臉泛白,吸在紙巾上化成一灘扁平物,傳出冰箱深處凍結腐爛、冰涼潮濕的抑臭。這樣計算尸體的點名動作,畫一個剔號的迅捷速度,筆尖刮過紙張時的輕快,使人權力高漲,彷彿可把死亡撮起來捏在兩指間壓碎。那碎裂的聲音,令我憶起新聞報導右列終日橫桓的確診數字,以及祖母那一聲聲宣告的輕呼:七十二個。昨天三十六個。比上午多四個。明天,明天會是多少?而我在一旁為詩詞打剔如登記停尸間床位。
一尾、兩尾,缺失的空間。
而且往往是沒有好死的。牠們的遺體順沿馬桶水流旋轉並吸進漩渦中心,在濾網上停擱,直至腐蝕,從網格的孔洞溢流。
必是報復和反噬,投壓於物的反作用力。多年來,海洋、水族館、賣魚的店鋪成為夢裡一再被撥動的C和弦。總是身處一個暗藍熒光的四角展覽廳,中央一圈環狀柱,項上天花板黑不見頂,越遠越暗,像逆過來那天空才是深海的暗沉底部。腳下是水藍波紋倒影,時而赤裸雙腳,尾指乾燥微涼;時而繞著水族箱,在鏤空的迴旋樓梯連綿往下走。然後。
然後是眼睛。
比頭顱龐大的尸白色眼球,裹在腐灰的肉中央,快速掠過玻璃內層,被環狀的展示面折射變形。魷魚嗎?還是扁平的未知海魚。沒法用肉眼確認的碩大姿態一瞬間遮蓋所有燈光,形成一層黑色的屏幕。在那短暫的瞬間,沒有眼臉的球體,像攝像頭般左右挪移,似有若無地停滯並盯緊我的方向,那瞳孔過於渙散過於巨大,凝視的範圍足以把我從頭到腳地包覆。
像某層空間閉上了就迎來黑暗,那禮袍般的環形幕降。
夢中,我格外沉靜,在那龐然、冷漠,無情與仁慈之間,近似神衹的目視下,感到有如在聖壇被刨析審視、被剝光衣服的不適與平靜,平靜是因為有了被徹底理解的可能——在如此單薄、甚至算不上活物的魚眼中,我該也是一副膚淺透明的形象,就是那樣的形象,才適合於我。
但夢醒後,唯一記得的,只是反復在可見的出口前迷路、兜轉。在一間四面鑲滿小魚缸、燈光昏暗的水族店門口進進出出,門鈴頻響。在金魚街密密麻麻的透明膠袋前,察覺全部魚眼忽然扭轉紛紛面朝我的方向。
驚醒,在床上彷彿攤平了殼的文蛤,作嘔、喘息般自出水口吐出沙子。曾經認定這些重複上演的水汽夢境,必有強烈的隱喻意味,比方說禁止逃逸的預感,受制與困厄的警示。
但認真一想,夢中我尋找出口、以迷路的姿態遊走,卻從沒從那個綠色熒光的EXIT離開,大概我只是吞食皮屑的細小魚群,在壓倒性的巨物體下索求庇護,而畏懼與其對視。
看來我是從來不願意離開那些夢的。所謂驚醒的冷汗,也不過是潛水者在水壓急升下的不耐反應。
魚的夢,是成年的我像通過漏斗那樣收縮、延長,極力使自己縮小起來的過程。我於是對魚有了感謝,毋寧說是愧疚的心情,儘管它們至今仍不被我視作生命。
成長後我第一次養魚,嘗試溫和、謹慎,讓牠們以寄生物的形式,以擺設的形態活命。要是它們能活下去,好像就等於顛覆和嘲笑了以前的自己。於是一整日沒完沒了地盯著魚缸,看牠們怎麼活、怎麼吃、喝、排洩。
盯著,視野漸被玻璃面的折射比率同化。(還是說,眼珠、玻璃、指縫,這些透明的介質本就易與彼此混和嗎?)那時窗外天色已是沉積濕潤的炭泥,密壓壓的。對岸商業大樓徹夜明晃的燈把窗沿照亮,床側夜燈將魚缸打出一層反光面,能看見自己的鼻子在發亮。偶爾大馬路上的士車頭燈流過,像紅色幻覺,缸裡,一尾垂死的紅孔雀魚浮至水面,嚥下一顆氣泡。
冷得皮膚緊縮的天氣,我在房間把暖氣打至最強,暖氣電壓的輕顫在空氣底部、墻壁深處,小彈珠似的來回敲動,聽久了和魚缸的氣泵傳出相同的氣泡碎裂聲和震蕩力,把空間困住,捆綁成結並來回鞭打。在這樣溫暖得無法呼吸的乾燥熱力中,我喉嚨疼痛,鼻孔燥熱,整個房間彷彿是飄滿綠藻水草的深邃魚缸內部。
一個呈現鏡面折射紋路,多重層疊幻影,扭曲怪氣的魚類視覺世界。
曾以為有魚缸之後,心臟的秒針行聲將被取代,只想不到它在濾水器顫鳴與滴水聲下豈止不減,反而更為響亮,強調對命限倒數的執著。
我掩上房門,蓋被子,關閉視線,到夢裡的水族館迷路。彷彿進入俄羅斯套娃的最裡一層,越縮越小,小至氣泡的輕,小至漂浮,近乎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