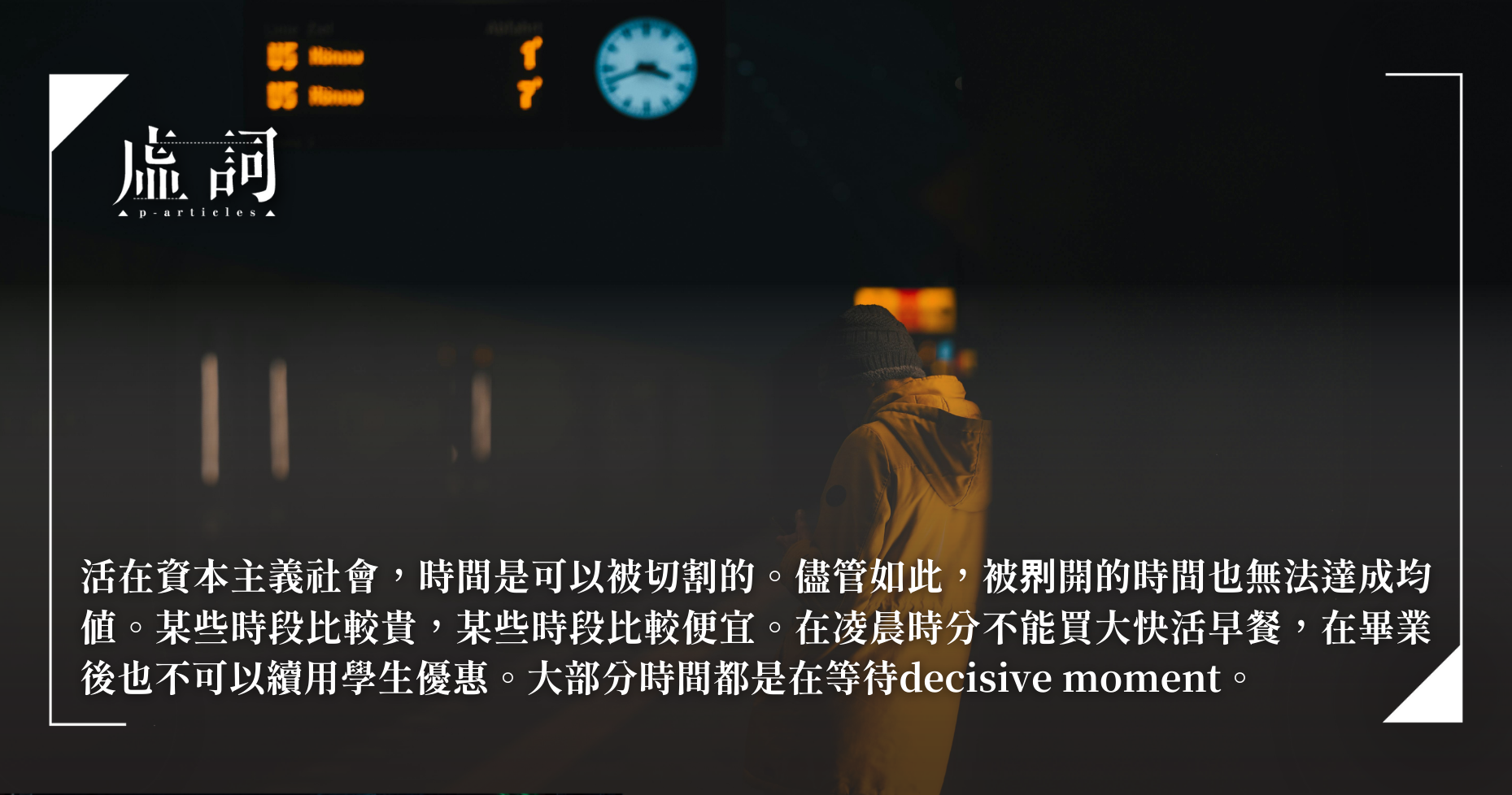天變後
小說 | by Cleo Adler | 2026-02-15
Cleo Adler傳來短篇小說,書寫「我」25歲時確診眼疾,從此世界只剩下仲夏的那一抹蔚藍。雖說命運多舛,但「我」在一次義工活動中認識失明了的章華,繼而令「我」眼中的世界重拾色彩。章華從「我」的身體律動感受地面;「我」又透過他的沉默,學會與悲傷共處。兩縷互不相關的靈魂就此產生瓜葛,兩輛駛往不同軌跡的列車,卻在黑暗中並肩而行。 (閱讀更多)
【字遊行·澳門】在時光縫隙裡的澳門
字遊行 | by 曾金智 | 2026-02-13
在曾金智眼中,澳門是一座在霓虹與石板路之間呼吸的城市,像一本厚重的書,封面是繁華,內頁卻藏著無數細膩故事。他在澳門旅居時,親眼見識賭場輝煌表象的背後,是一種被精密計算的空洞逃避,而街巷的奶茶、鑊氣,則是居民用日常節奏對均質化全球景觀的柔軟抵抗。「縫隙」是殖民與信仰的象徵印記,在澳門以斑駁的方式持續呼吸。這座城市的光譜,從極致的物慾橫流到極致的家常溫情,共同編織出無法被簡單定義的複雜靈魂。 (閱讀更多)
葉英傑詩三首(三)
詩歌 | by 葉英傑 | 2026-02-12
詩人葉英傑乃是大埔大火災民之一,再度傳來詩作,甫寫災後感受。在〈安家〉一詩中,透過新住客搬入中轉屋,其孩子已找到嬉耍的地方,映照出大人面對動盪的沉重與孩童在夾縫中作樂的生命力對比;〈回家的理由〉用魚兒洄游產卵的本能,比喻人們災後對家的牽掛,災民回到舊地只能隔著警戒線遠望,道出對舊居的眷戀及面對失去的無奈;〈地上的鳥〉借鳥自喻,寫出新舊居所從昔日的鳳凰木到如今單薄的樹與亂草,隱喻出自己的「無根感」和與脆弱,而失去舊居的鳥兒如常求生,如流離災民仍存生命韌性。 (閱讀更多)
腐
小說 | by 悇愉 | 2026-02-09
悇愉傳來小說,書寫父母在印尼鄉村經營飾物舖時,將「我」託付外婆照顧的經歷。在語言隔閡中,「我」度過孤寂時光,透過電視與周遭互動,又與那位總是帶著豆漿、在賭局中沉默的「豆腐佬」有著微妙的關係。然而,某個雨夜「豆腐佬」離奇穿過上鎖鐵閘出現於家中⋯⋯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