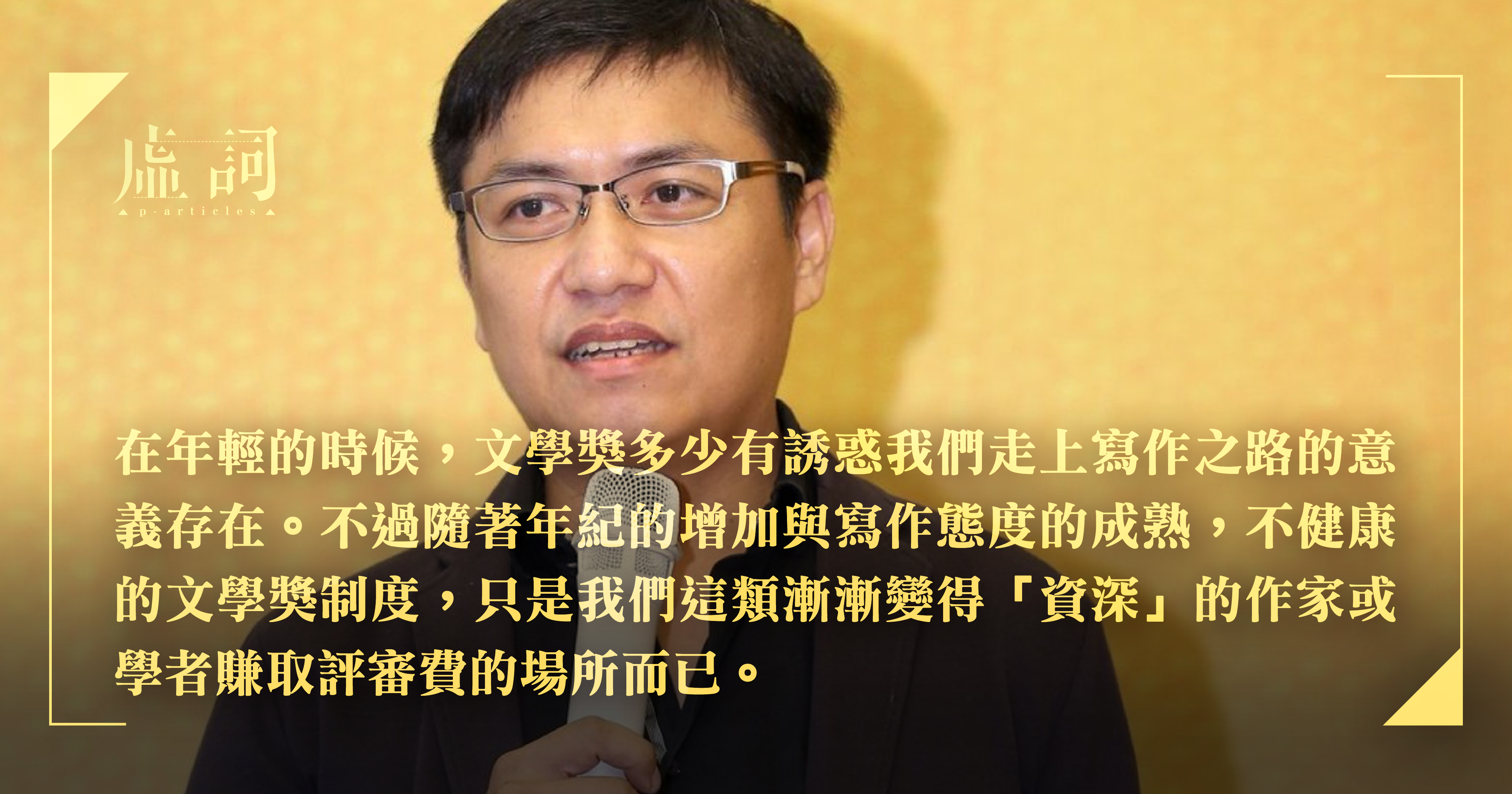小說家的未來簽名式:吳明益訪談錄(下)
專訪 | by 楊君寧 | 2021-05-28
在雙子星的航標下
筆者:您說過自己最想聽的故事,有三分之一是由黃春明老師寫出來的,還有三分之一他沒有寫,最後三分之一是您想親自去寫的。您接觸他的作品是在何時何種機緣,以至於到後來都留痕深遠?他所說的「小說不要寫給評論家看」給您的寫作帶來什麼樣的指導與變化?黃國峻往生後,您曾為他的《是,或一點也不》寫過懷悼式的評論,那您如何看待五年級後段及六年級前段班數位優秀寫作者在某幾年中相繼棄世?
吳明益:咦,我忘了何時講這話了。我大概高中時就讀過他的作品,比方說〈兒子的大玩偶〉。認識黃春明老師是因為他到我們學校(中央大學)演講時,我奉系上之命為他做了海報。他演講前看到海報,說希望能跟設計海報的人認識,於是我們才真的略微跨過讀者跟作者的界線。對於同齡作家的辭世,我只是偶爾會想,如果他們還活著,能寫更多的作品給讀者那該多好。
筆者:《本日公休》裏的小說大多寫於您服役期間,而後投稿給宋澤萊老師創辦並主編的《臺灣e文藝》,可以講一講您和這個刊物的關係嗎?當時軍中訓練生活與寫作如何平衡安排?在與宋澤萊老師電郵往來的交流研討中,您都獲得了哪些創作上的啟發?
吳明益:這個雜誌是宋澤萊老師想實踐他的文學理想,以及提攜後進的場域。後來小說家胡長松接手了這個雜誌的編務。宋老師那時會把自己的想法透過mail發給群組裏的所有人,我很少發言或發問,就是從閱讀中吸收。他曾跟我說,這個雜誌沒有字數限制,要我寫多長都無所謂,儘管寄去。軍中哪有時間寫作?我都是趁休假時寫的。在市區中逛街,然後找地方寫。
筆者:《家離水邊這麼近》出版後,您曾在張大春老師的電臺節目受訪。其後您提到過一些他講的觀念或知識,例如:「在A小說中的人物,在B小說中也可以成為配角」。同以《複眼人》為名,其實有長篇有短篇,而短篇並非簡單的長篇雛形;阿莉絲在《睡眠的航線》和《複眼人》中同名不同角色,都是在實踐這樣的寫作技法嗎?
吳明益:〈複眼人〉的短篇寫完以後,我一直覺得那個角色沒有死去。長篇《複眼人》寫作時,一開始並不是想寫複眼人的,後來他出現了,沒辦法,只好順著改書名了,哈。
筆者:由楊牧、李永平、陳黎等寫作者,甚至追溯到更早的王楨和,無論落籍抑或任教於此,都形成了頗為可觀的花蓮作家序列。當年您選擇到花蓮教書,在《蝶道》裏的說法是為了選擇一個可以繼續躲起來讀書思考寫作之地,還有沒有其他的考慮呢?東華創研所和東華文學獎鼓勵培養了一批有志創作的學生;近期新任吳茂昆校長打算進行的例如改革老師升等方式,根據專長累計資歷的舉措也會提供更多可能。以您的教學經驗和組織文學獎的經歷,怎麼看待其中的得失,哪些地方還可以更加改進,真正使得校園有良好的人文氛圍?
吳明益:當初我到花蓮是因為騎單車到學校附近,那時就決定了。我並不覺得東華特別怎麼樣培養了一批年輕寫作者,目前有成就的同學應該都是他門自己的天賦跟努力,東華只是提供了一個讓他們發展的空間。我的教學完全沒有經驗可以提供,每個學生都有差異性,說是教學比較像是對話。唯一我不太喜歡的是在校園裏就得「要求」學生符合某種規範,但這規範又往往引起反彈。如果我不是老師就不用去做這些事了。校園要有好的人文氛圍第一就是要鼓勵反動,其次就是聚集一批找麻煩、肯思考的人。這兩點都很難,我們沒有做得很好。
筆者:寫作《蝶道》同時您也在完成碩論,選擇王漁洋及其詩歌典律化為題。那麼當時您的主要學術興趣還是在古典文學領域嗎?張夢機老師逝世,印刻的《兩張詩壇》停止非常可惜。您從張夢機和顏昆陽兩位老師所獲得的古典文學教養是怎樣的?在寺廟裏講授《禮記》的經驗又留給您什麼回憶?
吳明益:我覺得中國古典文學給我許多養分,像張夢機、顏昆陽這些當初指導我古典文學的老師,都有一種獨特的文人氣質。那種氣質會讓人有「想成為那樣的人」那般的想法。教《禮記》的事是生活所迫,倒是當時我刻意挑釁講臺下學佛的學生一些談話,同時也在挑釁自己的思考,讓我難忘。
筆者:輔大大傳系給您的教益都有哪些?早年擔任臺北攝影節專刊主編和寫《音樂時代》與《廣告》雜誌專欄的經歷,較少聽您講過,那時的狀況是怎樣的?
吳明益:我們系上教我們的不算多,但我的同學教我很多。編攝影節專刊時讓我感受到有些藝術家的自傲,不太愉快的一段經驗。寫專欄則都是因為兩個雜誌有同學在其中,他們認為我能寫,所以給我空間。對我來說,當時能有一個練筆的空間,並且獲得一些財務上的支持,真的很重要。《音樂時代》專欄我批判了一些流行音樂的現象,當時覺得很痛快。
筆者:教授散文寫作課程的時候您調動過很多方法去激發學生的興趣與想像。本來人文學科的課程都很難教,寫作更是如此。教書近十年來,您最大的感想和對文學教育的觀念是怎樣的?
吳明益:說真的教書是我人生中很感苦惱之事,至今未獲得紓解。寫作的課程除了一再激起學生寫作的欲望外,就是討論各自的閱讀經驗。閱讀經驗確實有可能打開年輕寫作的眼界,不過有時也得靠機緣。所以我盡可能動用我能掌握的知識,包括音樂、繪畫、社會運動經驗、生態觀察等等……。只要有可能打開一個縫隙,就有可能打開成一道門。
筆者:《複眼人》多國版權的相繼售出在臺灣文學外譯史上帶來了嶄新的實現方式。回歸到文本本身的翻譯,其實仍是文化轉譯。您和不同國家的譯者在切磋溝通時遇到過什麼有趣的翻譯與文化問題麼,可以講講嗎?人地關係和全球環境應該是可以跨越種族、語言以及其他認同因素來由全世界共同討論的議題。然而今年年中將在東京舉辦的2012世界文明與發展論壇,其議程給人的感覺依然是:國家發展戰略和環保生態還是各自為政、彼此脫節的。這兩部分的學者沒有實際交流。官員們更加不會親自勘察地形地貌和河流的水文狀況,來決定一地的環保和發展模式。那您認為專業與行政的部分有沒有結合的可能,要怎樣去做才好?
吳明益:作品轉譯是很艱難的專業問題,我的語言能力並不好,不過很幸運遇到一些優秀的譯者,他們都很認真跟我求證一些文字上的細節。比方說〈虎爺〉在譯為日文時,譯者很仔細地問我了小說裏「我」(敘事者)的年齡跟性格,因為不同語境日文得用「我」、「僕」……等不同的字去表現。《睡眠的航線》外譯時,裏頭有一只名叫石頭的烏龜,譯者問我這只烏龜是公的還是母的,原來法文裏烏龜是陰性詞……。《複眼人》由於創造了一個瓦憂瓦憂島,雖然取法不少人類學著作,但也有不少形制是我所創造的。其中一種捕鳥的工具,譯者還畫了圖跟我求證。凡此種種,都讓我更加思考語言的細節。官員與專業者的落差,我想全世界多數國家無法解決。但公民素質一高,官員就沒辦法打馬虎眼……我覺得與其改善官僚體系,不如回頭提高公民素質,公民會讓官僚成長。
筆者:「運動文學」如成其為一次文類的話,必與對應的運動風氣之盛有關。棒球在臺灣勃興是從何時開始的,與日本的文化影響應該很有淵源?像是日本近年都還有棒球少年的漫畫,無疑是地位極尊的國民運動。劉大任、唐諾、詹偉雄這幾位寫籃球的老手、好手都有封筆收山之意。唐諾更是開玩笑說,不要一提到他就只想到他是寫NBA那個。在《世間的名字》裏他解構了運動健將可能由利生弊,被身體條件左右人生命運的狀況。您早年的《關於一只界外球》收於《臺灣棒球小說大展》,更有意味的是有人據此研究中華民國筆會在70年代外譯臺灣文學時,特意選擇棒球小說,將其於尋求國際地位的國族想像匯合;後來您為許又方老師散文集所寫的《咱耶棒球》足見深情一往,可以講講您的棒球情結和相關經驗麼?您的棒球經歷也與文學獎經驗很有聯繫,那麼能否順帶說說像您在《出詩02》裏說過的「對寫作的憧憬,以文學獎始,又以文學獎終」的含義?
吳明益:我從小就是個球迷,大學時候也跟同學組成球隊,不過當然是不可能真的走上那個少年的夢想。棒球對一直身處外交困境的臺灣而言,是個非常重要的出口,在那個政治失敗的年代,臺灣棒球在國際社會上的能見度,讓臺灣人多少建立了一些自信心。棒球也是殖民文化的遺留,是臺日關係很微妙的文化線索。我覺得這種運動在臺灣有多重隱喻。我想在年輕的時候,文學獎多少有誘惑我們走上寫作之路的意義存在。不過隨著年紀的增加與寫作態度的成熟,不健康的文學獎制度,只是我們這類漸漸變得「資深」的作家或學者賺取評審費的場所而已。另方面隨著文學獎的改革,以一本書為標準,並且長期追蹤整年度創作現狀的年度獎項,讓不同年紀、不同資歷的創作者,再次回到作品被同時檢視的舞臺上。我覺得這太重要了。因為這麼一來,作家不為追逐文學獎而創作,但文學獎隨時可能回頭「肯定」那些沉默的創作者。獎既不忌諱頒給同一人,也不會顧慮作者年紀,像布克獎、龔固爾獎、川端獎這類獎項,對作家的意義就是一體同適的檢視,也就是針對作品的檢視,我認為這才是尊重。至於對年輕寫作者來說,提供、贊助一個至少一年的寫作時間與場域,或許能補足目前我們強調「末端」生產結果的文學獎缺憾。
筆者:原住民問題因《賽德克·巴萊》之故,普遍關注的視點重又聚焦回霧社事件。您在《家離水邊這麼近》中《柴薪流下七腳川》一章,注目的卻是七腳川社,是機緣巧合還是另有原因?更早寫《最後的希以列克》時的創作動機是什麼?在《以書寫解放自然》中您回應有些人的質疑,認為研究原住民的自然書寫還需要更多調研和資料方能為之,這個有納入您未來的研究計畫中麼?與原住民的交往經驗中您的感觸又是怎樣,近年來花東地區的原住民面對漢化是如何保存其民族文化特質的?《水邊》書中未及寫到的您亦曾行腳過的花蓮溪流,以後會不會再撰文寫之呢?
吳明益:在花蓮居住,毫無疑問你就會開始認識原住民。我當時寫七腳川社,這是因為七腳川溪的緣故,而因為查閱了相關資料,那個原本湮沒不聞的世界就重新喚醒你。更早以前所寫的〈最後的希以列克〉,則是有一次到某個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題的樂園,突然看到原住民歌舞變成「表演」而非「文化生活」,那種掠奪式的文化展演,讓我突然感到一種痛苦。不過那時還年輕,所以構築出來的小說世界還很膚淺。與原住民接觸實在是個太複雜的議題了,有些原住民朋友因為我的外表,認為我「應該」也是原住民,所以往往很快地把我當成朋友看待。有時候我則是因為某些公眾事務而涉入,所以很難一概而論。不過概括來說,與原住民接觸時往往會有一種從語言到思維邏輯的異文化衝擊,這衝擊能讓我更反省漢人中心思維的教育體制。不過我想未來十年內都不可能重複類似《家離水邊那麼近》的寫作。
四個有貓的轉角
筆者:假如沒有當年偶然去做昆蟲解說員的經歷,您還會步入自然寫作和生態文學研究這個領域麼,或者會更晚一些?您表達過有時覺得不願回顧童年經歷,是由於裏面充滿了安徒生童話式的悲劇,這也影響到後來的寫作罷?從每年都立遺囑(這個行為持續了多少年呢?)到對死亡的從容達觀,您的觀念是怎樣發生變化的?
吳明益:我想可能要更晚一點,不過總是會開始的。那就好像有人為你造了一個星球等你降落一樣。我的童年經驗還好,我想跟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吧。應該說我想反芻的是那一整個世代的童年經驗,它構成了現在的我們這一代人。每年立遺囑這事我想超過十年了吧,我並非是對死亡從容達觀,而是覺得自己得準備好不麻煩他人而已。不過,隨著年紀增長,你周遭的人際網路越來越複雜,我認為反而越來越難拋開那個人際網路回到自己獨處的世界裏。死亡就是最終的、最純粹的獨處世界,但也自私得很。
筆者:您是如何與貓結緣的?對於動物保護中經常出現的是否素食、杜絕皮草、魚翅這類多有爭議的問題,您怎樣看待?流浪動物在城市中用TNR/TCR是最佳的方式對待嗎?北一女之前的校貓事件和近期的政大校犬事件都有賴熱心的動保人士出面參與,這些動物才被救下。所以您覺得設立動保司對保證流浪動物目前的生存狀況會有改善嗎?
吳明益:我總是回到演化學與動物學的觀點來看待這類事情,生物不總是獨立演化的,生物的演化跟其他生物息息相關。家畜、家禽跟人類共同演化超過萬年,牠們成為人類的食物、夥伴,跟各個文化的演化也有很深的關係,不能一概而論。流浪動物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才具有的,TNR當然不是最佳的模式,應該在飼養一開始就予以嚴格的法令限制,同時對違反者予以嚴格懲罰,再輔以健康的生態教育,問題才可能變小一點。但人類是一種生物,傷害他種生物,或其他人以求取個人生存,這種衝動我想一定存在,不會輕易消解的。
筆者:像七星保育基金會、荒野、千裏步道、黑潮、野望等這些生態環保組織,您感知的一個發展脈絡是怎樣的?您在編寫《臺北伊甸園》的導覽手冊之後,又有協助他們畫過一些動物和昆蟲的圖鑒?從去年的反國光石化運動到現在的蘭嶼反核廢料,您覺得環保運動的推進和抗議鬥爭方式有所進步麼,其中的關鍵因素為何?《迷蝶志》裏寫彼時蘭嶼,尚是有珠光鳳蝶出沒的地方,後來十年間,您有重訪過蘭嶼麼,體會到的變化是啥麼?
吳明益:這個問題幾不可能回答,您要讓我寫一本臺灣生態組織發展史嗎?哈。我參與這些運動有時主動有時被動,但近年確實有些「質」上的改變。從運動的策略和形式上,美學都已經參與其中,論述的深化也都有專家參與,而不再是喊口號式的,或局部反應而已。您問到珠光鳳蝶的問題,過去這種蝶種被達悟人視為惡靈,現在則是他們導覽觀光客的重點生物,自然就會注意棲地保育。原住民遭遇文明社會,也會漸漸調整他們和某些特定生物之間的關係。
筆者:您最初手繪生物圖像的想法是最低限度的干擾,不過這些畫作已經自成風格。您與插畫者的合作是怎樣的?張又然《春神跳舞的森林》真是優美細膩的繪本。《魔術師》的插圖和故事的氣質也蠻吻合的。未來您會不會再想要找其他繪畫人合作,或者有自己畫插圖的意向嗎?《虎爺》應該是您第一本自己做裝幀設計的書?《本日公休》的封面為什麼會選那樣的火焰圖案呢?
吳明益:我希望日後能與不同領域的優秀創作者合作,這不是一個獨立創作的時代,每本書的完成,都得靠各式各樣的專業人才。而且跟他們合作也能有些刺激,造成火花。《虎爺》是我設計的封面沒錯,但出版社做了微調,《本日公休》我則完全沒有參與意見,書印好才知道的。
筆者:收在《水邊》書內的多張連綴雲圖,是您某一段時間裏定時定點的每日記錄麼?您開始生態攝影是什麼時候,對此有怎樣的心得?您的攝影散文集何時可以面世?為了保證相片的品質會不會考慮出成攝影集的樣式?
吳明益:定點沒有定時。我學攝影是大學一年級進入傳播科系時,目前正在寫一本關於攝影的散文,目前一切還沒有確切成形,實在無從談起。
筆者:關於露營和步行,您的感觸怎樣,有沒遇到過比較驚險的特殊經驗之類?夜行萬華的一些場景後來被您收進小說裏,這類題材以後會不會再更深化去寫,單獨成為關於城市夜之暗面的,甚至帶有報導文學色彩的作品集合呢?
吳明益:露營和步行是人類遷徙、觀察環境的基本活動,這類的活動有些現代人覺得很無聊,但我卻覺得很能激發好奇心。由於自己會變成很像是一種生物,於是感官整個都敏銳起來。我不太善長寫報導的文體,我想未來還是會把這些感受鎔鑄到目前的幾個較明確的寫作目標上。
海是我們的路
筆者:楊照的《陽光書坊》中您談過《複眼人》,講到由之延伸的地理和環境問題。就您踏察過的地點而言,島嶼上步道和古道的現況如何?清水斷崖上可以獲得「海鳥的視野」,這樣的視野所見的景物有何不同?花蓮作為觀光地被誤解的機會很多,您覺得實際上最應去探勝的有哪些所在?雪山隧道和蘇花高都有其弊端,那麼您覺得,花東一帶由於天然地質造成的安全隱患,有沒有什麼更好的預防措施?
吳明益:這個問題真的太大太大了……。
筆者:伊能嘉矩、鹿野忠雄的臺灣踏查記錄,侵華戰爭前的中國城市地形圖,霧社事件的日文史料翻譯等現存的日本對臺灣和中國的研究令人驚歎,雖然其中有些純然是出於其侵略和殖民目的的預備功課,但這種調查功夫亦是下得很深。中興大學前身是日本的札幌農學院,也是日本在東亞推行其戰略計畫的農科實驗基地之一。您在中興的一年踏察主要的收穫是什麼?如何看待日本與臺灣之間糾結繁複的歷史文化互動關係?您計畫中以蝴蝶串聯來寫作的日據時期臺灣史的構想可以透露一些嗎?
吳明益:與其他領域專家的對話、一同工作是最大的收穫。比方說空汙專家莊秉潔、經濟學家陳吉仲都是我那時認識的,他們從不同專業領域,討論同一件事情,常讓我有重回學生時代的感動。許多人到了學院教書以後,就認定要鑽研一個專業,但文學不是一個專業。文學得寫很多種人,他們身上有不同的專業,得靠生活才能認識清楚一些。以蝴蝶寫臺灣史的計畫暫時擱下了,要處理的事太多,能力有限。
【後記:自在生枝】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這並非一篇均勻分佈的訪問,各部分的問題數目多少不一。原本的設計遵循一定的形式,保持每部分問題等額,但在實際的互動中,受訪人對題目的設置與應答提出了意見,因而有所調整刪削,此亦為一大貢獻。某些過分貪心龐大的問題遂自然脫落,問答長短交錯,形成現在呈現給諸位的樣貌。這不算短的受訪過程中,感謝受訪人吳明益老師不厭精細,言無不盡地一一隔海作答。訪問的最終完成要歸功於他。各種文責則由筆者擔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