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論,捕捉無形的「情感短路」:專訪《情感資本主義》作者駱頴佳
打開手機,又是看到「十二港人被送中XX天」標題的一天。見字發獃半會,把新聞碌走。看到心儀商品減價的廣告,想要犒賞連日來因工作而勞累的自己,於是買買買。價錢很划算,商品設計很有品味;快樂有時候就是擁有一隻漂亮的杯子。到了下星期收件時,才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很想要——期待貨物來臨期間的充實感迅速失卻。
疲倦、自戀、再度疲倦——這樣無數個私密而集體的時刻,是《情感資本主義》嘗試以理論處理的命題之一。因此它非常困難,難在情感的無言性、複雜性,和流動性。這本書之於情感,就像魯米諾之於被擦去的血跡一樣,嘗試重新顯現無痕的情感互動——只是當怠倦的日常始終不是兇案現場、理論終究不是魯米諾,一切該如何追溯與研究?
身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的作者駱頴佳,比大部分人都更清楚情感理論研究的侷限。他在自序中便毫不諱言自己的窘境:「這本書注定吃力不討好,因為它要用文字捕捉當代社會政經文化的情感操作……」
雖明白限制,但駱對於自己嘗試處理的問題,絕對毫不含糊:在抗爭陰霾、制度不公以及疫症的夾擊中、在這個苦難者每日都如此清晰的社會裡,如駱所言,我們要如何持續「敏感於他者的苦困」?我們要怎樣理解因為怠倦而選擇不再受他者影響的「情感短路」?而對駱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如何探尋出路,重新與人連結?

連休息都是監控一環:情感規訓與「功績社會」
書寫《情感資本主義》,本來是駱研究近代情感文化理論及哲學的一次爬梳及反省——期間經歷浩大的反送中運動、新冠肺炎疫症,都是駱始料未及的事。
相比起眼下因大型社會事件而觸發的情感困頓,積存在(perpetuate)日常生活已久結構性問題同樣亟需處理,那就是「情感資本主義」本身、這本書的命題之一:我們的情感和精神力量「如何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模式裡被挪用、積累、生產及消耗以幫助資本主義由有效地運作?」 要理解這種「挪用、積累、生產及消耗」,就先要理解情感如何流動——而駱在書中所運用的其中一種理解框架,就是力必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
「力必多」的概念源於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起初泛指一種假設存在的本能性欲衝動,能透過被滿足、昇華成創造力等不同途徑釋放,或因窒礙而累積。後來在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李歐塔(Lyotard)的《力必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等討論微觀欲望政治的後現代著作中,多被詮釋為受資本主義壓抑、亟待解放的精神能量。
駱嘗試以簡單的語言概括如今力必多經濟對我們的影響:「就是整個資本主義其實在操控你的情緒能量,甚至——你可能本來有一種批判社會的欲望、參與公民社會的欲望,但它(情感資本主義的機制)令你感到勞累。」
馬克思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使我們與自己的勞動、生產,甚至是我們自己、周遭的人疏離,即常言的「異化」。而情感資本主義的可怕之處在於,異化的不只是身不由己的工作,還有為圖便捷而變成唯一選擇的閒餘活動(如放假時例牌只去shopping)。力必多的釋放與否、疏導方式,都是受到監控的一環。休息、管理情緒,最終是為了更有效地工作。
駱解釋,情感變成生產手段,並非什麼新鮮事,韋伯(Weber) 早就指出,基督新教徒對自我欲望的規範來促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服務業在現代社會中的蓬勃發展,更是加劇了這種現象,尤其是二戰後西方的管理文化對當代人影響甚深。他舉例,「你去逛書店逛的時候,你看到心理學(那一欄),不會見到很多說什麼佛洛伊德、或是拉康這樣的心理學書,很多都教你怎樣在職場上怎樣不要亂發脾氣、管制你的 EQ、甚至怎樣去積極——反正就是不要『放負』。」
他想起一個學生曾跟他分享在迪士尼樂園裡打工的經歷,令人哭笑不得:「連笑容也要 control 你,不可以笑錯某種『型號』,錯讓其他人覺得你很奸狡。」駱觀察到,即使是在一般職場上,也隨處可見情緒管理文化的深入。
「用福柯(Foucault)的講法就是在 discipline(規訓)你的情感、身體,從而達至一種 profit-making(牟利)、『快』的方法——你鬧情緒咪拖慢工序。在香港,也不只是你出來工作是這樣,其實讀書已經係咁。特別有一些傳統的學校,很規管你的情緒,只是不斷叫你讀書、讀書、讀書。」
「我們的情緒、慾望,其實是被韓炳哲(Han Byung -chul)所講的,那種『功績化』勞累去 torture(折磨)我們,去勞役我們。」駱於書中援引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所提出的「功績社會」一概念,進一步解釋為何連追求快樂和滿足都會變成自我勞役——社會對功績的標榜,令「他人的要求(被)內化成自我要求」,不工作的時間便用來增值自己,務求他日能更有效地工作,形成無意識的自我壓迫——那幾乎像是恐怖電影裡被邪物俯身的情節,連自己也變成敵人。
駱形容,在力必多經濟的脈絡中,這種倦怠就是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謂的「情感短路」。這種「工作時間」已超出「工作時段」的社會局面讓我們倦怠得只能「顧掂自己先」,累得無法關心他人,變成「不情動主體」(disaffected individual) ;但當我們渴望解放時,情感又能達到真正流通嗎?
比起世界末日,資本主義、或是情感資本主義的終結之所以更難想像,就是因為這部龐大的機器既製造了問題,也提供了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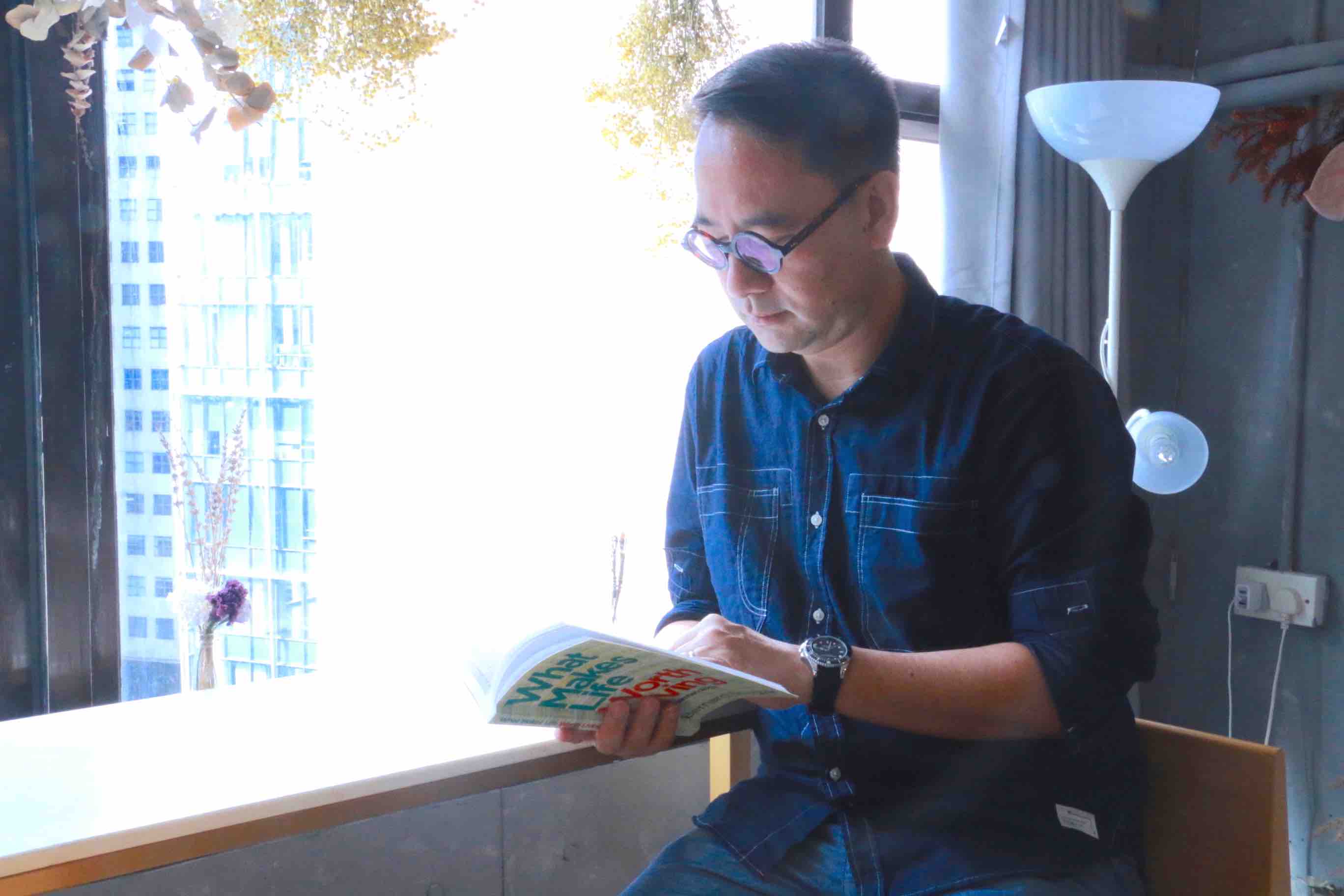
失去人的條件:情感「代包」與「廢人化」
在《情感資本主義》面世的同時,左翼 21 亦出版了《青年「奴」工:廿一世紀的香港故事》,其中收錄了十多位來自零售業、建造業、飲食業等業界的青年勞工的故事。編輯李峻嶸在〈跋〉中「勞工團結的障礙」一段提到:
「在當下的香港,不少青年勞工都期望自己的工作不是純粹維生的工具。他們希望工作能讓自己提升和有滿足感。當工作既無法令人覺得有前景,滿足感又欠奉時,青年人就會嘗試在工作以外尋求自己的生活意義。倘若更多青年人覺得在自己的生活中,工作的重要性其實不是那麼高,要他們犧牲時間為改善職場待遇奮鬥,就更不容易。」
受訪者中當然不乏透過工作實踐理想的青年人,但更多是在工作以外以消費途徑來獲取便捷的快樂。這和駱所說的不謀而合:「今日很可惜,我們的情感、情緒,很多都是被資本主義變成消費欲望。」
「在斯蒂格勒的理想世界裡,人是可以自由地運用自己的欲望,去建立自己的文化藝術創作,甚至是一個社群性好高(的社會),一個『we society』,大家可以建立一種好理想的城邦。」但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機制中,我們的欲望似乎被限制在某幾個軌跡內流動,環回往復,無法突破。如上述「勞工團結的障礙」中提到的,人們被迫進入無法為自己帶來滿足的產業,以勞動換取金錢,再以金錢換資本主義社會所催生的娛樂,就像不停注入嗎啡以緩解生活的勞累及痛苦,而失去了改革產業問題、生存問題本身的動力。
這種透過消費和娛樂得到的情感「釋放」,在斯蒂格勒的角度看來,是窒礙了力必多的真正解放。駱精準的將之概括為「代包」:有人把釋放的路徑都給我們制訂好,我們只需要把它買下來——去酒吧如是,買精緻的水杯如是,看 Netflix 如是。
「咁多時間,(你會想,不如)走去賺多一點錢,去買啲嘢俾自己可能仲好。我們原本能用自己的能力去,例如,作隻歌仔唱下、創作文化藝術——斯蒂格勒覺得欲望本可以由我們自己掌控,但今日好多嘢係『代包』。當然他用的字眼是有一點抽象,我純粹簡化了他的說話——就是今天很多文化工業就是取代了我們可親自動手的工作或創作,即透過創作、關心他者來達至理想的解放。」
這種說法的背後,暗示著一種終極理想的解放想像——在斯蒂格勒向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借用的話語中,這種解放想像就是「跨個體化」(transindividuation)。
駱嘗試先簡單解釋「個體化」本身的意思:「就是一個『情感的充盈』,有一種很充實,很滿足(的感覺)。」而「跨個體化」則是一種進一步的、主體與主體的交流和互相成就:「(人們)互相彼此豐富,大家的能量互相促進,而且人和人——甚至不只是和人,可以同non-human(非人類),這就是現在 posthumanism(後人類主義)會討論的事情。……這個就牽涉動物倫理,甚至植物、空間、大自然,甚至細菌。所以『個體化』就是說,人不只是簡簡單單一個人,而是一種情動的主體(the affective subject),他的情緒、情感,是與外在的一切結連及交接。人在過程中會彼此增生,此消彼長。」
在斯蒂格勒的語境裡,這種「跨個體化」,在今日的社會有時會遇到挫折,原因在於一種「情感短路」——這也是駱在書中、以至訪問中所持續思考的觀點。在《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一書中,斯蒂格勒將這種「短路」解釋為人們嘗試內化一個並非由他們自身創造的電路(circuit)的結果——面對一種主導的想法(doxa),人們選擇適應;人們適應著他們沒有共同創造、卻因為消費文化及科技而流通的主導性思想(dominant ideas);人們適應著這些他們無法共享、參與,而只能屈從其中的思想。
駱解釋,這種「短路」就是一切討論的重心之一。「所以開頭講的力比多經濟就是講這個問題,這就是整本書要講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打開欲望,流向一個我們可以——例如——實踐公義的社會,一種人倫比較關注的生活方式。」
適應總伴隨著捨棄與取替——所謂「代包」的意思,不只是指情感解放的方式被取代,還有知識以及回憶的能力。斯蒂格勒將這種現象稱為「proletarianization」,直譯是「無產階級化」,但斯蒂格勒的學生許煜則將之翻譯為「廢人化」,駱深感這個譯法非常精彩,笑言「就是廢了『武功』嘛。」
簡單來說,「廢人化」就是人們被迫放棄自己原先擁有的知識,去學習能迎合市場的相應知識,以保持競爭力。駱舉例說,像是農夫因為城市化而失去農地,只能被迫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改學別的技能以維持生計。但駱進一步解釋說,在「廢人化」的過程中,技能知識只是其中一種被迫取代的知識——根據斯蒂格勒的說法,還有「生活知識」和「倫理知識」兩種經驗同樣面臨被外化的危機。
駱以掌故的流失為例來說明生活知識的流逝,「以前我們的生活方式,例如我阿爺阿嬤湊我們的時候,會講很多故仔,很過癮。可能是在講以前的生活經驗、走難的經驗,這是屬於他和個孫交流的一種生活的知識。講故仔是一種生活知識的傳遞。……但你想一下,我們已經越來越少人講故仔,特別上一代給下一代說的口傳故仔。故事可能已經(多數變成)電影,(被)Netflix 取代晒。當然,嗰啲故仔又講得好聽,又視覺化。」又例如是中產家庭普遍聘請外傭的文化,令一般由父母傳遞給孩子的生活知識,容易被外傭姐姐「代包」。
就連促進這種掌故的出現、流淌、流傳的空間,都因為科技而收窄。駱言及自己兒時居住公屋的回憶,言談間不無懷念和惋惜。「(從前人們)會曬晒啲屋企人相掛在牆上……排晒係個公屋度,喺個架度,邊個結婚呀、邊個啲 BB 相。……每逢拜年,阿婆就話,阿仔 / 阿孫,睇下你以前,怎樣怎樣……現在是沒有,我們很少;但現在的影像氾濫到一個地步,到了我們大個,可能會沒有記憶。重點不是沒有承載記憶的硬件,而是影像氾濫,令我們不再珍惜,也未必會曬相。」駱慨嘆,今時今日,「連記憶都要 Facebook 提醒你。」
我們某程度上不再以自身內在的情感動力和編排方式去記存人事、不再以自身的情感經驗去和他者交流——就如亨利米勒所說的,「我們不再交談:我們只從報章雜誌中撿取一知半解的事實、理論,來淹沒彼此。」只是供我們尋找代理語言的媒介不僅限於報章雜誌,還有無數的影視作品、消費娛樂。我們持續被餵哺著一種情感得到舒緩的信息,持續適應著一個主要由消費文化建構的信仰體系——「廢人化」也是異化的一種,但異化的不再只是勞動,而是情感本能。駱的描述一針見血:「因為(用消費得來的)那樣東西,有時無法表達你生命裡的一些深刻的感受,但你若能創作,例如寫詩,那就很不同。」
駱釐清,這並不是要人們停止所有消費和消遣,而是要人們警醒於情感資本主義操作下,物件有一種斯蒂格勒所謂的「藥性」(pharmakon),即凡物皆可用,卻不總有益處(作為禮物的物可傳遞善意的信息,但大量的消費品也可造成生態破壞)。「就如(斯蒂格勒)研究科技——科技可以是良藥,可以是毒藥,睇你點用。我們可以用科技來救人,但科技也可能令我們成為奴隸,被它控制,或是監控你的自由。」所以,我們要思考怎樣的對物的分配(經濟學),能促進公平社會的建立,讓我們的情感在惠及他者的生命中得到滿足,而非只滿足一己的私欲。

重新「通電」的可能:美學作為方法
要嘗試解決情感短路、倦怠、以致對他人冷漠的問題,則在於「我們能不能把情感導向一種很 caring(關顧他人)的、一種救贖性的,或一種醫治性的方向裡去。」,而書中提及的不同情感空間的建立也是由此方向來進行探索。所以,除了爬梳近代情感文化理論及哲學,探尋可行的出路也是《情感資本主義》的主要命題之一。駱不希望「安於描述我們有多慘,而是希望思考有沒有轉化性的出路」,在書中則以極為謙卑的口吻指出,「我亦希望本書能令近年常處於犬儒及絕望的香港人能得到丁點兒啟發及幫助——這是我寫作的卑微願望」。「卑微」是出於謙遜,也是出於「找出路」這個目標之浩大。
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後現代或當代文化論著裡——著名者如詹明信(Federic Jameson)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資本主義多時被描繪成一種能把批判本身也吸收的「阿基拉式」怪物。以這種論調書寫的當代代表,當數在約十年前提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capitalist realism)的費克 (Mark Fisher)。這個觀念的出現,標誌著資本主義的不可突破性——資本主義被當作我們的唯一現實(reality),一切文化上的發展只是舊日的變奏版,沒有真正的「新」可言,「未來」失效(the failure of future);批判資本主義的文藝作品給予人們清醒的錯覺,無形中卻鞏固這種現實。
所以在資本主義面前,探討出路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而駱也深知這一點。但面對情感資本主義,駱在著作中提出的,並非要完全擺脫我們身處的現實,而是要從打開欲望流動的空間做起,以重新與他人連結——美學就是其中一種辦法。
駱在書中和訪問中連番解釋,這裡的「美學」指的不僅是觀賞藝術,而是培養一種「匠人式」的藝術創造,或是默觀及專注力上的修煉 (這也是斯蒂格勒所關注),唯有此,才能沉澱一種持久的精神力量,整頓自己的情感,好能夠專心地關注他者的需要。斯蒂格勒指出,物件變得有益的「良藥」,正在於它成為一種可建立關顧關係的中介「過渡物」(the transitional object),如玩具之於父母與子女,從中將人與人結連。此外,「過渡物」甚至不只是物件,更是一種促進情感連結的人文空間——如「深夜食堂」之於食客與主廚。駱認為,香港今日的「小店」絕對能為不少人提供另類的、能建立深入關係的社區空間,就如昔日香港人開士多仔,來串連社區。而自反送中運動起相繼林立的「黃店」,也為人們開啟了新的場域,讓人們的共同情感有了流動、轉化、交織、重新分配的地方,例如將憤怒轉化成能支持「手足」的良心消費。
「如果你把握到力必多經濟這個概念(以及其對情感的操作),其實你去耕田、甚至是跑馬拉松、甚至有人做記者、我做學者,甚至為人父母(parenting),這些都可以(為我們打開出路)——如果我們有意識地專心去做,其實就是注入一種抗爭情感的實踐。」
以「他者」為先的情感政治
香港人在反送中運動中所產生的高度結連、強調「齊上齊落」的共同體想像,無一不衝擊著駱的思想。他在運動中目睹很多人「有一種『living for the others』的勇氣……很多人在這件事入面受他者受苦的情感衝擊,從而改變了——如果學術一點講——他們的『主體性』」。這種觀察剛好和他在書中探討的「他者理論」、哀悼主體等命題無縫接軌。因為「如何和他者接壤」不僅是思考如何解決「情感短路」的進路,也是駱向來最關注的議題之一。
駱對「他者」、情感、受苦等議題情有獨鍾,其中尤其受他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之一、猶太裔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啟發。他在書中這樣總括列維納斯著作《總體與無限》的立論,淒美莫名:
「人總是有自我主義傾向,直至與他者相遇。人對別人的責任只有在被動及不自由的情況下,在面對他者痛苦面容的衝擊下,主體才會對他者負上責任。」
過去一年多,抗爭者正是時刻蒙受他者苦難的感召,既不由自主又責無旁貸。在列維納斯的文字中,「他者」像鬼魅一樣——駱形容是「隨時在你身邊顯現,超越時間」。
研究列維納斯多年,駱也因為近年的社會運動,對「他者理論」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以前我不懂。但當我去懂得默念一些受苦者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他那個鮮活的經驗會再次出現,去再次 interrupt(打擾)你。……你睇返舊年反送中運動很多的圖片和故仔,你以為自己放得低,但其實佢會再次觸動你。我覺得這個就是列維納斯所說,『他者』好像一種循環,他永遠都會回來找你。」
駱受列維納斯啟發之餘,又深受他者苦難的震撼,不禁覺得這種「以他者的痛苦及缺乏為由,因而衍生出責任與慈悲為主導的政治,比以怨恨或憤怒作主導的社會參與為佳」。
但駱強調,他並不是要否定憤怒,只是不要讓憤怒轉移視線。他坦言,「唔憤怒就假啦。所以我不是否定憤怒。我只是說,如果運動是要很持久,你的初心仍然需要指向一種對受苦者的關懷。憤怒固然是一種推動力;憤怒的好處是會給你勇氣。……我覺得憤怒是必然需要的——要處理憤怒也不是很幼稚地說,『好啦我而家寬恕你啦』這樣。特別是一些公共事件的憤怒,例如一些集體暴力——我覺得一定要有一種社會的機制達至一種真正的寬恕。(但)你見到香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已經不了了之。根本政府沒做到,根本持續地憤怒是必須。我只不過是在說,更長遠的路要怎麼走;因為你常常讓憤怒去 trigger(觸發)你,也會有一個危險,就是你會——嚴重啲,製造更大的暴力或看不見事情的真象。」
駱笑言,「你可以話我『左膠』,我仍然相信要持久地行動的時候需要一種對人性的慈悲,是很重要的。」
無論是在書中、還是從訪問中,都能隱隱感覺到駱的某種踟躕不安——《情感資本主義》不是一本易讀的書,儘管駱的行文已極盡簡潔流暢,並多以生活例子入文,情感文化理論就如情感本身,紛紜複雜。駱關切地問過記者好幾次,書的內容會否太深,又自嘲說也許情感這回事還是用小說來說最好——無論在紙上,或是在現實中,駱總是在反覆的拷問自己,能否傳遞好自己想說的話。
「特別我們讀人文科學,怎樣可以令這件事不離地,而卻和我的生活相關,我想是很重要的。透過你學的知識和你身處的世界產生對話——有時可能是現實世界衝擊我去思考,有時候是我看完書去批判返個現實世界——我覺得對我來說,學問、哲學也好、其他理論也好,我也很希望將它變成我一種生活的方式。當然這個是要小心,但這是我對做學問的自我要求。」
在駱的研究世界中,他人 / 他者始終是核心。《情感資本主義》是一本理論之書,也是一本呼喚之書。駱在向我們披露著他最誠懇的反思,以對有緣的讀者作出一點提醒,令我們更覺察到情感的流動與分配、自己又如何被既存的機制所限。比起容易使人沉緬其中的小說,或許直接、真摯、充滿警惕的理論,更適合承載駱的這種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