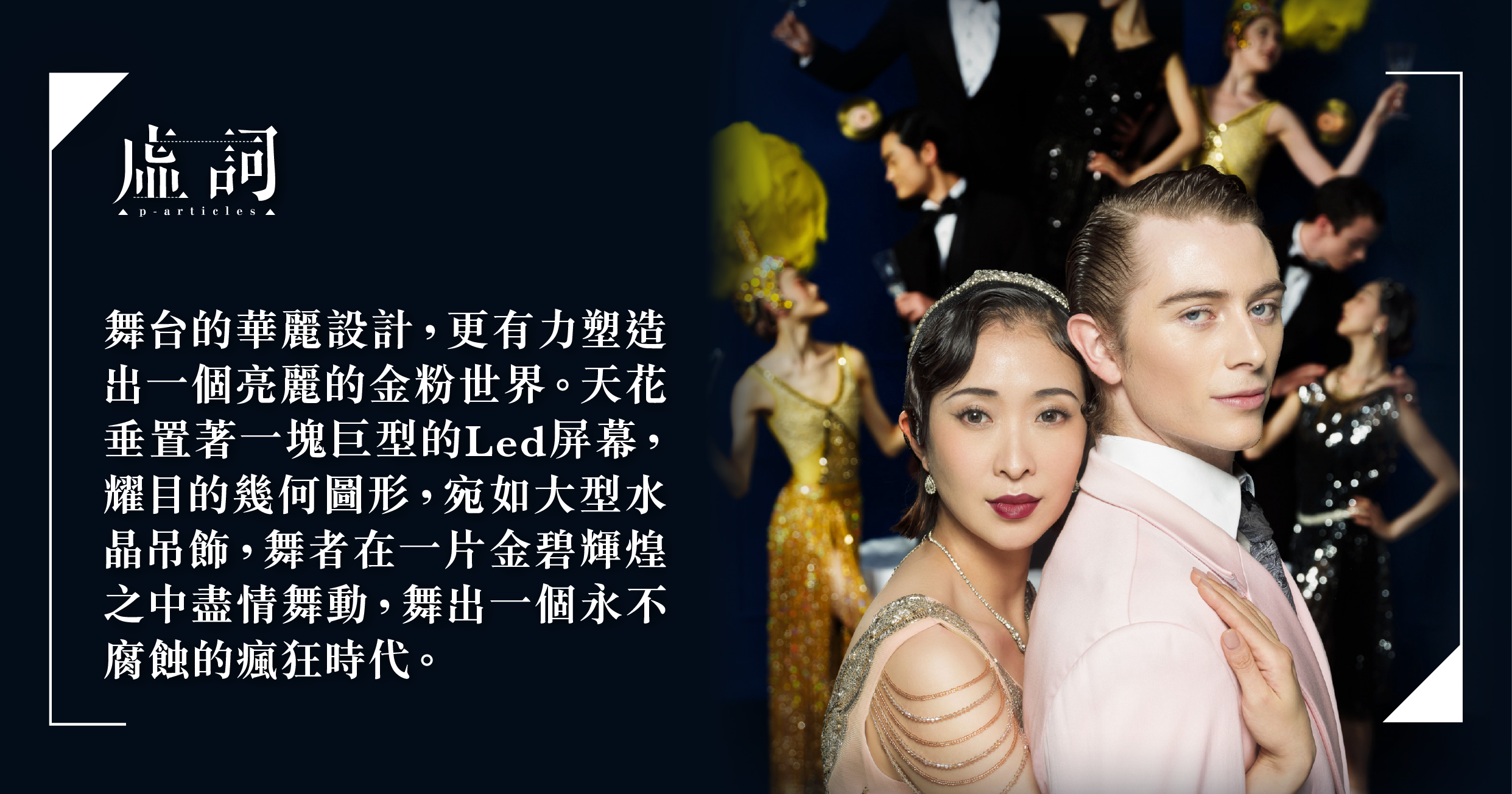《大亨小傳》不但是美國文學的經典傑作,更得世界各地文人的青睞,如村上春樹便為之迷戀,要親自將之翻譯。村上曾言:「如果只能選擇一本,我會毫不猶疑地選擇《大亨小傳》。若不是因為費茲傑羅的小說,我不會寫出今天這樣的文學作品。事實上,我甚至可能根本不會寫作。」可見村上春樹認為這本小說對他日後的創作至關重要;而故事中瑰麗的場景、男女主角情感細緻的流動,以及字裡行間對浮華世界與人性貪婪腐敗的刻劃,也令無數導演、編舞為之傾慕,爭相將之帶到鏡頭前或舞台上,與觀眾見面。 (閱讀更多)
暗香浮過雙城記
因著雙妹嚜的香港血統,它偶爾作為故夢的香氣出現,也多出現在香港作家筆下和港產影視作品裡。李碧華為它寫了一篇散文和一篇小說,都叫《雙妹嚜》,幾乎可說為之作傳。散文〈雙妹嚜〉收錄在文集《鏡花》裡,那是李碧華在豆腐塊文章中用意精雕細琢的一個時期,她寫雙妹嚜,「是三十年代,全國女子一齊作的綺夢。」「像可樂瓶那種幽幽的綠,像一頭貓在靜夜裡的眼睛。而商標,沒用過也見過,一直流傳至今,成為一種巧笑倩兮的靜定的魂。永遠有兩個不知是甚麼關係的女子,曖昧地依偎相擁。」 (閱讀更多)
露易絲.葛綠珂:詩人發現了死亡的秘密
死亡與源頭,是每一個詩人不可避開的主題,在葛綠珂這裏,更是由始至終纏繞一生。對於迷戀死亡書寫的葛綠珂來說:沒有一語成讖這回事,她活了八十歲,是大多數自殺的自白派詩人的好幾倍,這是一種神奇的魔術:她把源頭書寫召喚過來,保護了她的死亡書寫,祛除了自己和讀者都不免的死亡情結。 (閱讀更多)
用思考抵抗狂熱,用愛擁抱日常
其他 | by Sir. 春風燒 | 2023-10-30
移居西班牙的前央視女主持兼記者柴靜沉寂多年,推出關於歐洲恐怖主義的紀錄片《陌生人——對話聖戰分子》。Sir. 春風燒看畢心生敬佩,又心有戚戚,不禁思索生活安定的人為何成為聖戰分子,只剩下一張殘暴而狂熱的臉。他又認為在文明世界中,用常識、理性和人道主義對抗狂熱,在求知和接觸個體認識自我以及周圍的一切,以此抵抗各式各樣的蒙昧和狹隘,是每個個體的責任。 (閱讀更多)
如回憶因人太多而失去了——評《4拍4家族》
由賴恩慈執導的《4拍4家族》透過來自四個不同年代的音樂人,戲劇化地組成的樂隊,呈現各自對音樂(節拍)的感知、期待、碰撞和理解的過程。江俊豪認為故事表面是一個失職父親向女兒贖罪的故事,內裡卻是從個人、家庭,到城市回憶、失憶、尋找與保存的嚴肅課題,但曲目與曲目之間應要讓觀眾對歌詞與角色有多一層靜默的思考。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