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澳門時間】給我一片黃色的澳門時間
散文 | by 袁紹珊 | 2020-1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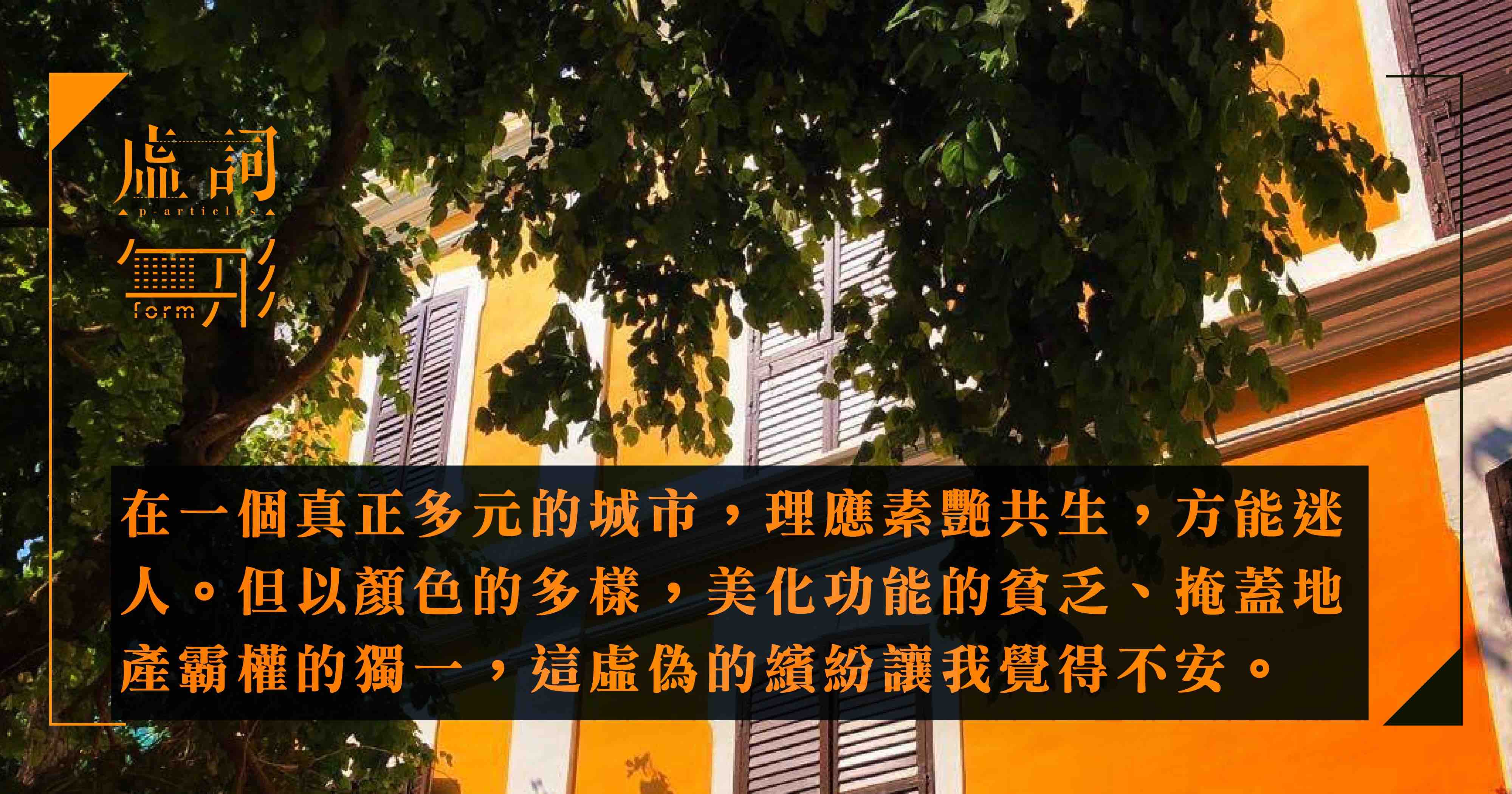
(賀綾聲攝)
在澳門,時間彷彿是用以虛度,而不是被管理的。建築外牆越斑駁越美麗,輕軌、巴士、飛機均以晚點為己任,街上沒幾個鐘準時,壞了,就光明正大地壞下去,像一鏡到底的漫長影片。
在我眼中,黃色全面接管了城巿,奶黃色的教堂,賭場的金黃,街巷的琥珀色燈光。黃色是這座城巿的濾鏡,世故、天真、貪婪又靜穆,讓曲徑通幽的歷史,變得雋永而滄桑。
我對黃色的偏愛,似乎是與生俱來。明亮的黃,一向是好奇善變的雙子座的好搭擋。枱頭的黃水晶,衣櫥裡的黃衣裙、黃背包、黃鞋子,畫框裡褐黃色的古地圖。聽說檸檬黃的反射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容易在人的記憶中保持温度。

我的童年主要在澳門北區度過。那裡沒有馬卡龍般繽紛的葡式大宅,連街燈都無比慘白,一切以功能先行,只有灰頭土臉的雜貨店、千篇一律的白色經濟房屋、鏽跡斑斑的鐵枝花籠、亂七八糟的鐵皮篷蓋、螢光色的吵鬧大排檔,一切沉悶壓抑。但不知何故,黃色卻是童年記憶中最明亮的部分,一如自動隱去回歸前暗黑猩紅的曲尺、手榴彈、AK47自動步槍,只記得名字唯美的黃色炸藥。
時間在泛黃的日子中也默然流逝了:周末飲茶的燒賣、奶皇包、鮮竹卷和馬拉糕,校門口的咖哩魚蛋,和兄長天天流連的美式快餐店,吃不起的路環葡撻,母親做的片糖湯圓和燉蛋,父親凌晨一點下班後喝的冰啤酒,母親在街上被搶的小金錬,在公園廣場迎風高飛的黃色風箏,茶餐廳午後出爐的合桃小蛋糕,奶黃色Forever friends小熊床鋪,金髮碧眼的葡文學校學生,已經消失的黃色電召的士和黃頁電話簿,和母親共吃榴槤、芒果時的尷尬與洋相百出……長大後看到巨型黃色小鴨在澳門海上飄著,沒有喜悅與療癒,只覺刺目。在寸金尺土的北區,在節約水電的新移民區,浴缸可是奢侈品呢──幾經艱苦才爭取到一雙冬天洗碗用的黃色橡膠手套,我哪敢奢望其他無用的玩具。
小時候,萬物於我皆無比稀有,唯獨時間可以盡情揮霍。因此糖果只咬一半,紙巾只用半張,床鋪的枕頭就是我的時間囊和保險箱。記憶中最深刻的黃色,不是故宮的黃色琉璃瓦,不是黃色建築遍地的墨西哥小鎮伊薩馬爾(Itzamná),而是父親給我剝的一片橘子。一口大小的尋常的飯後果,一種近乎條件反射的淡然關愛,被我珍而重之地收到枕下,生怕幸福即生即滅,明日不再。做完一個橙香四溢的夢,一覺醒來,只剩一堆壓碎的果肉、濡濕的枕頭和悔恨無言的我。
人生頭一次看清楚傷逝的顏色與形狀。一片平凡的橙黃橘子,教會我活在當下。從一毛不拔地保留,到囫圇吞棗地愛。
清代《芥子園畫傳》有云:「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唇齒、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中國古代書畫主張「遺貌求神」,不似西畫特別重視明暗和色調的作用。人的記憶,卻和古書畫相似,時間久遠,片段的顏色又淡了,面目又模糊了,恩怨情仇,最後化成一片暖黃的塵埃、黑白的水墨,心就自由了。
如今的黃色,是淡黃的日記、藏書、父輩的臨時證件,印在馬路上的鮮黃標記,大三巴旁夾雜著陶片、貝殼、碎石的土黃色舊城牆;是穿過跨海大橋時的橘黃日落,新填海區的滾滾沙塵,金子般發亮的賭場外牆;是半夜醉看的鵝黃街燈,是父親墳前土黃色的香。

直至長大成人,我才敢承認自己有多喜歡黃色──在中國古代代表高貴,在當代淪為色情的隱喻。雖然黃色事業在澳門如此發達,黃色建築在這座小城又是如此尋常。
按《閱讀澳門城市色彩》的研究指出,澳門建築文物立面的色調以黃、綠、紅、藍為主,黑白色系只佔百分之五,黃色系及綠色系的建築物卻佔整體的六成五。用法國色彩學者讓.菲力普.郎科羅教授(Jean Philippe Lenclos)創立的「色彩地理學」(Geographie de la Couleur)學說的觀點來看:任何城巿景觀所呈現的色彩,必然有相關的地理文化學成因。黃色在傳統的葡萄牙建築規範上,屬於宗教建築的慣用色,而黃色主體建築,加以白色線條勾勒出建築樑柱和裝飾紋樣,配以百葉窗,最能體現南歐風情的教堂格調,如聖奧斯定堂的米黃和聖老楞佐堂的象牙黃。何東圖書館的檸檬黃是一抹午後清涼,一如在蛋黃色的聖母玫瑰堂裡,輕步走上百年鐘樓,木板吱吱作響,莊嚴中散發著隨時樓塌的冒險氣息,測試上帝愛不愛我。
每次到香港,總不期然想起澳門,最大感覺是城巿顏色的轉變,以及建築物的高度之別。被某些學者喻為「歷史廢墟」的澳門,比香港開埠早了三百多年,曾是遠東重要的中轉港。至1578年,澳門已擁有居民近萬、教堂五座,葡人房屋共二百多間,以灰白色為城巿主調──「垣以磚,或築土為之,其厚四五尺,多鑿牖於周,垣飾以堊」,用白色的石灰來裝飾牆壁,如媽閣廟的外牆,早期為磚灰而非今天的大紅色調。
城巿色調的變化,也是時代變遷的明證。澳門近代建築在用色上像廣彩瓷器般大膽,好比薄荷綠的墳場、桃紅的陸軍俱樂部、鮮藍色的社工局,色彩豔度之高,在亞洲可謂首屈一指。如今的素雅,只餘鄭家大屋了,近年重鋪的葡式黑白「石仔路」,美則美矣,但實用性大不如前,主要是討旅客歡心之用──手工粗糙,下雨容易積水、濕滑無比,對高跟鞋尤其不友好。
偏偏澳門遐邇馳名的人情味,包含了逆來順受的天性。對城巿規劃無動於衷,認為填海造陸理所當然,深信刺眼反光的賭場建築越多越好,但城巿的多樣性卻每況愈下,旅遊博彩業的獨大,漸漸凌駕於澳門居民的日常生活──以色彩比喻,就是見證可愛的奶黃變成土豪金的過程。
《美國大城巿的生與死》中反覆強調多樣化環境的重要性,無論顏色、形式、材料如何多變,在單一功能的建築群裡,還是不存在真正的建築多樣性。近年本土文化淪落至為旅客服務,向來有荒寂之美的內港,也強行被官方的七彩壁畫和潮流塗鴉所佔,有如在老婦臉上化了一個豔俗的濃妝。
紅、橙、綠、藍、紫、絳諸般色相,在一個真正多元的城巿,理應素艷共生,方能迷人。但以顏色的多樣,美化功能的貧乏、掩蓋地產霸權的獨一,這虛偽的繽紛讓我覺得不安。
時間用以虛度,那是孩童視角;在成人眼中,時間在澳門是用來沖淡一切的,讓你慢慢忘記如何愛一座城,學習接受無所謂的人生。但話說回來,假若澳門的時間有顏色,在我心中便是黃色。它讓人想起晨光與落霞,雛菊的可愛與草木的頹敗,還有童年與成長──帶著淡淡的橘子香,讓你在千瘡百孔的城巿裡,不忘記愛的修補作用。
(此出版計劃由澳門基金會贊助,並獲澳門筆會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