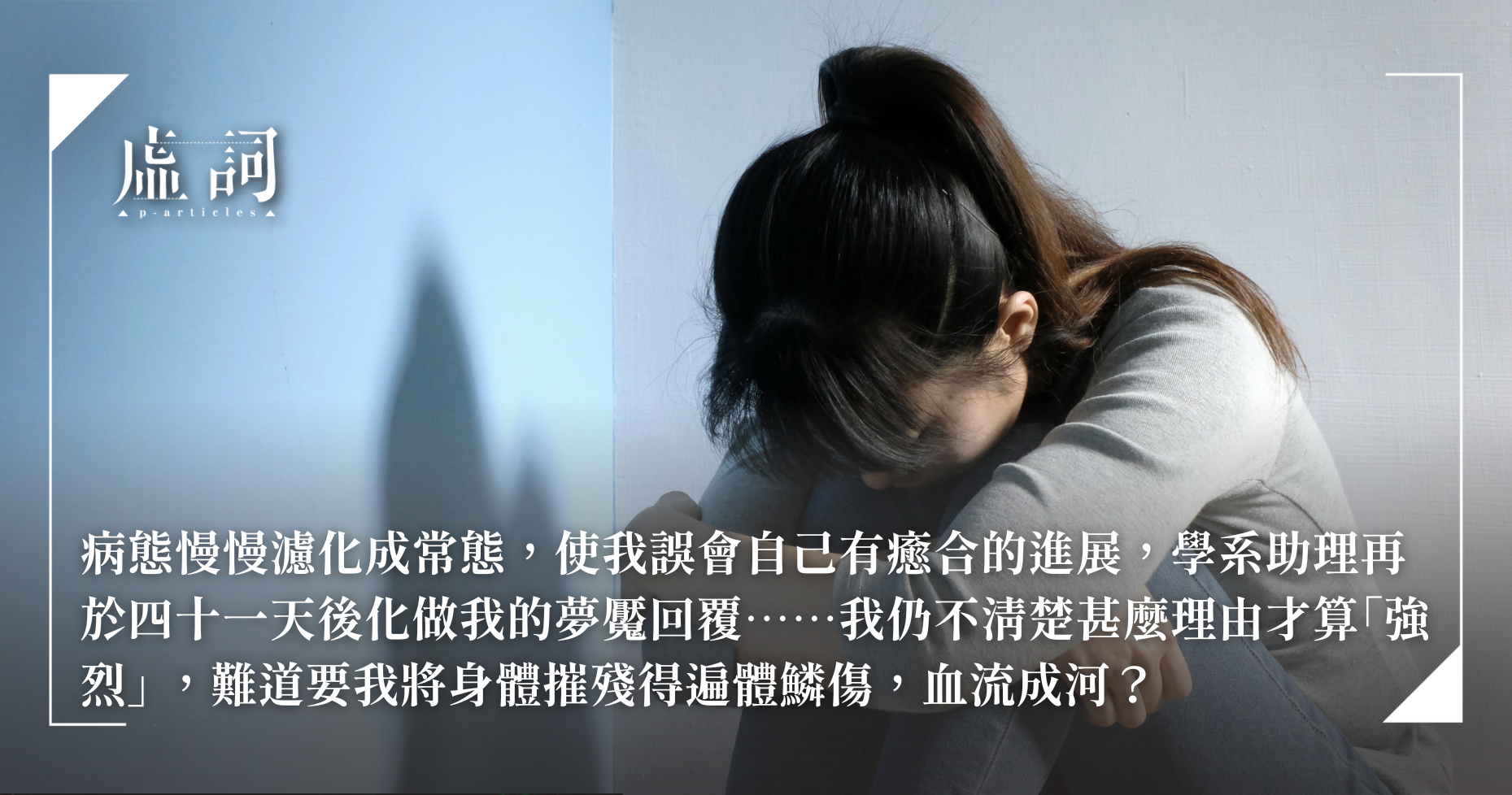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病
教育侏羅紀 | by 佘潁欣 | 2025-04-07
轉科是我一年前便做好的決定,所持學分也遠超標準,但學系助理仍將我的退修請求攔截說:「因為你還是(某科)的學生。」學系部門要求我提供「強烈理由」才能退修,如呈交醫療文件證明自己因病無法學習。早知我將要轉科的他們就像病嬌,用盡反智行為想留住我心,妄想我多修一門課就會回心轉意。
為什麼一定要證明自己「有病」,才算是一個「強烈」的退修理由?我感覺自己在這裏失去了靈魂,但只要沒有醫療文件證實,他們仍可質疑靈魂是否確實存在。我理解程序是工作所需,那又有誰來理解我?
為獲得支援文件,我開始定期約見輔導員。當她說出席記錄也是醫療證明,我便立刻詢問學系助理出席記錄是否足夠當證明。一天、兩天、三天,我也沒有收到她任何回覆,只有一個意義未明的藍剔。或許他們打算在逾期退修的限期前一晚拒絕申請,令我的學分一夜便因那個“F”而低於三,藉此把我強行留下。我每兩星期都要向輔導員更新那停滯的程序,直至我真的在等待期間「喜獲」精神病⋯⋯
謝謝部門的悉心栽培,讓我明白自己也能有確診的機會。
在我不斷檢查電郵的日子,我逐漸厭倦這種懸著的不安,嘗試與輔導員聊人際、家庭、理想。當我儲齊數張潔白的A5長方出席紙,我就將其繳交到退修系統,稍稍遺忘對未知的恐懼,等待結果,重投生活。
病態慢慢濾化成常態,使我誤會自己有癒合的進展,學系助理再於四十一天後化做我的夢魘回覆:「出席紙不能作『強烈理由』,需輔導員的信證明『你有問題』。」我仍不清楚甚麼理由才算「強烈」,難道要我將身體摧殘得遍體鱗傷,血流成河?
距離逾期退修還剩兩星期,我不解為何連早有答案的二元問題也需時四十一天去回覆,他們大概認為限期前兩星期是一段充裕的處理時間吧?他們壓根沒想過對於一個有焦慮傾向的學生而言,兩星期限期是枚兩秒內可以顛覆她生活的地雷。
輔導員需獲學系請求才能寫支援文件,寫支援文件又需時一星期,她再將我轉介給大學醫務處,醫務處再將我轉介去精神科,排期見醫生又需時兩個月。我感覺自己是個沾滿泥巴的球,他們一接到就會想將我拋給別的部門,最後沒有人願意接緊我,沒有人抹去那些讓我渾身不適的髒物。我就這樣不斷被拋接,任憑方向或是速度都不能由我去控制。我只能等待從一邊落到另一邊,沉浸在因頻繁移動產生的暈眩。
我的生活又被迫返回這場輪迴,每天醒來都好像複製了昨天的焦慮。
後來,我約見了學業指導教授,請她為我寫申請退修的信,作為附加支援文件。我向她訴說對學系的反感,分享它如何影響我的學業規劃,又如何加劇我的病情。她微笑將我綁回牢籠,重新指導我這裏有很多值得我去學習的地方,輕輕將責任添置到我肩上勸說:「不只是你有壓力,所有人都有。」明明我們都在說粵語,卻儼如兩個語言不通的人在交談。我不懂回覆她,她是想我答「是喔」、「大家都辛苦了」、「一起加油」嗎?跟她告別後,我隨即去見輔導員,見完輔導員再去見醫生。我如此將困擾複述三次,又將情緒演繹三次。
來來回回,我開始對自己的焦慮麻木,它已徹底融入了我的呼吸。
這天,我獲得了三份支援文件,包括出席紙、輔導員的信、醫生轉介信。我凝望這三份用普通A5白紙列印的長方文件,有些甚至連會面時間都沒有由負責人員親自填寫。若不是申請退修,根本不會看出分別,畢竟它們只是換了人名日期的統一描述,無特別標註。支援文件被我上載到退修系統,並在限期前兩天申請成功,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但沒有特別高興——
因為,我意識到病的不只是我,而我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