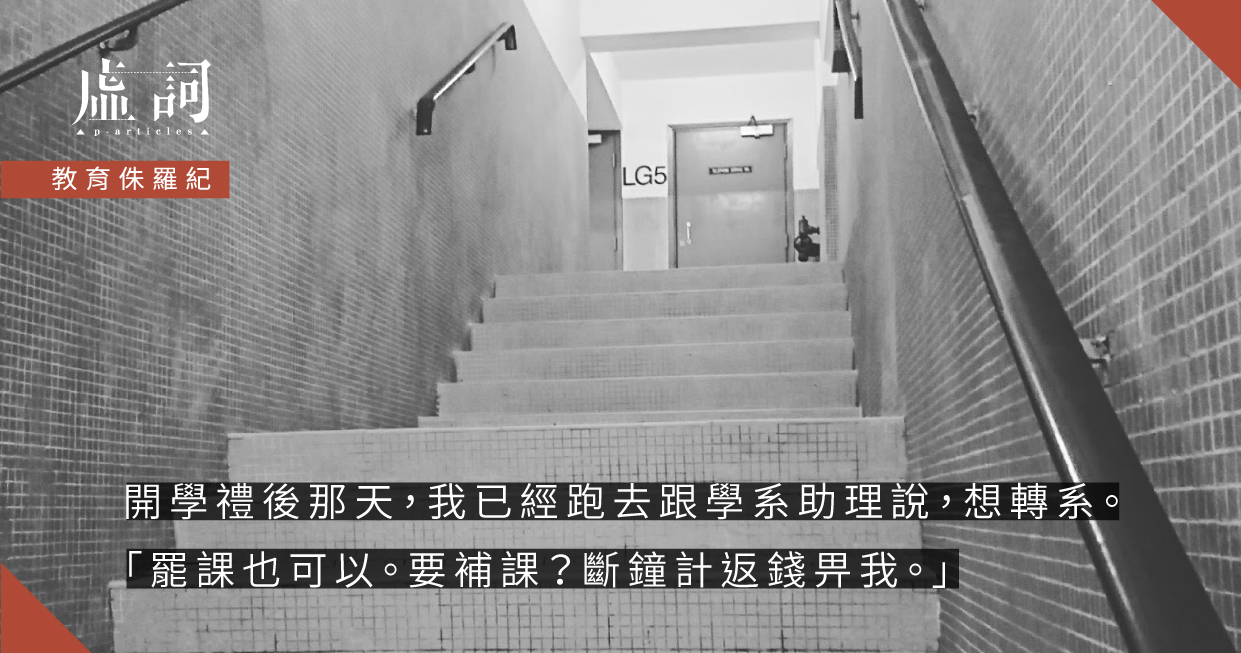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畢業】那些年,我聽過最殘忍的話
我討厭歷史,正如我討厭自己。
身為一個唸歷史系的大學畢業生,站在歷史與時代的關口,總是無能為力書寫。
甚麼是大學的價值?是在明明德?是培養獨立自主的反叛精神?是所謂的大學五件事?
畢業禮當天,人人笑容滿面,容光煥發。我看著以二十多萬學債換來的畢業證書,忖測各人臉上的答案;而我又不禁回溯,四年前的暴烈與虛無。
「補課?斷鐘計返錢畀我。」
2014年,重考公開試。放榜,選讀樹仁。
甩難。這是最初的想法。上半年那崩塌的狀態,已把自己逼瘋——親人離世,失戀。看港聞,報人被斬,我怒得在臉書上打滿粗口。如今看來,一切言行都很可笑,真的十分可笑。
「如果你想當老師,對不起,這學系幫不了你。」
「我們不會安排到甚麼機會給你們。」
開學禮後那天,我已經跑去跟學系助理說,想轉系。
「罷課也可以。要補課?斷鐘計返錢畀我。」
「我唔會為你哋做啲咩。」
9月26日,學生衝進公民廣場。28日,示威者佔據金鐘海富六條行車線、灣仔告士打道與分域街一帶。我在分域碼頭。
電話傳來發放催淚彈的消息。人群開始推擁,原來最前方的人已經被煙霧逼退。朋友、中學老師傳來訊息:快離開。再不離開就沒命了。
翌日,回樹仁與系方老師開會。那時的我,第一次明白:原來在某些人的眼中,用87枚催淚彈趕絕學生是合理的事。又,原來五四運動裡,學生打官員、燒官邸是行義;這裡的大學生,佔路示威,要求對話,就是雖遠必誅。
有些人,只配在地獄得到永生
明明大家都在讀同一本歷史書,有些人真的會這樣,literally crazy。上課三小時,一半時間說政治。
「搞示威唔好舉雪山獅子旗,學黃之鋒幾好,又食到女。」
說判斷事件是講statement的人,總是在下judgement。
還有一課。另一個奇異「博士」,著我們用六何法比較兩宗新聞報導手法的異同。不要緊,我早已對這學系失去所有期望。兩次公開試都考得差,只有樹仁作最佳的升學選擇。我抵死。
二年級,沒有人斷鐘計錢給那位「老師」。他最新的學術興趣,是學生對校政的批評。
「妄自菲薄,自怨自艾。唔鐘意讀咪唔好讀囉,冇人拎枝槍指住你讀!」
人必自侮而人侮之。這句說話以後,我再不能禮貌地,當面喚他「老師」。
如果天真的有眼,我希望他那就讀國際學校的兒子,將來會是同志平權、多元成家運動的最堅實支持者——因為這樣,就是對這種集極右、建制、反同與廢老於一身的人渣,最大的懲罰。
活得像一條狗
「你畀人拉咗,我會要你即刻退學。」
曾幾何時,我以為自己可以消化這句無情的說話——我不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的不孝子。我不想再因為自己的情緒,辜負他們的愛與緣份。
住宿的關係,我可以四、五天都睡在金鐘,有時間跑趟旺角,之後再回寶馬山。入秋一病,又得休息三、四天。
17樓只有一格洗澡間有恆溫熱水供應。回到宿通常是早上八、九點,上早課的人已經佔用無誤。沖洗幾分鐘。還是回房鑽被窩更好。
即使不回家,父母還是能夠讀到你在網上的言論。你以為隔代真存在坦誠溝通?罵自己事小,獻醜事大。前輩出頭,想以理勸服蠻牛。我只想搵窿捐。
家裡罵你敗壞家聲,學校說你冇腦廢青。
樹仁不大,幸好還是依山而建,總有孤清零落之處。有時上課上得難以忍受,LG5與LG6中間的無人樓梯,是挺適合我這種活得像狗的人,抱膝哭嚎。
If you can’t beat them
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相信:自己曾在四年前的10月,協助行動組織在學校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
香港還是一個大商場,與監獄。大學的存在,也只是篩出有用與沒用的配件,而已。
2015、2016年,我發現不少同學、同齡朋友參加各式各樣的內地基金會、交流團。著西裝,飲紅酒,去晚宴,上電視。如此很好。大家都有各自的難處。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選擇目前道路的原因。比起他們,我仍然時刻質疑自己當下的價值。
獲內地大公司聘任、當建制派議員的社區主任、考警察或公務員⋯⋯ 聽著畢業禮上的興奮笑聲,四年以來,好些熟悉的身影,早已隨我那些自以為勇悍的部份,可笑地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