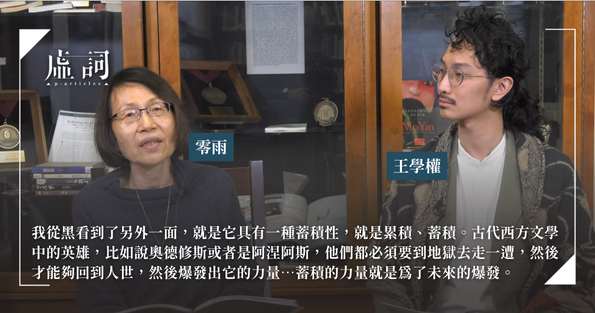社群平台是鴉片還是錘子?歐陸理論家赫特.洛芬克《困在社群平台》新書分享
專訪 | by 謝達文 | 2026-02-23
荷蘭媒體理論家赫特.洛芬克(Geert Lovink)著作《困在社群平台》繁中版於去年年未推出,並在近月到訪台灣舉分享會,與聽眾一談交媒體的本質。會上,洛芬克以「鴉片」與「錘子」為喻,批判當代社交平台讓人成癮、陷入內爆,繼而主張應將社交網絡視為工具,用以達成特定目標,使用後即擱置,而非如平台邏輯般要求用戶永遠在線。洛芬克認為解決之道應是推廣Fediverse或Signal等應用程式,拾「組織」的動能,透過建立更分散、自主的網絡架構,讓溝通重新服務於共同的行動目標。 (閱讀更多)
談《極樂海》——筆訪詩人石堯丹
專訪 | by 李浩榮 | 2025-12-18
香港詩人石堯丹最近出版其首部詩集《極樂海》,詩集中可見他與多位前輩詩人的對話。李浩榮藉此機會與他進行筆訪,大談他所欣賞的前輩詩人,一窺他們如何影響石堯丹的創作。石堯丹讚揚楊牧詩作極具音樂性、節奏感,用字古雅且情感厚積薄發;也斯的詩作則讓他感受到城市觀察下的生活無奈,詩句輕盈卻情感沉重;邱剛健的詩風以暴力、血腥、死亡與情色為特色,風格獨特。 (閱讀更多)
筆作陽具,道成肉身——訪崑南天地人最終章《去年人間世》
六十四年過去,人世間盡是記憶混和的時間,崑南的「天地人」三部曲終告築成。鑿開過地的門,跳過一場顛倒的天堂狂舞,崑南最終回落塵世,凝視《去年人間世》,雖九十高齡卻永遠年輕,創作力洶湧澎湃,彷彿也在與時間玩著變身遊戲。崑南笑言:「我的起點就在終點,你不用跟我爭。我很自信,我寫的東西沒有人寫得到。華人作家來說,沒有人學我這樣寫。我一向是前衛,我走在前面。」站在終點回望,崑南早看透人間種種不過一場大夢。 (閱讀更多)
寫小說就像寫一隻貓在伸懶腰:訪韓麗珠《裸山》(下)
再續榮獲2025年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及入圍「2026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香港作家韓麗珠《裸山》訪問上篇,在下篇中她視此書為突破過往魔幻風格、回歸「瑣碎」日常的嘗試。韓麗珠表示自己視小說為一頂巨大魔術帽,探尋生活難以看見的本質;散文則置於寫實之中,令她寫來無壓、純粹快樂。《裸山》三名主角皆經歷重大失去,卻指向一個共通真相:只要愛,就注定關乎失去。韓麗珠認為藝術的最大意義不在改變社會或流傳後世,而在創作那一刻給予作者的意義。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