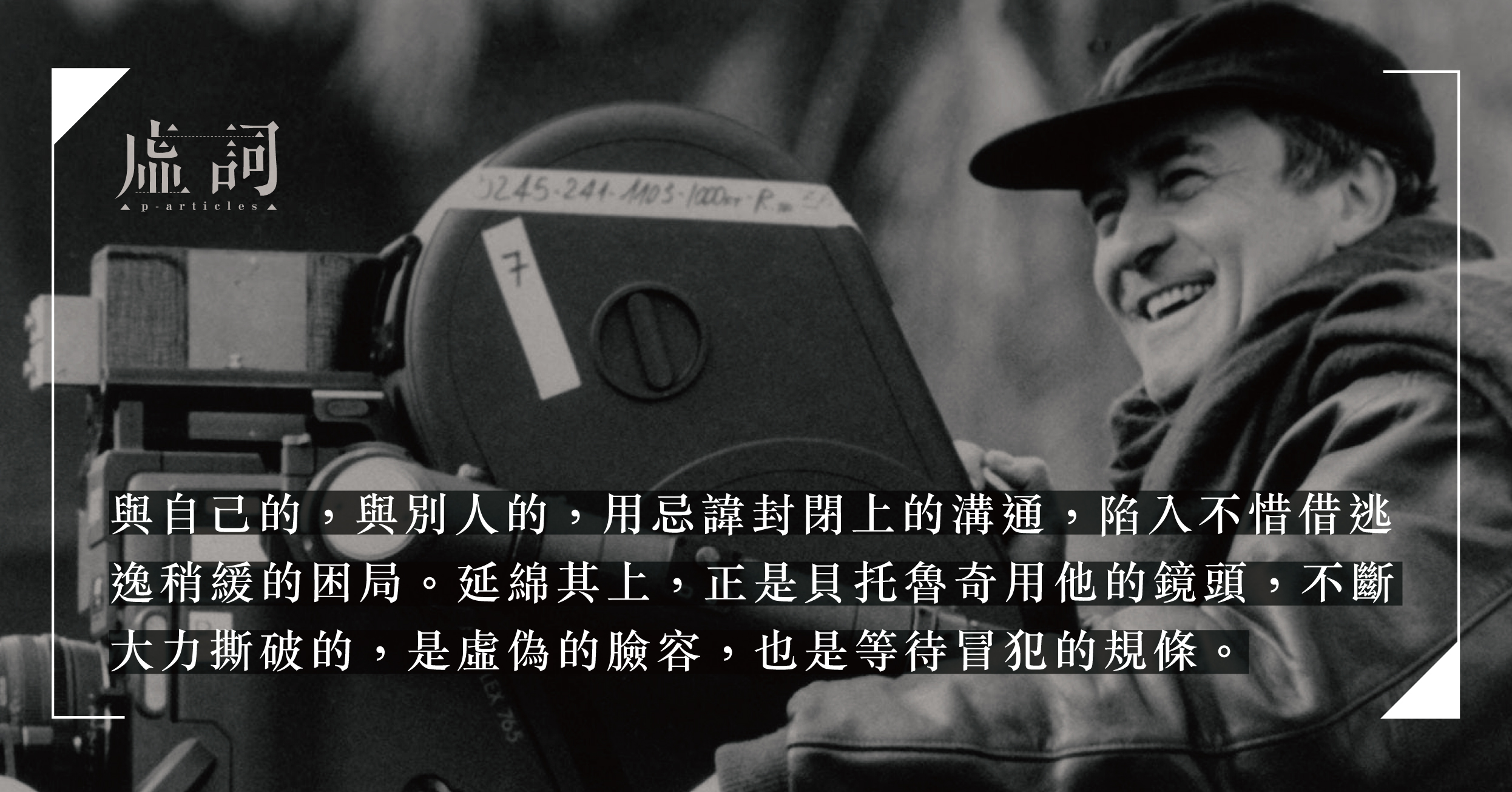犯禁與溝通:貝托魯奇追尋的真正革命
很多年之後,《月亮》(La luna,1979)的兩幕影像仍在我腦內揮之不去。第一幕:母親日間在陽台跟剛開始走路的兒子玩耍,父親拿著捕獲的魚回來,母親注意力轉到他身上,開啟留聲機,扭動身子與之起舞;失去了母親的兒子看在眼裡,哭喪著臉,晃著纏繞毛線的赤軀投向外祖母;下一個鏡頭已是晚上,母親推著嬰兒車在山路上獨行,抬頭望天,一輪明月高懸。
第二幕:長大了的兒子用粉筆在城鎮的牆上畫線,走到哪裡便畫到哪裡,最後消失在一間廢屋前;另一個少年跟縱粉筆跡找到他,在高處的破洞看見兒子在下面注射海洛英,少年用姿勢「嘲弄」他,弄出的聲響嚇了兒子一跳,連忙把注射設備掃到一旁。然後是一個交代兩人所處位置的遠攝鏡,左上角的少年與右下角的兒子——一個曾經到過紐約再回歸意大利,處處顯得格格不入的孩子。
直面亂倫誘惑,徘徊虛無深淵,最後以大母親的歌聲洗滌父與子的苦罪,《月亮》堪稱我最喜歡的一部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作品。2018年尾貝氏仙遊,「年僅」七十七歲。年初還聽聞他正籌備拍攝新作(一部愛情電影),噩耗傳來不免有點愕然,唯有借重溫他為我們留下的多部傑作,致以深切悼念。
貝托魯奇出身文化世家,屬於早慧的創作人。十五歲開始寫作,廿一歲就拍出處女作《死神》(La commare secca,1962),編劇還要是柏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那是一部《羅生門》(1950)式的電影,妓女被殺,警方盤問不同疑犯,每個謀殺版本間之以雷暴和妓女死前在家準備出門情景,風格先聲奪人,雖然擺脫不了柏索里尼的影響,卻已為貝托魯奇贏得不少掌聲。

《月亮》(La luna,1979)
不過,真正讓貝氏揮灑自如,盡顯才華的當推其第二部作品《革命之前》(Before the Revolution,1964),《月亮》不少主題原型均可以在裡面找到——迷惘少年、死亡陰影、亂倫禁忌,手搖鏡、大特寫、跳接,直接連接生命的躁動和意識飛躍,而且是在貝托魯奇的家鄉帕爾馬取景。看過電影的鮮有不被片首即出現的好友對話打動。——心儀共產主義的中產主人公法比西奧(Francesco Barilli飾)與好友奧古斯天奴(Allen Midgette飾)分享彼此面對的沮喪和時代困惑。後者提及對家人的惡意,並且觸及箇中更深刻的階級仇恨。騎著腳踏車的奧古斯天奴嘗試在法比西奧面前表演雜技,一次又一次跌倒,一次又一次重試,直至一次倒下不太能動了,法比西奧上前扶起他,而這一切可能不過是一次沒有點明的閃回——之前一組鏡頭是奧古斯天奴騎著腳踏車離開主人公,鏡頭從主人公的腋下目送他遠去。「你打算幹甚麼?一場革命?」他拋下了叩問,同時預言了主人公的失敗。
貝托魯奇是著名的左翼導演,他和柏索里尼的投契並不偶然。其更多觀眾鍾情的作品《同流者》(The Conformist,1970)和《1900》(Novecento,1976),都有濃烈的社會主義關懷情味。《同流者》對法西斯主義展開無情的批判,強烈的視覺風格、畫面經營及簡約有力的場面調度,令不少影評人一直懷疑王家衛的影象美學脫胎自彼。《1900》更是史詩級的巨構,五小時多的放映長度、超級巨星〔羅拔迪尼路、謝勒狄柏度(Gérard Depardieu)、法蘭車思嘉佩天妮(Francesca
Bertini )、蘿拉貝蒂(Laura Betti)〕的參與演出、波瀾壯闊的場面、宏闊的歷史視野(一語道破法西斯在共產主義管治下復闢),初步展示貝托魯奇有糅合美國電影類型及歐洲電影風格的能力。他這種跨文化跨範式能力在十年後的《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1987)得到進一步印證。
對貝托魯奇來說,反法西斯是一定的了,但另一邊的社會主義理想,畢竟到最後難寄厚望。《革命之前》裡,明顯乃貝氏夫子自道的主人公,其所面臨的革命既非社會也非政治的;法比西奧和阿姨珍娜(Adriana Asti飾)的不倫關係,衝擊圍繞他建立的整個人際關係和人倫世界。她搭上他,傷害他,最後揭開她其實才是受害人,並且有能力反過來「救贖」後來放棄了理想,選擇同流合污,屈從社會模塑的他(對,就是做conformist)。珍娜便是這場革命本身!而主人公最終背叛了這場道德革命,最好的他留了在革命之前。
理想不足恃,於是在情慾關口前駐足,並且嘗試探測可否推至最極端的程度——這大抵是《巴黎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1972)的大前提。這部惡名昭著的作品令貝托魯奇長年受到官司及批評困擾,因為反法西斯的他被發現在創作裡,在片場上卻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者。他與男主角馬龍白蘭度「同流」,合謀宰制當時年尚丁齡的女主角瑪麗亞施奈德(Maria Schneider),充份說明了假藝術之名,他可以讓自己結下的繩圈套上自己的頸項。誰說他不也是將最好的貝托魯奇留在電影裡?電影當然就是他世界裡不斷進行的革命;現實的他,有時不免成為某種逃兵。

《巴黎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1972)
觀眾不難發現,《巴黎最後探戈》的主人公保羅(馬龍白蘭度飾)是一隻撲火的飛蛾。激進點說,電影一開始他便「死了」,整個故事彰顯的他之自毀,透過放縱、胡為、控制和傷害別人最終反噬自己的另類情愛,他渴望死神之吻而最後如願以嚐,不過是為自己舉行的一場喪禮。不明所以的觀眾嗅出了頹唐、腐化、資本主義社會下人的無望;了解逃逸與莊嚴辯證關係的,則能體味貝托魯奇嚮往的自由真義,不得不在死亡驅力圍繞慾望對象不停打轉的過程裡,一再提煉,然後通過考驗。
明乎此,《情陷撒哈拉》(The Sheltering Sky,1990)之被視為貝托魯奇晚年佳作便不難理解了。電影改編自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的英文原名小說《遮蔽的天空》,講述一對感情陷入困境的紐約夫婦到北非旅行,讀者很快發現丈夫其實是去尋死的,而妻子在丈夫死後被阿拉伯人擄走,淪為性奴。貝托魯奇找來尊麥高維治和狄寶娜穎嘉飾演這對夫婦,將他們表面難以理喻的心路歷程,透過影象語言拉長成為超過兩小時的視覺盛宴。電影裡一再強調的,那出發便不打算回程的旅行,再一次以情慾為布幔,遮蓋住呼之欲出的深層理念,我們未必要以「自由」稱謂之,因為它是被禁止的,就像女主人公在故事中段「被迫」戴上的面紗,被迫戴上的手鐐腳鐐,我們不便揭開解開,以免讓虛無與自由的結盟,把僅餘的潛在知音人也嚇跑。
竊玉偷香從來是貝托魯奇的暗喻與反諷,《盜美人》(Stealing Beauty,1996)片首以帶著自嘲意味的偷窺者鏡頭,追隨美少女麗芙泰勒出入無礙,並不旨在炮製另一齣《一樹梨花壓海棠》(Lolita,1962,寇比力克導演)。麗芙泰勒飾演的露茜,代表了一眾不堪成年失去的純真與初心,卻放肆地發出被污辱的邀請。貝托魯奇用最情色的方法突顯人們對自己的背棄,然後將被背棄了的東西置入禁忌裡,打破禁忌因而成為不可避免的儀式。
到了《戲夢巴黎》(The Dreamers,2003),貝托魯奇索性畫公仔畫出腸了。表面上透過一名美國青年的眼睛去嘲弄「六八風雲」包含的法式浪漫,以冷峻實用,被美式帝國主義「污染」了的視點(這裡當然再一次包括了貝托魯奇的自嘲)解剖左翼理想,將之「還原」成有點可笑的天真感性。同樣有亂倫暗示的雙生兄妹,標誌著等待打破的禁忌,但美國青年最後選擇後退了,他的「覺醒」彷彿置自己於「同流者」(這次是同流於浪漫革命)之外,但其實是把投身宣示為誤會,合理化自己「躍升」為一度不願意成為的大人。這時,有心的觀眾可能會記起《革命之前》珍娜在電話亭向遠方心理醫生的聲聲呼救;種種愛與誠,革命的擁抱與投身,難道不就是連場注定溝通不了的溝通嘗試嗎?與自己的,與別人的,用忌諱封閉上的溝通,陷入不惜借逃逸稍緩的困局。延綿其上,正是貝托魯奇用他的鏡頭,不斷大力撕破的,是虛偽的臉容,也是等待冒犯的規條。

《戲夢巴黎》(The Dreamer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