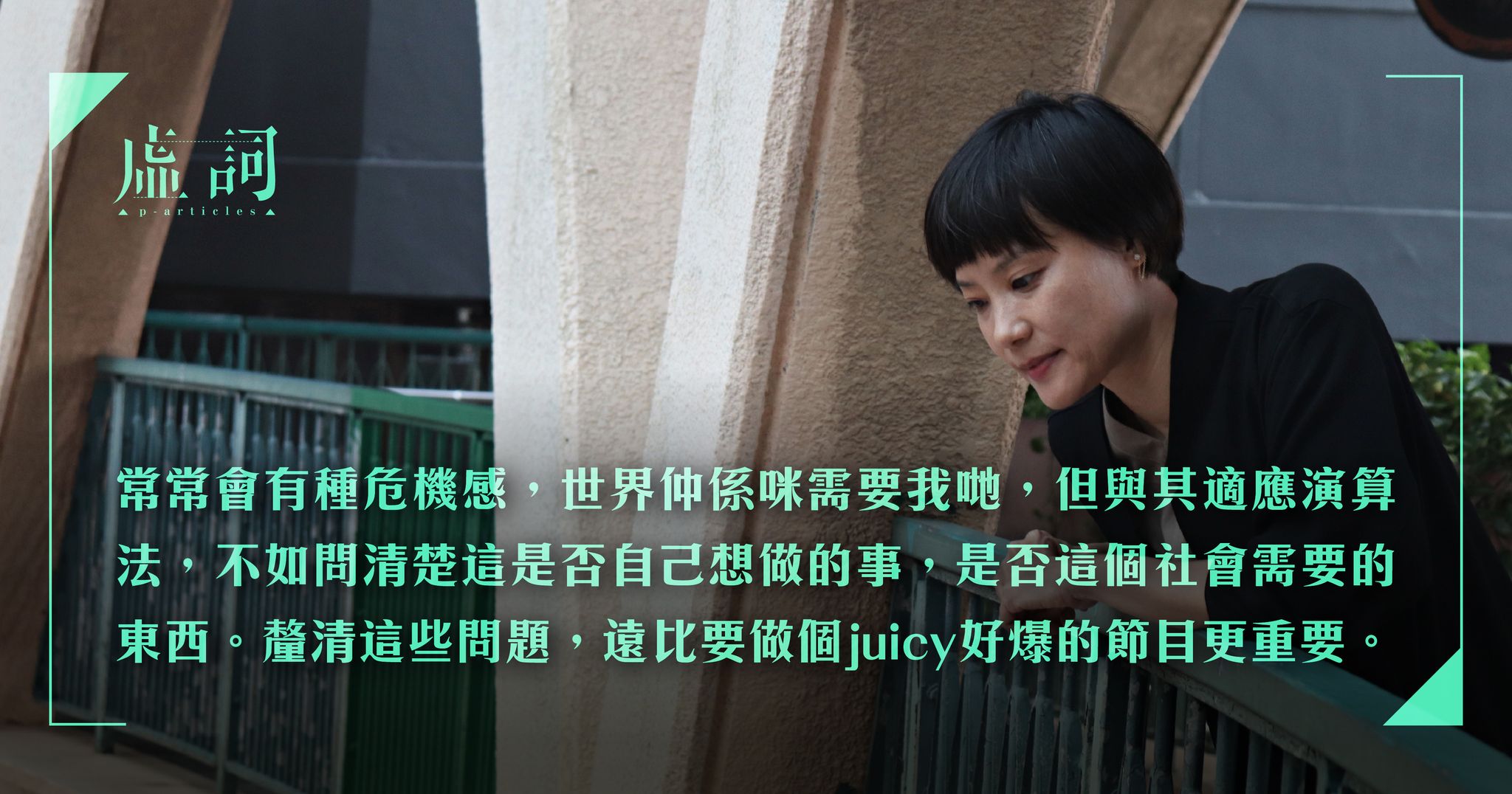訪「眾聲號」團隊——感動到一些人就可以,繼續做值得做的事
港台節目《鏗鏘集》今年經歷停工,節目內容亦多次被無故抽起,前監製李賢哲與其他編導離職後,以他們的方式繼續紀錄香港人和事,另闢新平台「眾聲號」,分別製作關注社會時事的《眾聲集》,以及側重人物對談的《冒號開引號》。轉移陣地,繼續傳承,《冒號開引號》監製Dora與《眾聲集》編導Fanny,分享她們與團隊如何延續《鏗鏘集》的精神,在變幻的時局,繼續紀錄香港日常。
「點解好睇,是要真誠」
離開港台,沒有了體制的框架,在新平台可作更多嘗試,無奈社會環境所限,紅線難以捉摸,任何題材與訪問內容,都有可能變得敏感,Dora認為現在製作節目的最大局限,來自時勢。「局限並非來自我怕些甚麼,而是整個世界不同了,現在很多人唔想講嘢,就算對方答應受訪,可能很多事情唔敢講,或者講得唔詳盡。其實運動之後,要找嘉賓都有困難。但也不至於要censor自己,我們一直都是以專業的角度作衡量。」雖然新平台的兩個節目,定位皆非要以勇者姿態挑戰時局,Fanny坦言今時今日製作節目,也要顧及受訪者的安全,即使他們願意無所不談,節目播出前也會再三思考。好像《眾聲集》第一集,以「末世公民」為題訪問鄒幸彤,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原本約好的訪問,也因對方被捕而提前結束。「身處這個時勢,很多與社會政治有關的東西,都沒辦法不去觸碰,但我們知道能在新平台繼續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也不想稍瞬即逝,會很bear in mind並非要衝出來挑戰時局。經歷2019年,整個社會令我們的題材都偏向政治,但其實以前《鏗鏘集》也有做人物關懷的題材,之後我們也會夾雜在節目當中。」

節目播出兩集後,網絡上也引起不少迴響,《冒號開引號》頭炮找來伍家朗與盧覓雪對談,亦為節目帶來了一個好開始。要做好這類對談節目,Dora覺得最重要是能讓嘉賓與主持擦出火花。「其實每次都沒有心目中的A配B,而是本著去找有趣的人這個想法。我們很著重主持的input,從第一輯到現在,每次定好主題後,主持人都絕對不會是讀稿機器,節目好睇是因為主持投入,觀眾覺得他們所問的問題,與其身分很相稱,亦與過去的經歷有關,這樣會來得比較natural。」看似簡單的操作,但團隊背後所費的功夫,卻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如何令對談節目變得獨特,除了借助大量的資料搜集外,讓被訪者在現場真心而觸動地重述往事,Dora說還得須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我們希望做到的訪問,是關於那個人獨特經歷的故事,對方講得返裡面的領悟。講就好易,但有時可能準備得好好,若被訪者不在狀態,或者主持問不到,也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當坊間的訪談節目多不勝數,要突圍而出,Dora認為關鍵在於訪談予人的觀感,是否夠真。其中一個她很喜歡觀看,並經常作為參考的媒體素材,是在紐約街頭蒐集故事的企劃《Humans of New York》。「那些交談對象,全部都是不認識的人,但為何這些訪問特別好睇,因為被訪者講到人生一段很獨特的經歷,即使遠在美國發生,我在香港也會睇到喊,證明一個有human touch的故事,是無分國界的。」這種從被訪者身上,找到共同的通感並感動觀眾,也是Dora希望在對談節目做到的效果。「點解好睇,是要真誠,如果是個真誠的訪問,我相信觀眾一定會想看,現在是個大家很care是否真誠的時代,MIRROR點解會紅,大家已分析過一萬次,因為他們夠真。市面有很多訪談,但多以輕鬆娛樂為主,如果某些人能夠分享他的經歷,讓大家知道原來仍有人走過這些路,我覺得已經很療癒,希望觀眾看完會開心,也會感到溫暖。」
為求拍到真摯的訪談內容,團隊事前都會做足準備功夫,然而拍攝現場太多事情無法預計,Dora說「每次都係博一鋪」,並由此談及她製作第一輯《鏗鏘說》,至今仍教她印象深刻的訪問。「某次我去做yoga,落堂後老師跟另一同學聊天,說起為何會來做yoga,原來他讀醫要考試,經常覺得自己很蠢,然後他說:『呢排有個訪問,自己一想放棄就會去睇,每次睇完又再返去溫書。』我知道他說的,就是我們製作的節目,亦令我覺得無須感動全世界,只要幫到一個人走過某些路,已經很好。」這集名為「醫者的初心」的節目,在該輯《鏗鏘說》也是很常被談論的一集,製作團隊與被訪者梁慧康,重看當年訪問片段,對方回憶廿多年醫者生涯的真摯,鏡頭外亦令人動容。「醫生受訪的那刻,現場已很感動,我們沒想過他會說得這樣好,而他又願意交出心來分享經驗,現場也能感覺到特別容易撻著的氣氛。」
紀錄意義非在當刻,而是再之後
「不要懷憂喪志,讓我們再一起試試。」這是《眾聲號》監製李賢哲在節目開播前,於社交平台的寄語,也是他與戰友們在通訊軟件的群組名稱。作為《眾聲號》的靈魂人物,監製李賢哲帶領前《鏗鏘集》團隊,過渡到這個網絡新平台,繼續紀錄當下的時代。雖然此刻李賢哲並不在香港,但Dora與Fanny說他每天都跟團隊保持緊密聯繫,運作模式跟以前《鏗鏘集》時代相比,分別不大。「因為我(Dora)是《冒號開引號》的監製,相對簡單,風險也較低,我告訴他有甚麼訪問人選,他亦不會太理;但因為他是《眾聲集》的監製,involve程度亦較多,會參與傾故仔、睇片等,(製作流程)其實跟以前差不多。時間方面,是要與他捉緊,但始終現在我們出片不算密,就算他不在港,事情還可趕及處理。」科技發達,隔空也可遙距指揮節目的運作,但面對香港風高浪急的變化,每天與李賢哲在群組裡通訊的Dora與Fanny,都說很能感受對方身在異地,因時差而感受的那種無奈。「有段時期,每朝都發生很多事情,邊個邊個畀人拉咗,記得李賢哲離港那天,正是教協解散的日子,我完全感受得到,他每天起床拿著電話的崩潰,看過一大堆message,原來個世界又差咗。」
《冒號開引號》監製Dora,《眾聲集》編導Fanny則在鏡頭以外受訪。
最初《眾聲集》與《冒號開引號》的構思,是每個月各播放一集,後來如監製李賢哲所說,「在具體討論拍攝題材時,很快就碰上時效性、新聞性等新聞學的基本問題」,與團隊經過討論並調節後,節目暫改成每三星期播放一集。如何填補每集之間的疏落空檔,Fanny說曾經考慮過製作短片,但團隊始終覺得「long form」的製作,才是他們最想展現的方式。「當初我們也有想過,是否可以分成三條十分鐘的短片來發佈,迎合觀眾,不過我們還是想一氣呵成,始終講故仔的方法與整個鋪排都不同,帶出來的感覺也會不同,也是我們想stick to的東西。」以往有整個電視台作後援支持,所得資源自然比較充裕,現在轉型網絡製作,幕後人員亦有所減省,縱使資源不及港台年代,Dora仍然有信心能保持節目的質素。然而,網絡生態總是難以估計,製作付出的心力與觀眾反應,經常不成正比。觀眾有多重視團隊背後的心血,也是Dora很關注的事情之一。「如果我畀少好多錢,但都有這兩個人對談,觀眾肯唔肯,其實我不知道,這刻我們還在摸索網絡觀眾,是否value這些額外之物,但如果我們還有空間,都希望提供比較靚的視覺觀影經驗,始終品味也是一種抗衡。」轉戰網絡平台,投進媒體經營的新世界,Dora與Fanny說有很多東西,他們仍然處於摸索階段,但在尚未要為演算法服務前,先做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更為重要。「當要思考有乜新嘢可以做,就覺得自己好像甚麼也不懂,因此常常會有種危機感,世界仲係咪需要我哋,但與其適應演算法,不如問清楚這是否自己想做的事,是否這個社會需要的東西。釐清這些問題,遠比要做個juicy好爆的節目更重要,至少此刻我們覺得仍然有紀錄的需要,就先做我們認為值得做的事情,真係唔work再算。」
亂世之下,紀錄片更有存在的價值。曾經參與製作港台節目《鏗鏘四十年》的Fanny,重溫不同年代的歷史檔案時,覺得當中最能觸動自己的,是當初某些可能只為meet deadline而製作的故事,原來紀錄了某個很特別的場景與時刻。「除了自己喜歡做之外,原來也並非只為我自己,可能紀錄了時代很重要的事,或者一個人很重要的經歷,這些東西過咗就冇,只有當刻才有這種感受,五年十年後再看就很有意思,無論歷史重演也好,自打嘴巴也好,自我實現也好,意義並非在這刻,更大的意義是再之後,無論是誰拿來再看,都是個很重要的記錄,這也是我為何要堅持投入做紀錄。講真,做咗唔會改變到世界,但能放在歷史長河裡,紀錄片的吸引之處亦在於此。」
能在新平台延續這份精神,固然值得鼓舞,然而Fanny與Dora對媒體生存的前景,同樣偏向悲觀。「與所有人的想法都係,行到幾多行幾多,對我們的意義是要好好珍惜,做盡佢,你永遠不知道能否做落去,也不知道自己還可以轉化幾多次,始終每次進化與轉變,都需要耗費不少力氣與勇氣。」對於「眾聲號」的未來方向,Fanny說只能先做好當下,看看將來能否擦出新的火花,再行到另一條路。這種想法,亦如Dora對《冒號開引號》的願景般,紀錄社會之餘,亦期望能溫暖大家。「有啲嘢你唔畀我做,那就繼續做我們仍然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這些東西,我們一直都有做,因此也無須覺得很委屈,未來可以繼續exp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