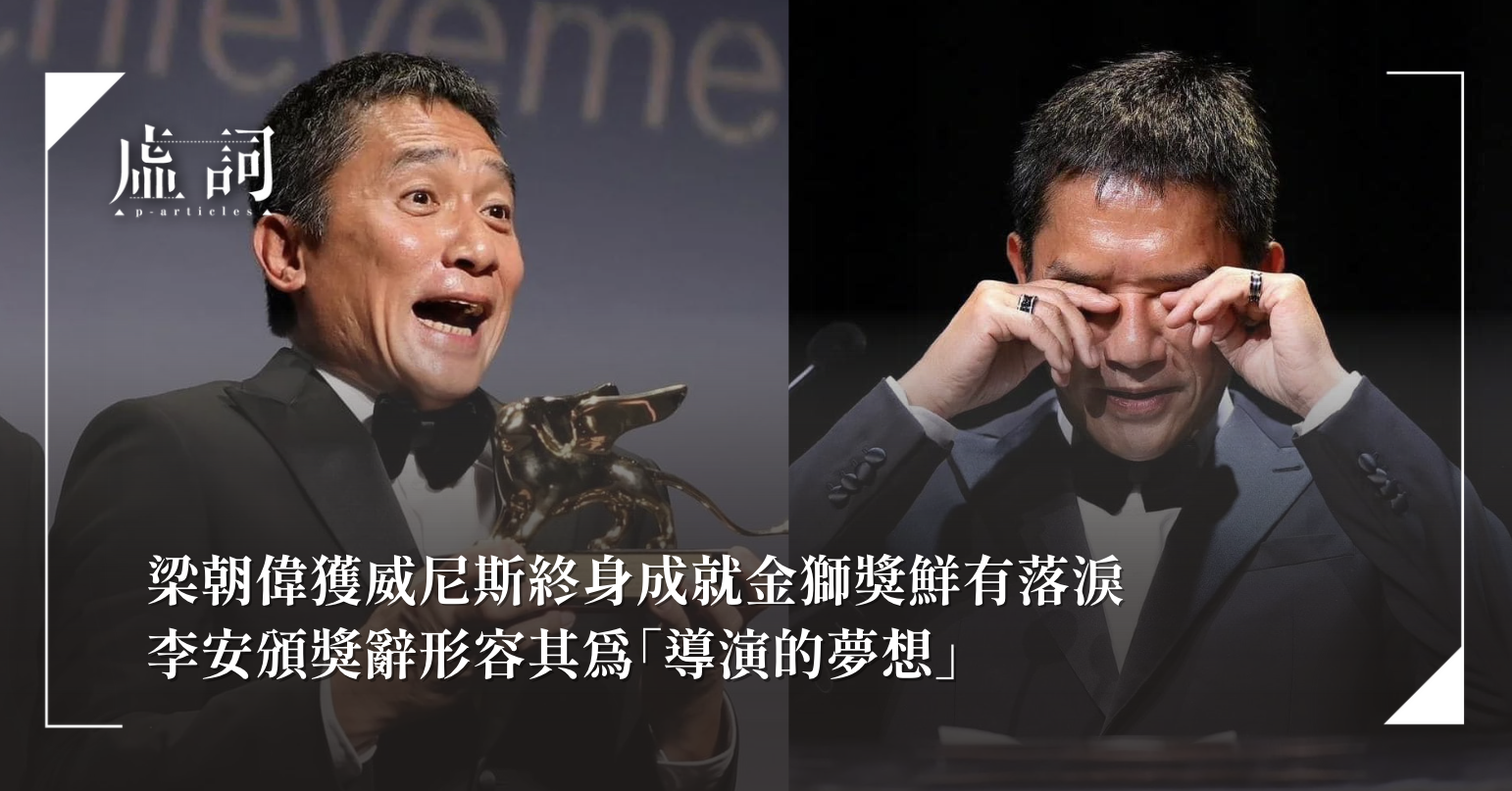【無形・致我們終將遠去的校園】前置詞:這些年,我們一起漫遊的校園
無秩序編輯室 | by 無形編輯部 | 2023-09-13
你好,你現在翻開的,是由七位作家建構的校園地圖。這裡展現的場域,可能是你記憶中某個鮮明座標,也可能是你從未到訪的異域。但無論如何,這場漫遊與探索,定必讓你重新想像觀看校園的方式。 就讓《無形》編輯部為你導航。 (閱讀更多)
【新書】《同道心影——記憶中的文友》〈顧城的城〉
其他 | by 劉以鬯 | 2023-08-31
香港中華書局今年推出劉以鬯散文集《同道心影》,收錄了〈顧城的城〉一文,又適逢顧城離世三十週年,當年《香港文學》第108期特此設計專輯,劉以鬯為其撰文,說明顧城、謝燁夫妻倆與《香港文學》的緣分與通信內容,由此表達對兩人的不捨哀逝,紀念這名詩人。 (閱讀更多)
首屆香港演藝博覽於下年末舉辦 本地與國際共襄盛舉 今開放報名參演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08-30
今日(30/8)香港藝術發展局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記者會,正式宣布首屆香港演藝博覽(博覽)將於2024年10月14至18日在港舉行,並且宣布國際精品演出及項目推介將於今天公開報名,邀請全球藝術人員及團體提交申請,參與亞洲文化藝術的重要里程碑,惟所有提案將由專家審視是否符合《國安法》,博覽亦將與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接連舉辦。 (閱讀更多)
心田先祖種 福地後人耕——郭詩詠X何福仁X劉偉成「從未離開的西西」講座紀錄
報導 | by 許茵茵 | 2023-09-07
西西一生筆耕不綴,書寫我城,為香港塑造了豐富的文學形象。故人已逝,但她的文字滋潤著一代代讀者們,從未離開。今年香港書展的第一天,大會便邀請到郭詩詠、何福仁和劉偉成三人舉辦題為「從未離開的西西」的研討會,和廣大讀者分享他們對於西西作品的看法,帶領大家走進西西作品中的世界。本次介紹的書籍包括電影評論《西西看電影(中冊)》,以及今年出版的詩集《左手之思》和散文集《港島吾愛》,讓我們可以感受到西西的作品正在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她的生命。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