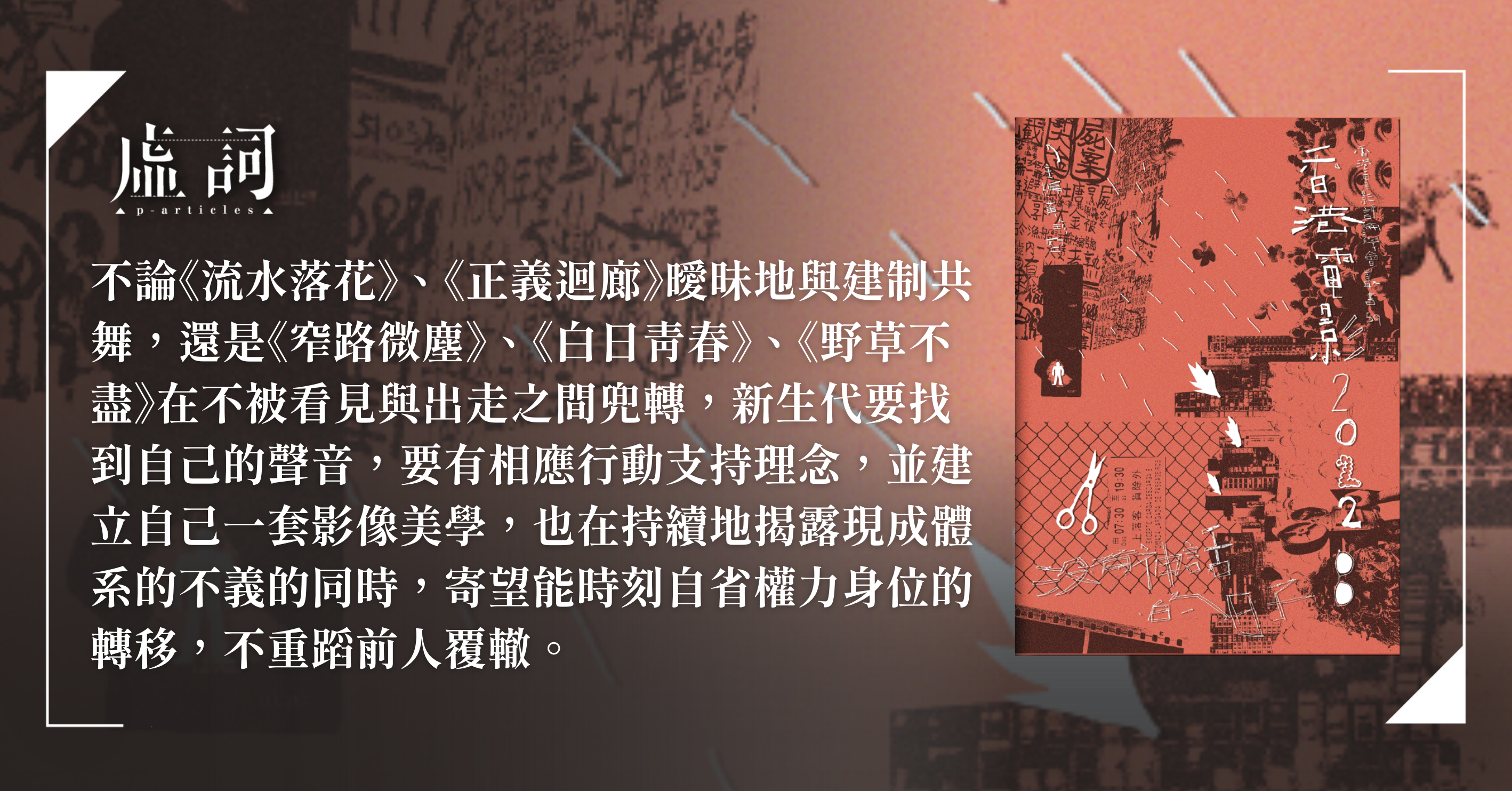【新書】新生代的出走與反抗: 論2022年香港電影
影評 | by 查柏朗 | 2023-12-22
上一代與下一代在價值觀、文化傳承或權力上的不對等,不只造成代溝,更往往引發下一代的出走、反抗,甚至是仇恨。2022 年的香港電影脈絡中,處處可見這種對立——於家庭是父母與兒女,於學校是師長與學生,於電影拍攝現場是拍攝者與被拍攝對象,於社會是當權者與受規範的人民。
高壓的愛、克制的愛
縱觀今年的香港電影,題材定位較安全的作品會選擇聚焦家庭,以小觀大——《飯戲攻心》、《過時.過節》皆強調齊人開飯,父輩不懂怎樣表達愛、長兄為父死抱不合時傳統,到最後分崩離析,後者結尾鏡頭看到一家人各自的區隔,前者則反枱重聚再高呼「走出去」。另一邊廂,風格、整體感覺最激烈者乃取材謀殺雙親案的《正義迴廊》,可惜電影放棄透過奇案的極端性去窺探兩代矛盾之源,與案件最為有關的情節,除最表面的樓宇資產爭奪外,就只有無人性的希特拉崇拜因子,反而在片中其他環節更見兩代行事想法之不同及衝突(警察、記者、律師及陪審團)。長片以外,在年輕新銳的短片中亦可見對校園層級架構的批判:《群鼠》中,領袖生假老師之威去欺壓同輩,暗藏學校管理層的默許;《防止自殺手冊》也劍指學校教師/高層及風紀所構成的威權式體制。
最全方位地呈現上述世代、師長與學生、被拍者與拍攝者之間的衝突者,當數《給十九歲的我》,還從戲內延伸到戲外。被拍攝學生的家庭背景迥異,有嚴格規訓、有疏離放任。學校方面,有教師看死某學生的嘴臉,也有教師「春風化雨」,但更大的衝突呈現於公映後被拍攝學生的公開信, 展示了學校內部對於學生權益的忽視。這有別於《群鼠》、《防止自殺手冊》的虛構世界,校方並不全然只關心自身,當中有真心的信念;片中的部分學生如「Madam」和「阿雀」皆表現出對拍攝團隊的接受,甚至更高度的信任, 從中不難看見團隊的態度並非完全沒有可取之處。然而,這無助於解決導演張婉婷與親自跟拍的兩個主角之間的問題。
影片毫無掩飾地交代了以導演張婉婷為首的團隊,在拍攝過程中與女生們之間的碰撞,可直接見於學生遮掩鏡頭,暗示在中三過後再沒有拍過學生家居的畫面,也印證後來外界對於這紀錄片計劃是否真的完全得到受訪者同意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張婉婷作為英華校友,以「大師姐」姿態去看千禧後出生的女孩,以旁白由上而下的引導方式,將她對學生們的評頭品足以及綽號起名(並非學生之間的稱呼)貫穿全片,甚或在某些場面刺激到受訪者情緒(學校放榜一幕最明顯),這種意圖讓觀眾更投入的方式, 很像商業娛樂片的操作邏輯。攝製隊追拍着一群想法避開鏡頭的女孩,校長竟將其歸咎於反叛,甚至有忘恩負義的論斷;副校就以「用上帝嘅愛浸死佢哋」作應對。這些可能是剪接的粗暴效果,卻足以反映電影主創團隊直至後期製作,仍缺乏相應的問題意識。
轉眼看《流水落花》,錦田自然風景連綿,花瓣落下流水處,漸飄遠直至消失於畫面——以流水輕送落花的方式去愛護下一代,正是「浸死」的愛之相反。「流水落花」一片名已表明主角一家的關係:不同寄養小孩的個案展現了孩子成長的不同時期,當中也有小孩不願意配合的情況,電影卻完整地呈現天美姨姨(鄭秀文飾)怎樣從不解到嘗試理解對方,並尋求對方了解自己的雙向過程,當中並非時刻扮演完美、妥貼的照顧者,例如曾按捺不住怒氣斥責文森(黃梓樂飾)尿床、獨留小孩在家,卻從不訴諸權威。
天美了解到其身份的局限:「姨姨」而非「媽媽」的叫法,從開首便表明她心裏清楚兩者之間的界線,到中段為建立情感才企圖摒棄當中區別, 嘗試面對分離之痛。天美姨姨無法為文森平反學校欺凌,亦不能介入小菁(李昀蔚飾)、家希(曾睿彤飾)等人的原生家庭問題,讓她意識到自己過客/中介的身位,只能在對方需要時去扶持、陪伴,而非解決一切疑難。
經過長期審視與調整彼此的距離,天美對「家庭」與自己都有更深入的認知,比有血緣紐帶的父母親更甚,明白個體的遭遇從來不能全權被另一個人掌控。相比《給十九歲的我》中所顯露電影作者過度的情感投射及在場痕跡,《流水落花》流露的奉獻精神更貼近前者亟欲刻畫的關懷,也許甚至更能貼近英華女學校辦學傳統所頌揚的基督信仰內核。《流水落花》作為劇情片卻較低調節制,寫人物趨向理想楷模,反而《給十九歲的我》要記錄真實,加上拍攝時長及創作取態,就易突顯箇中衝突,更引起話題, 不論正反。
失敗的救贖想像?
張婉婷及英華校方對於女生們或帶有好意的動機,但卻不斷重複着為學校、大局可將就一己私隱的論調,偏偏忽視新生代對自主及擺脫體制定義的渴求——她們早就不需要前輩大導演的史詩大敍述,拿起手機自拍自況捕捉小動態更是自在。
《給十九歲的我》這種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一廂情願,於《白日青春》倒反過來——劉國瑞作為年輕新導演,想像着陳白日(黃秋生飾)這個人物, 會不惜一切地幫助年輕人,是在親生兒子童年時缺席的移情、殺害對方父親的愧疚,也是自己命不久矣想豁出去的衝動。這些個人因素的堆疊,擴展到社會層面,其實就是一種「想當年我沒有好好為新一代着想、去規劃理想的未來,現在趁尚餘不多時間,讓我盡力能幫就幫」的補償心態。只是,若香港普遍的上一代根本沒有認為自己對年輕人有虧欠的話,《白日青春》的情感召喚就會顯得薄弱可笑。
在類型化的包裝下,《白日》後半段將關鍵的心理連環轉折套進一夜的電光火石之間:害怕被警察拘捕、寧願冒死逃亡而孤注一擲的非理性恐懼、「拯救年輕人」的狂熱,只有套入特定情境才成立,在某種被壓縮的時空下才被釋放,於日復日「復常」的香港社會,這些不安、罪疚、義無反顧,或僅被視為一時的虛妄。沉重的包袱只要不去觸摸,就不會痛楚, 若抗拒直面這些情緒,《白日青春》自然顯得「脫離現實」。
故事還不止於此,更進一步推論就算前人取捨再多,始終停在岸邊,被過去的包袱纏繞,不能再踏前。就當劉國瑞不了解(或只是不想展現)港人功利、講求成本效益的一面,就當「傾家蕩產」只是一個極端的寓言設計, 《白日青春》就是點明了上一代去到如斯地步,原來還是不夠盡,還是沒法給年青人任何保障。前路還得年輕世代自己去闖——金錢等資源可以給, 陪伴與指導則到此為止。哈山(林諾飾)往後會否被出賣?船隻會否駛到比香港狀況更壞的海域?大海影像、指南針特寫所指向的不確定與茫然, 將烙在觀眾腦海裏縈繞不散。《白日》的異鄉難民題材看似與香港最遙遠, 底蘊的心情卻最接近。
主演的黃秋生與執導的劉國瑞,不約而同在宣傳電影的專訪中交出對角色的兩種理解。黃秋生認為陳白日即使有善意也是相當天真,竟將小孩一人送去深海,那只是一種愚昧的偏執,舉動只是自私地為自己好過,而不為小孩真正福祉設想;劉國瑞則對角色更為憐憫,想表現白日在其有限選項下已交出他的極限,因此下達無奈的結論:白日與青春最終不會同行, 兩代「同路人」只是當晚限定。這可算是賈勝楓流水送落花的變奏,而《白日青春》的旅程更陽剛、更暴力、更凶險。《白日青春》體現了資深演員與新秀導演的角力,各自有其發自資歷與崗位的權力制衡,造就了片中的衝擊,火花不斷。
破解(偽)世代仇恨的循環
《白日青春》還以兩段父子關係各自身世的平行鋪展,點出了世代循環的悲劇性。過去的白日,當下的哈山,離開家園,面向深海,不知何去何從。片末的怒海教人聯想起許鞍華昔日代表作自非偶然,香港由始至終都在尋問着同一命題。
紀錄片《野草不盡》也在探討軀殼離開家園之後,靈魂是否仍留於此; 或若軀殼不走,靈魂會否反而變異?貫穿兩個移英港人的掙扎的,是香港的地景人事轉變:小孩懂得唸普通話宣揚「愛國」、公共空間掛滿中國國旗、牆上的圖騰或顏色消失⋯⋯上一代的因,造成下一代的果,形成詛咒,是《白日青春》、《野草不盡》的潛台詞,也是短片《九龍皇帝》的寓意:祖先沒有處理好的手尾,留待後人埋單。
《白日青春》渴望跨越國族、世代的共情能夠改變循環,於是哈山的殺父仇人選擇救贖,哈山也沒有開槍。這份心意也反映在梁銘佳及Kate Reilly 執導的《夜香.鴛鴦.深水埗》(2020)描述持有不同政見、不同世代價值觀念,或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如何選擇嘗試溝通,跨越樊籬,而非建立仇恨。大抵梁銘佳參與《白日青春》的攝影、Kate Reilly 為之任表演指導, 並非偶然,而是他們願景一致的憑證。《白日青春》在此看來就似是長片版的《夜更》(2020),將的士司機一夜面對的處境推向極致。
上一代的罪,不能以下一代的血去等價取替,反而只會持續衍生更多罪惡與鮮血——韋家輝經歷基督信仰的轉化,在《神探大戰》交出了對「輪迴」的最新答卷,至此成功推翻了從前電視劇常糾結的兩代仇怨設計,父親的罪報於兒子之上也是不義。神探父女的同路歧途,到凶殺案受害者後人的大報復,引申最後李俊(劉青雲飾)是否殺害方禮信(林峯飾)兒子以完成復仇, 闡述個體恩怨不應誅連血緣之親。殺害仇人兒女與伸張正義乃毫無關連,若對手是魔鬼,對親兒根本也無血性可言,互殺只是助長惡魔當道的仇恨世界蔓延。這亦是對於復仇戲碼,尤以亞洲或華語為甚長久以來的「誅九族」牽連,或在社會上常見的「死全家」詛咒的有效回應。
《神探大戰》申明,受害與加害不是固定的狀態,而會流動互換。曾被打壓的弱勢群體,可反過來掌握權勢;本來是正義的一方可以導向邪惡, 只因堅持自己是正確的一份執念。這執念可促成偉大的革新轉變,也可走入歧途而導致災難。2007 年《神探》留下沒完沒了的尾巴,皆因坦承「神探」都是人,不應該有分別,因此可以犯罪,《神探大戰》重申這點再作昇華: 正正就是人,就會有心魔(片尾見李俊鏡像為方禮信)。既然如此,就要時刻警醒,不要自以為義——探求真相,不等同自以為理解真相。
因此,世代壓迫實只是偽命題,真正於歷史循環的,是當權者對無權者的迫害——上一代之所以在各個領域成為被批判、挑戰的對象,乃因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掌握權力的一方,由個人的家庭單位出發,到校園、社會的管理亦如是。對權力的不自覺、對自己有絕對真理的偏執,就等同自比為全知上帝,即使有善良的初衷,也會將愛演繹為惡。
《給十九歲的我》戲內的記錄、戲外的延伸,就是《神探大戰》無意中批判的對象。聯合導演郭偉倫於金像獎台上發表的感言,可以是大義凜然,也可以是十惡不赦,視乎其出發點;社交網絡的攻擊留言,同樣出於正義,卻有可能超過了對方應該承受指責的比例尺度。是以片中形容善惡僅為一線之隔,大邪若正,「大惡若善,絕對的執念」,就會讓人墮入深淵; 「我們不是神,只是探」的謙卑,檢討自身盲點與不足,才是唯一解決之道。
饒有意思的是,《神探大戰》與《給十九歲的我》的創作意圖皆有基督信仰的引領,卻有着正反的觀照。連同黃秋生就《白日青春》受訪引用聖經「回歸小孩樣式」的演技方法去指出自己也要學習的林諾、前述《流水落花》與基督犧牲情操的脗合(鄭秀文的接演或非偶然),2022 年的香港電影也許普遍帶有某種精神信仰,以回應或抵抗當下社會的崩壞之勢。
新生代的沿革
《神探大戰》的訊息通透,電影本身能將之傳達給觀眾的力度卻不足, 源於其沿襲上一個十年的港產/合拍警匪動作片制式,這工業類型的美學不新鮮,甚至已開始被抗拒,尤其是「TVB 式」的尷尬特技。影片結局亦反映其保守,李俊與其女兒都有平反冤假錯案的衝動,只是女兒走上「私了」一途被否定,李俊拐了一大彎則仍被建制肯定、重新吸納,才有最後的說教, 相信制度可以制衡人性,及鏡中心魔的永恆掙扎。
反觀同年的新導演們,各有不同風格理念去拍攝這一個時代的香港電影,《流水落花》顯然受日本片的影響,尤其是枝裕和拍攝美食與自然風景變化的細節,及其非血緣家庭的命題;《白日青春》借鏡港式江湖片的類型, 套在導演原來對邊緣社群的關注;《正義迴廊》從選角、空間運用的光線/ 陰影、場景的剪接等,都顯露其舞台劇形式的傾向;《野草不盡》及其他類型的獨立紀錄片,皆在拓展這片過往在香港較少人談論的創作形式 (《給十九歲的我》本來可以是很成功的兩代電影人合作例子),還有《窄路微塵》偏近英式廚槽戲劇(kitchen sink drama)的處理。
《流水落花》的錦田遠離都市,仿如自成一國,偶然也要與外邊體系周旋,以談善言所飾的社工為監察/介入為代表。天美的崗位微妙,既巧用公共資源(做寄養父母賺錢),間中需忍受官方計劃的麻木,像文森被送走、小花(吳祉嶠飾)要出國,都不在其控制之內。《窄路微塵》比《流水落花》自若於體制邊界的描述更為激進,當中公共資源能給予Candy(袁澧林飾) 的支持全然欠奉。電影所提倡的是無權者乃同路人的互助精神,以微塵自喻, 不被大眾看見,那我們看見彼此就可以——窄哥(張繼聰飾)懶得向制度交代,以至被刑罰也不作多餘辯解,就按自己判斷是非尺度去做人,即使要冒着被背叛的風險,也堅持同理諒解,那就是Candy與窄哥之間的相濡以沫。
《窄路微塵》與《流水落花》分別對建制的無視與抵制,到《正義迴廊》、《白日青春》進一步挖掘既得利益者(或曰上一代人)所建立的腐化系統, 及既定意識形態的偏見。《正義迴廊》各個第二梯隊的刻畫,初級探員(王雍泰飾)、年輕記者(柯譯誼飾)、實習律師(梁雍婷飾)這些後輩,觀察着自己上司(邵仲衡、郭慧、林海峰等飾)的舊派作風,盡見不恰當的陋習: 疏忽證據、套取證供程序錯誤、無視採訪道德、不求真相只求應付工作要求等。新一代從而另起爐灶,期許合力建構更美好制度的願景。
《白日青春》所描述的社群更為邊緣,未來也更為灰暗絕望,只有被驅趕、被危害(法例陷阱、歧視、不融入主流群體),唯一堅持捍衛法律原則的哈山父親(潘文星飾)則一早死去,逃亡也不知何處為出路。到《野草不盡》,人物成功離去後,卻仍被陰影籠罩,步步為營,不能真正自由地發聲及行動,且思緒及牽掛尚留在本土。逃不掉或不欲逃,又無法正面對抗,怎樣在狹縫中體現自由,大概又要返回《窄路微塵》,到路太窄容不下,又重投怒海⋯⋯
不論《流水落花》、《正義迴廊》曖昧地與建制共舞,還是《窄路微塵》、《白日青春》、《野草不盡》在不被看見與出走之間兜轉,新生代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要有相應行動支持理念,並建立自己一套影像美學,也在持續地揭露現成體系的不義的同時,寄望能時刻自省權力身位的轉移,不重蹈前人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