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爾與香港空間革命
空間 | by 張一村 | 2019-0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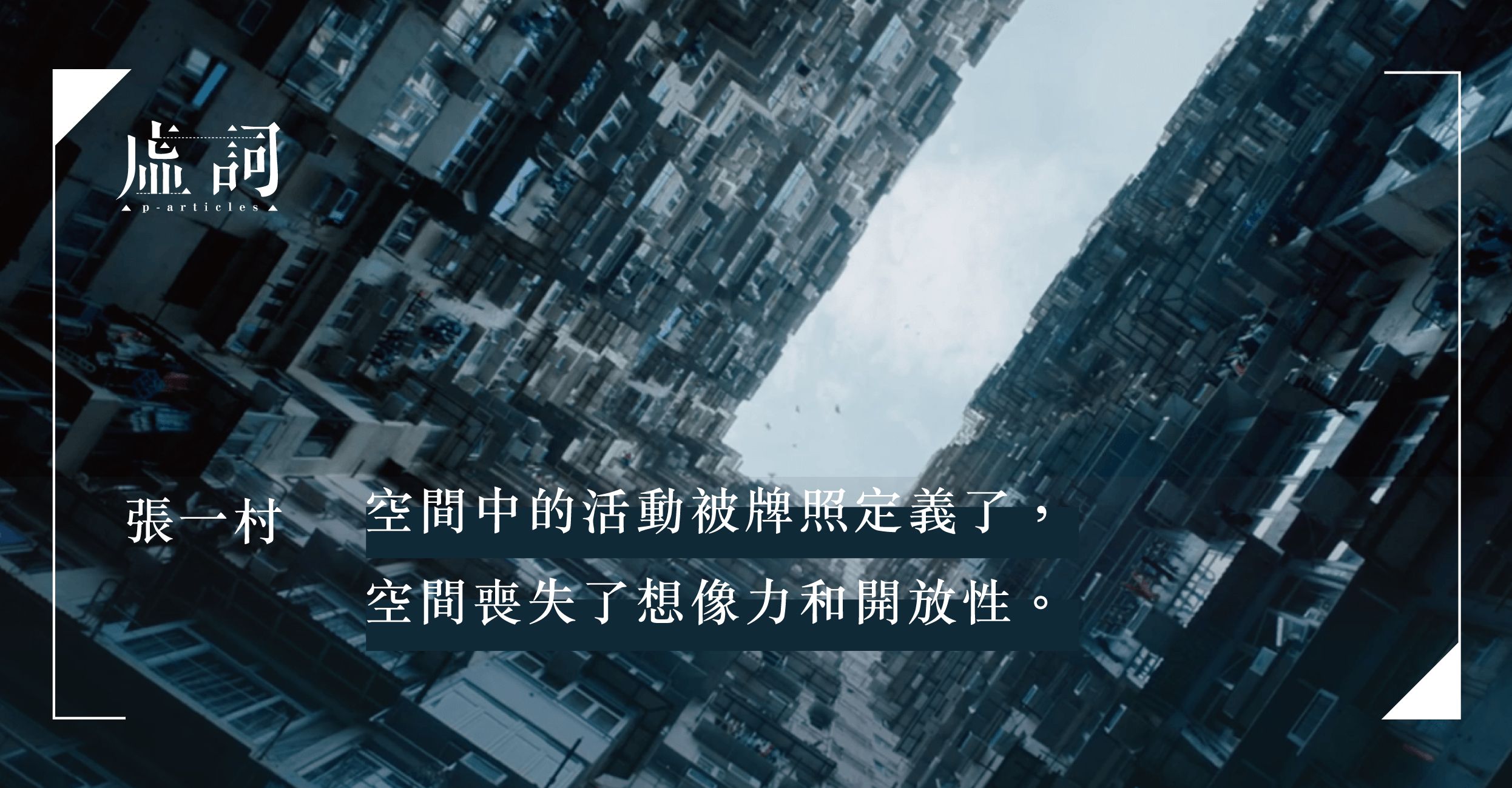
01.jpeg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
法國左翼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著名的空間理論,他提出沒有空間解放,便沒有革命成功。空間不足是表象,本質是支配空間的單向度權力需要解放。資本主義體系發展至今,已經由「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的生產」,空間本身已經被商品化,導致交換價值超過使用價值,造成空間功能與人的生活、生產活動距離漸遠,乃至逐漸異化,「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註1)
無死角的空間支配
這種空間異化源於資本主義「中心性」的建立,並造成由中心至邊緣支配權力的層級化,以致在邊緣底層的空間使用者,並不是空間權力的支配者。當社會以「幸福」作為人類的理想目標,並將安全視為「幸福」的首要條件(註2),「控制論社會」(cybernetic society)便逐漸形成。列斐伏爾寫道:「控制論似乎是科學主義最現代的形式……它們是校準者,禁止這個、規定那個,它們在一種邏輯的方式中進行組織、每一種信號系統(如交通信號燈)都決定著一種處理機械,只有命令才能有運動。」(註3) 社會輿論在致力渲染和消滅不安全因素的風險之時,無形中亦在建構和鞏固「中心性」的權力架構。
在今日香港,「控制論社會」的情形俯拾皆是:只要政府以「危及公眾安全」為由,即使在芸芸億萬棵樹中,只有其中一棵因為風雨而倒塌誤中行人,「寧枉毋縱」式的斬樹也是理所當然;即使芸芸千萬間工廈中,只有其中一間發生火災,所有工廈的多元用途(如開音樂會)也只能受到扼殺。當政府將對風險的認知能力從個人手中搶奪過來,個人便可以不帶腦袋「存在」於不同空間之中,以致在香港權力核心的中環海濱舉辦成人展,即使只限定成人入場,展品卻要荒謬地遮蔽性徵,還要受盡道德輿論攻訐。形形色色的規限、牌照、契約,無一不在支配每一寸空間的使用。
單一化的空間若同死城
商業運作要達致盈利最大化,便需把流程標準化,以及做到機械性的重複。都市空間若以提升交換價值為目的,功能便會變得單一化、同質化,而這結果將同時與控制論社會追求安全的目標結成共謀。過往,公立學校的校舍在日間是上、下午校,晚上是供在職人士進修的夜校,假日可供借出作非牟利制服團體活動,以及舉辦會議、考試、比賽等活動;然而到了現在,公立學校體系在教育產業化之下分割出直資、私校、IB學校、副學士書院、自資進修書院等各自為政的院校,伴隨而來的是空間使用的封閉化。多功能式的社區會堂、大會堂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歌劇院,未來則是戲曲中心,功能愈來愈趨向單一和僵化。在私營領域,前舖後居是違反公契的。住是住,商是商;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空間還被牌照制度規管著,經營食、住、行、樂都需要為特定的空間領有特定牌照,於是空間中的活動被牌照定義了,空間喪失了想像力和開放性。
空間功能單一化,更加方便控制論社會對空間自上而下的管理,財閥則配合將空間同質化。資本永遠是理性、精於計算的,經過資本運作的空間已經產生出一套交換價值最大化的標準。從一個住宅屋苑尚未建成之際,發展商便運用各種既定的符號指涉,不論是半山、深水埗、元朗、上水,皆統一命名為「御」、「璽」、「一號」。然後是間隔,在有限的空間下,房間越多越好,結果房間的標準面積都是兩米乘兩米。空間內的牆越多,間隔也就越為千篇一律:眼鏡房、鑽石廳、龍蝦則……結果室內的佈置屈從了空間,人的生活也屈從了空間。間隔、劏房是最流行的發展模式:住宅只有百多呎,舊商場、工廈被劏開數百格轉售。列斐伏爾指出,當社會「社會化」、生命「原子化」,「當交流與關係的網絡越來越厚積、有效、與此同時個體的意識就變得更加孤絕和對『他人』無視,這就是矛盾運作的層面。」(註4) 一旦商場變成劏場,商場便由此變得冷冷清清;一旦都市變成劏場,人被置於格子之中,都市便變得孤獨、割裂,從而喪失生命力。
權力結構與深層矛盾
空間既受權力支配,亦受時間支配。「時間被化約成為空間的限制」(註5),當生活以面向中環為目標,空間亦會被中環時間同質化:西鐵通車後,從元朗出中環的時間無異於從九龍出中環,於是九龍的人口逐漸遷往元朗,導致元朗的樓價變得跟九龍相若,而元朗與九龍之間的社區差異亦逐漸消弭。以中環為中心計算交通時間,都市像洋葱一樣一環一環地包圍核心,只有階級貴賤的落差,沒有社區文化的落差,於是深水埗、土瓜灣的舊區重建走向「士紳化」,舊社區的人情關懷遭受抹平。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時間綿延理論(durée)中,時間分為可切割、可量化的數學時間,對立於綿延不斷的意識時間;資本主義世界的時間是數學時間,誰將商品週轉的時間壓縮至最短,才能在競爭中生存。資本主義空間亦可作如是觀,當空間被同質、量化,社會便不再有象徵、輪廓、人文綿延。
因此,空間不足是假象,空間矛盾實質源自支配空間的權力結構,需要將「先前由『自上而下』生產出來的社會空間,重新建構為『自下而上』的空間」;「將取用置於支配之上,將需要置於命令之上,將使用置於交換之上」,再建立「普遍性的自我管理」。(註6) 雖然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在當今客觀條件下看似空想,但互聯網共享經濟的去中心化本質已經接近這種「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通過邊緣空間的自我管理,社會空間重塑思潮的孕育,將有望達致對「本真生活」、「缺席的生活」的還原。當大眾深信牛頓絕對時空的世界之時,愛恩斯坦卻看到了當物體具有相當的質量,便可以使時空彎曲,最終愛恩斯坦理論取代了牛頓理論,成為物理學的新典範。在今日都市的絕對時空之下,同樣醞釀著時空思想的新維度,最終需靠空間革命打破困局。
(本文原題為《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及其在當下香港的批判與實踐》)
註腳:
[1] 亨利.列斐伏爾著,王志弘譯:〈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載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47。
[2] 亨利.列斐伏爾著,李鈞譯:〈甚麼是現代性?──致柯斯塔斯.阿克舍洛斯〉,載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頁24。
[3] 同上註,頁38。
[4] 同上註,頁23。
[5] 亨利.列斐伏爾著,王志弘譯:〈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載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頁49。
[6] 同上註,頁5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