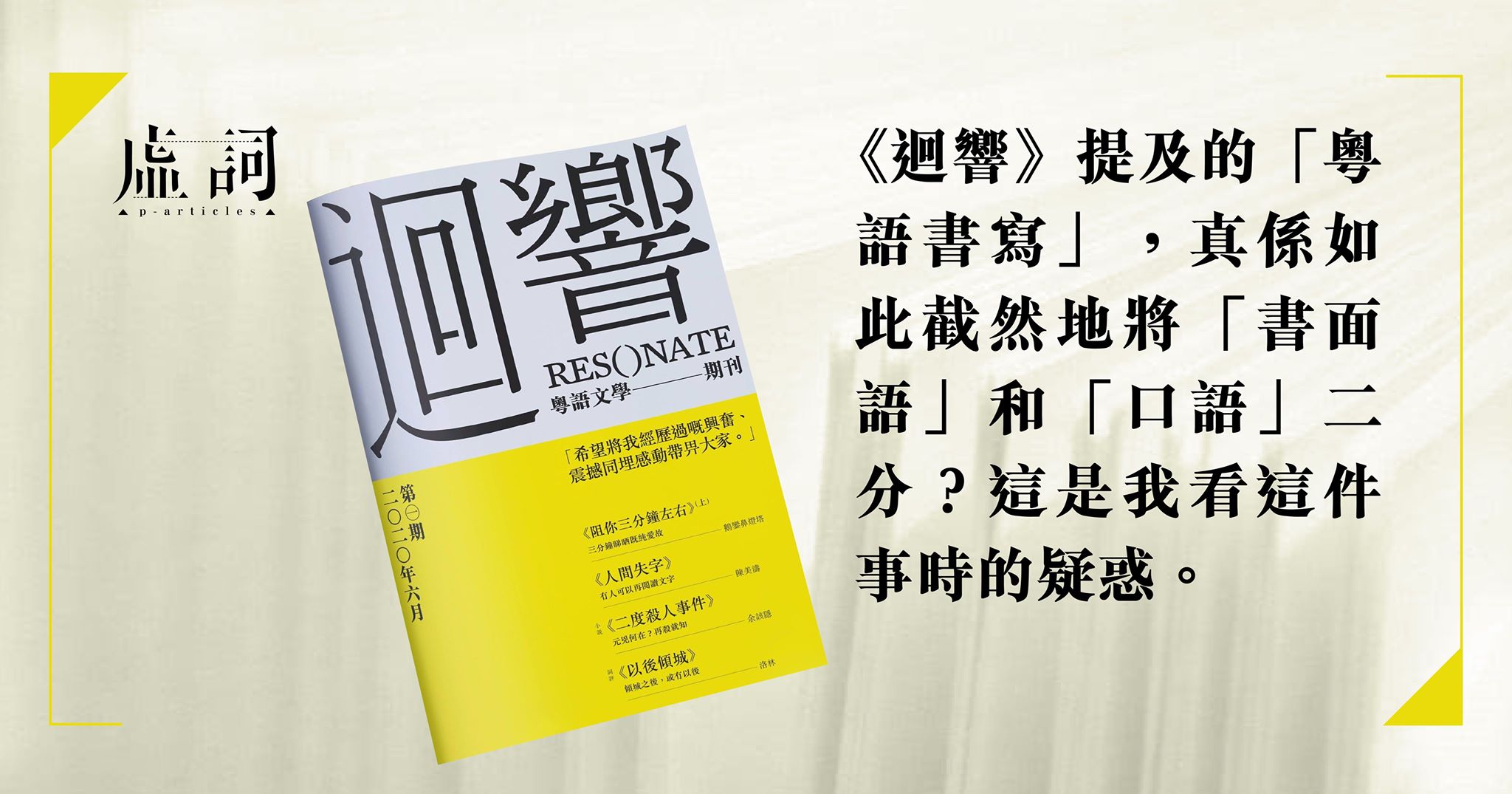【粵語文學期刊】關於《迴響》,我想講……
先講一個小故事,N年前,還在嶺南中文系讀書。有一科叫「各體文類寫作」,由也斯主講,搭配黃淑嫺、陳智德做助教。[1] 記得有次導修,也斯不知道係回應某同學的作品,定係整體地談甚麼是寫作,總之,他提出一個方法:一路寫,一路讀自己寫的字出來;至少是,是在心裡讀一次。聽從也斯教誨,從此每次寫任何文字,包括:學術論文、電郵、Facebook Status、IG動態,我都一邊寫一邊口郁郁,或至少是心入面「讀」出來。
要討論《迴響》這幾日的「炎上」,無論係已寫成文字的評論,還是本人身邊的文學/文化界朋友對《迴響》的負皮,大部份都係來自於《立場新聞》的一篇報道。[2] 譬如,有人用一整篇文章,逐點反駁總編輯豬伯的言論,尤其是他論點與論據截然二分的謬誤。亦有人行文暗指豬伯的講法,簡化港式粵語的複雜面貌,特別係將它和官話二元對立起來。這些批評肯定有可以替豬伯辯護餘地,但絕對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3] 所以,這篇文章反而想引進《明報》的報道去展開討論。[4] 報道一開始,記者已提出自身寫作的悖論:《明報》副刊行文習慣使用書面語,但報道《迴響》團隊主張,無法不使用多多少少口語。讀完成篇報道,似乎除了對話用口語寫外,不太見有其他部份採取《迴響》編輯群主張的港式粵語成份。與此同時,上述提及回應《迴響》團隊的文章,都是有以用全粵語寫成。《迴響》提及的「粵語書寫」,真係如此截然地將「書面語」和「口語」二分?這是我看這件事時的疑惑。
於是,我試著比較《明報》和《立場新聞》的報道,看看怎樣可以在期刊出版前,捕捉到它某些面向。一比之下,發現前者比後者更能使讀者對它的內容有初步的輪廓。關於期刊的內容,如果我沒看錯,立場記者用間接轉述的方式寫道:「內容方面,他(豬伯)認為可以粵語作為引子,用大眾熟悉而親切的語言重新產生閱讀樂趣。」但係,除了這一句很簡單的關於期刊語文的描述外,讀罷整篇文章,不見得更理解這部文學期刊——尤其係以「粵語文學」為名的期刊,是如何用期刊的方式——即係「稿例」——定義「粵語文學」,有的只是好勁的soundbite:《迴響》係當生意去Run。相比之下,明報記者起碼有一段,通過其中一位編輯阿擇的講法,帶出《迴響》審稿準則:「閱讀稿件時會視乎作者是否以廣東話的句法(syntax)來寫。」這一句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因為它比其他因應不同記者問法而回答的說法,更準確地揭示究竟團隊是以怎樣的編輯方針去看待「粵語文學」。
要講句法的重要性,就要稍稍講講個人學習和書寫經驗。我係香港人,日常口語係港式粵語;但同時,我多年來經受的語文訓練,無論是中小學基礎語文學習,還是大學的文學講習、寫作訓練,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種「紙面上的中文」。德勒茲在〈甚麼是少數文學?〉內,剖析卡夫卡寫作時面對的語言困境:身為猶大裔的德語作家,他無法用德語寫作,更無法用德語以外的語言寫作;所以,德語僅僅是卡夫卡在寫作時使用的語言,係一種「紙面上的德語」。同樣地,像我這種由細到大學中文,老師講書時,都係聽住港式粵語學中文的學生,「中文」只是一種紙面上的、書寫時候才會使用的語言。直到文首提及跟也斯學寫作時,我才懵懵懂懂地意識到日常使用的語句(句法syntax),怎樣跟我的寫作融合;這意識在往後看着愈來愈多人推動保育港式粵語,變得愈來愈明晰。換句話講,我寫作時很多時候是用港式粵語的句法,配搭所謂的書面語詞彙(但我仍是堅持寫蕃茄而不會寫西紅杮)。這篇文章,基本上也是以這種形式書寫。[5]
但係,港式粵語在香港語境更為複雜的是,上一段提及的「中文」,在香港愈來愈深刻地鑲嵌於備受中國影響的全球化進程時,經歷過另一重轉化。記得我唸小學、中學時,學校在中文堂以外,會另設普通話堂,好似係一星期上一堂左右。但在2018-2019學年,據港語學製作的「中文教學語言資料庫」[6],接近一半香港中小學用普通話教中文。本來中小學生還會分清兩套「中文」——跟口語較接近的「白話」和規範漢語,但這種區分愈來愈模糊,甚至出現不少以港式粵語去講普通話詞彙的混種語言情景。[7] 這轉變背後有政治經濟基礎,跟一套中港融合論述有深刻關係:這是預認香港與中國有深刻經貿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必須延續,所以香港人需要學識普通話,才可以捕捉與中國相關的經濟利益,配合時代發展。影響所及,是香港人耳聞目睹以港式粵語為載體的本土文化,為港式粵語逐漸喪失位置感到異常焦慮。它的重要表徵,在於接受普通話教育的下一代,他們的「中文」跟之前的香港人——像我這種還是學習白話的人——距離愈來愈遠,「中文」變得更像是「紙面上的中文」。
下一代會如何看待他們的混種語言,還是未知之數,但現在推動保育港式粵語的本土論者,大概會有如下想法:本來香港學生學的「中文」,係所謂廣義粵語地區的共同語——「白話」。它雖然在詞彙與香港人的日常口語或多或少有出入,但至少句法相近,甚至是絕大部時間是等同。從劉擇明的說法,推測審稿要求是傾向於文法導向,即係只要符合句法是「廣東話句法」[8] 的要求,就算文字不必然全粵語入文,也是可以接受。而《迴響》團隊的取態,想當然是以保育「句法」的角度去保育港式粵語。即係話,如果用港式粵語入文,但句法不是港式粵語的句法,也不能說是他們定義的「粵語書寫」。舉個例,普通話的形容詞可以放在句子最後(今天人真多);港式粵語則不能(今日真係多人)。如果寫做「今日人真係多」,可能不比「今天真的多人」更符合《迴響》以句法決定粵語書寫的定義,哪怕前者明明用上港式粵語詞彙「係」。再舉個例,普通話的副詞通常放在動詞前(多喝兩杯吧),港式粵語則相反(飲多兩杯啦)。寫做「喝多兩杯吧」,大概比「多飲兩杯啦」更像是《迴響》編輯想看到的粵語書寫。甚至,我大膽地猜想,我這篇文章按理也符合他們定義的「粵語書寫」。以上當然純屬我個人猜想,但我相信至少可以說明,以句法作為一種理解粵語書寫的探索,不一定是一種很原生主義式的寫作教條,它也有可能實現不同的文學語言探索。至少,不一定是全粵語入文,才算是「粵語文學」啦!
或者保險點說,我不確定《迴響》在審稿時會如何設定界線,有幾鬆有幾緊,之但係在這個時勢搞本土事業,如果看到是在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在我而言,用句法去講、去理解「粵語文學」,起碼比起「粵語入文」提升了一個層次——唯有信前線手足判斷,適時做些提點。共勉。
餘論:我記得李智良在某場合提過一個問題:為甚麼英語書寫的香港故事,很多時候不被香港人當成香港文學的一部份?這提問的重要意義,在於提出「香港文學」可以有很多種。《迴響》團隊最惹起爭議的表述,是訪問中談及黃碧雲的寫作,容易使人理解他們高呼粵語文學才是香港文學。若這真的是他們的看法,那會使人非常失望;但如果他們在訪問中是以一個比較差的表述,旨在提出香港文學另一種可能性的話,還是有它的積極意義。即係話,我們可如此理解《迴響》在文學場域實驗的一件事:試圖用句法去審視一種以港式粵語為主體的文學,它可以理解為一種香港文學的形式。據我理解,這是「粵文圈」內的一種共識。
[1] 與文章無關,但與記憶攸關。這科係必修科,全級有至少三十幾四十人上堂。由於是寫作課,所以要小班教學,為此分了好幾組導修。而每一組導修,印象中都係由也斯帶,我的那組甚至有當時仍未成為教授的黃淑嫺、陳智德。無論如何,那時候跟也斯學寫作,建立我好多關於寫作的基本理解。
[2] 黎家怡:〈眾籌搞粵語文學期刊 90後總編:我當係生意咁run〉,《立場新聞》,2020/6/15。
[3] 舉個例,豬伯稱「閱讀本身就係用嚟娛樂,唔需要有咩功利嘅目的。」有人反駁指「娛樂本身就是功利目的。快感就是功利。」問題係,豬伯口說的「功利」是等同於效益主義的「utility」,就像邊沁理解「快感」般是量度「utility」的尺度?會不會,豬伯講的功利,不過是像中小學生做的閱讀報告般需要有「得着」的那種「功利」。
[4] 劉彤茵:〈粵語寫期刊眾籌成功 下月出爐 「廣東話應該有佢嘅文學」〉,《明報》,2020/6/12。
[5] 當年讀中文系另一科「現代漢語」,許子濱教授要求眾人按規範漢語的準則撰寫一篇文章,那時候我用也斯教的「『讀』寫法」去寫,結果成篇文被改到不似人形……但要補充一句,許教授傳授的很多知識一直銘記在心,例如:「的而且確」係錯誤的用法、粵語拼音方案等。
[6] 資料參見:https://sites.google.com/site/hklangstudies/2-SSchoolData。
[7] 參見鄭韶華:〈小學生仲識幾多廣東話? 「我唔知我講普通話定粵語 分唔到」〉,《香港01》,2018/5/18。
[8] 整篇文章特別以「港式粵語」指稱香港人使用的語言,但由於這裏寫的是《迴響》團隊借劉擇明之口提出的說法,所以引錄原話,感覺較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