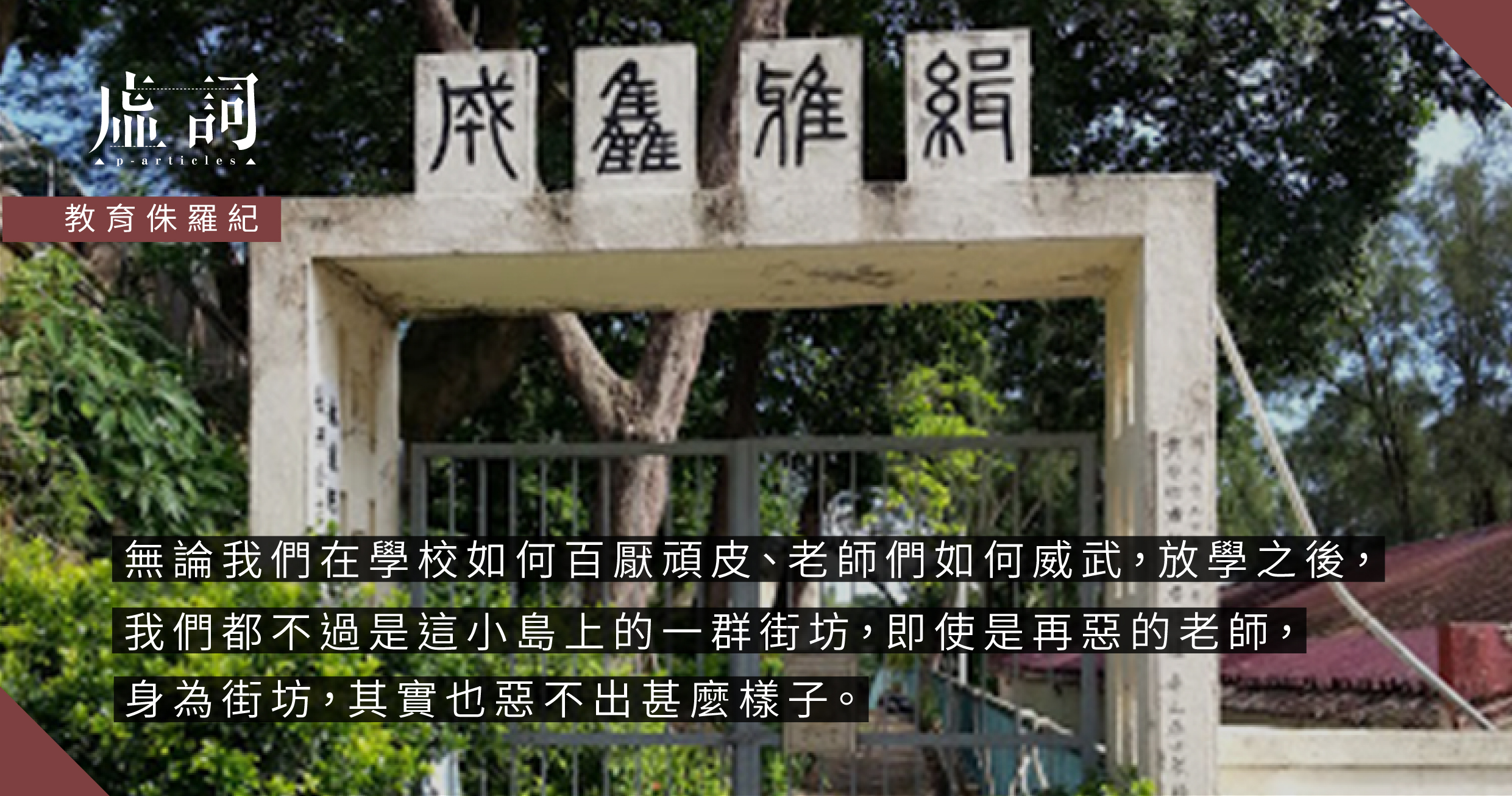小學六年,讀的是小島上的村校。說是村校,當年島上六間小學(國民、聖心、錦江、順德、漁會、公立),其中兩間雖然各有天主教及基督教辦學團體背景,但廣義來說,都算村校。劉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中提到,香港郊野佔全港面積百分之七十五,村校的存在,早就是一種特別而特定的存在——它與鄉村或郊野同生共滅,要是你無法忘記成長的地方或家鄉,你也必然無法忘記學校的樣子。 (閱讀更多)
論思想及個性之難
其他 | by 周保松 | 2019-02-19
我留意到,現在網路媒體很流行一些思想速成節目,聲稱消費者只需付出很少的金錢和時間,就可以輕鬆擁有上下數千年的學問和思想。我明白這類節目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同時在知識普及上起到很多作用。不過,如果有人希望通過這類文化消費,便能輕輕鬆鬆地成為有思想有見地的人,我認為不大可能,甚至適得其反。 (閱讀更多)
【單身動物園】多麗絲・萊辛:結了兩次不算數的婚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 | 2019-02-18
以《金色筆記》名噪一時、於2007年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萊辛,一生結婚兩次,卻極力否認這兩次婚姻的實效性,到底其中經歷了些甚麽? (閱讀更多)
【教育侏羅紀・文理分科】:生化醫理皆可詩
我在中學教的是生物科,課外也兼顧一些文學推廣工作,而認識我的朋友大概知道我會寫作,寫了甚麼就沒多少人理會了。間中有人問起「你不是讀理科的嗎?為甚麼會參與文學活動的呢」,我著實不懂怎樣回應。 (閱讀更多)
【失眠書單】有位醫師,叫博爾赫斯
其他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02-13
聽說失眠症也分幾種類型,有人因為工作壓力、人際關係而失眠;有人因為負面情緒太多而失眠;亦有人因為正面情緒太少而失眠。太深奧的精神醫學理論我也不懂,無論如何,我們對失眠總不會太過陌生,半夜裡的煎熬大概也沒人想經歷多次,但有時就是會陷入泥淖中不能自拔。那時候什麼能拉你一把?如果吃藥太傷,喝熱鮮奶不奏效,數綿羊嫌太單調,不妨看書。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