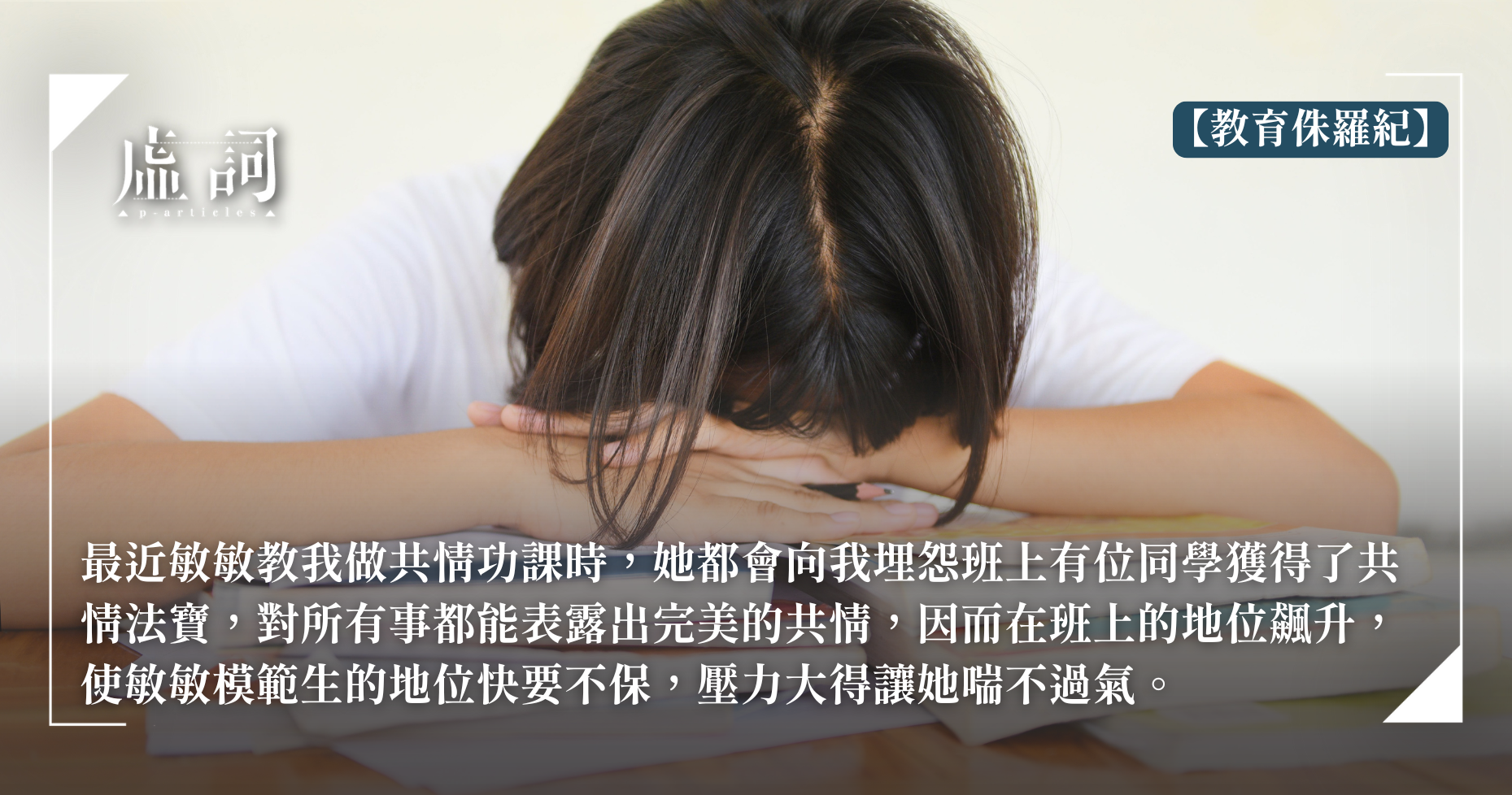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蟻群
教育侏羅紀 | by 佘潁欣 | 2025-05-20
敏敏死了,她刺耳的哭聲終於靜止。
她不是敏敏的摯友嗎?怎麼滿臉不在乎?是不是太痛苦?不。聽說敏敏曾向她求救,只是她置之不理。可憐了我們的共情模範生⋯⋯不要緊,我相信小愛會好好頂替她的。難得我的耳根因敏敏自殺得到三十二秒的解脫,我又被迫將耳機音量調教到最強,隔開新的一堆雜音。敏敏的分貝,九十、八十六、一百、一百三十;新的分貝,四十二、六十、五十六、六十二或三?無論如何,敏敏的音波還是最難受的,猶如我家樓上每週四九時後開始的三十二秒電鑽聲,現在的聲效都只是近似媽媽若隱若現的炒菜聲。
敏敏總是好奇地問,世上竟有人能一直無動於衷,妳是不是有什麼童年創傷?妳是不是神經有缺陷?我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或是我個子高大,難聽到大家的話,與大家情感的距離較遠;又或是家樓上的電鑽聲,使我聽覺變得靈敏,開始討厭擾攘的人聲。她訝然地問,電鑽聲?我從沒聽過,畢竟沒人會想騷擾到人,多數寧願自己用手慢慢砌。聽罷,我想起小時候夢見媽媽被螞蟻咬遍全身,牠們的腹部閃爍淺黃磷光,似乎在用耀眼的軀殼覆蓋媽媽醜陋的紅疹。起床後,媽媽便因嚴重過敏自殺,我驚慌得摟着她一直嚎哭,漸漸便聽見了迴盪、連貫、尖銳的一百三十分貝,它們以三十二秒為一個節拍。夢裏的蟻群一直以整齊的虛線作爬行軌跡,寄居在我的腦袋裏為我撓癢,令我的世界開始分裂。
最近敏敏教我做共情功課時,她都會向我埋怨班上有位同學,我忘了叫什麼名字,獲得了共情法寶,對所有事都能表露出完美的共情,因而在班上的地位飆升,使敏敏模範生的地位快要不保,壓力大得讓她喘不過氣。我懊惱地問,模範生要來教我這種共情白痴,又要承擔並安慰同學的負面情緒,還要幫老師管理共情秩序,有什麼好?敏敏笑咪咪地回,以模範生的身份畢業能獲歷屆模範生親手寫的《共情秘笈》,二十四小時隨時能諮詢他們的共情建議,學懂便能共情到所有人。所有人都將會喜歡我優秀的共情能力,我一畢業就能靠共情得來的關係網求職,能共情他人便永不再會感到孤獨,家人會以我的共情為榮,還能因共情而受不同人的喜愛和讚賞,這可是整個社會所渴求的事!我不理解,那無非是缺愛的人想要博取注意,她更應解決自己的安全感問題,我不懂敏敏的焦慮,但她又不肯問法寶的來源,吞吞吐吐地指出那是淺黃的特殊眼藥水,是一種稀有的國際禁藥。
既然是國際禁藥,又有誰能買?賄賂?偷竊?自己研發?
雪兒,妳在想什麼?嘶——這段新的音頻靠太近了。不開心就儘管哭出來吧!她很煩,我不喜歡,她的淺黃髮色和淺黃指甲也太刺眼。我相信妳一定有努力拯救過敏敏,妳看妳為了她失眠而生的眼袋!課室炎熱,同學過分熱情,空調故意被閒置出淺黃裂痕,隙縫中偶爾會湧現出一群烏黑的螞蟻來偷聽講課。淺黃的百葉簾讓陽光變成刺眼的金光,淺黃桌椅、地板、牆壁、壁報都讓我難以睜眼,同學校服的淺黃亦在弱化我的視力,令我左眼澀痛,可我不會滴眼藥水。我皺眉抬眼望向她說,我沒有,我只是因為熬夜看書,並告訴她我很忙,請不要再打擾我。同學們的臉扭曲成不同幾何圖形,而她勉強地將臉保持一直線為我辯解,妳一定是有苦衷的吧?我不理解,我沒請律師,她為什麼要幫我說話?我的眼球又開始痕癢,我焦躁地揉搓眼睛說,我沒有,只是她每次到達一百三十分貝的哭聲都會使我耳蝸絨毛斷裂三根,使我顳葉深處傳來輕微的窸窣聲,像螞蟻用前肢刮擦耳骨。我想她儘快閉嘴或直接離開,若然這便是苦衷的話。小愛妳不要管她啦!小愛太善良了,小愛果然是我們的天使。她難以置信地拿出裙袋裏的《共情寶典》翻閲,同學們羨慕地包圍她,爭先恐後地窺看價值連城的天書,竊竊私語道,小愛買到絕版書好厲害,難怪那麼懂共情!這本書很貴,對呀,是我兼職一輩子也賺不來的錢,小愛妳是原價買的嗎?可以向妳買電子版或借來列印嗎?她得戚地揚起嘴角笑說,不,我明白大家好學,可我們要為原作版權著想,我有空一定會和大家分享的!小愛小愛小愛,熱烈鼓掌,熱烈歡呼,小愛小愛小愛,熱烈鼓掌,熱烈歡呼。
她大概是馬戲團的猴子,不知哪來的表演慾,但拜托不要煩我,不要靠近我,這裏不是妳的舞台。她終於把像石頭般厚的「天書」合上回覆,我相信雪兒只是太愛這個世界,以至無法專注於單一生命,我們一起救贖她吧!當她說出「救贖」二字,音頻終於超越了敏敏的一百三十分貝,筆直地撞入我的耳膜。雪兒,妳的臉書帳號是什麼?我想加妳當朋友聊天。我沒有臉書,我不需要朋友,亦不想和人聊天。那妳怎樣得知別人的心情?我不想知道。電話號碼總該有吧?我不想給妳,這是我的私隱。
我不解為何全班都已將她當補選模範生,她還要死纏爛打來博取我的支持,不斷嘗試接近我。有敏敏這麼麻煩的模範生來糾纏我已夠煎熬,儘管她的共情能力似乎沒有敏敏要死要活般洶湧,更像一種完美無瑕的演出。或許她害怕我會拆穿她精湛的演技吧?全班彷彿在竊笑不入流的我,或是嘲笑我狠狠拒絕小愛讓她蒙羞。一層陰沉的迷霧將她重重包圍,她低頭沉默,我看不見她真實的表情,無法猜度她的心理狀態。當我欲離開課室時,她立刻噙淚拉着我說,不要緊,我會陪妳走出傷痛,誠實面對自己心底的疤痕吧!我心想難道這是什麼復仇伎倆?她到底有多喜歡演戲?她的眼淚可真廉價。
甚麼顏色最先吸引眼球? 李雪兒。黃;大腦的哪部分處理聽力和語言?李雪兒。顳葉;地球上有記錄以來最冷的溫度是? 李雪兒。攝氏負八十九點二度;完美,請坐下。我只有在科學課會獲得掌聲和友善的眼神,我不解為何每次回答基礎問題時,全班都會以驚訝的表情仰望我,但這些我初小常識課便學會了。下課鐘聲響起,老師將我喊停質問,李雪兒,妳為何不在敏敏最無助時伸出妳的援手?什麼老師,我忘記他的姓氏了,我本以為他把我留下是想表揚我。他的嘴巴緊緊地捏成橫線,猶如整齊的螞蟻在操場排隊。我隱隱聽見螞蟻啃食腐木的雜音,從左腦緩慢向右腦遷徙。何時算是她最無助的時候?她每秒都向我宣洩無助,我哪分得清哪次才是「最」?老師凌厲地追問我,為何她跳樓那天曾找過妳,妳卻放任她輕生?跳樓那天是哪一天?是她哭訴同學們嫌棄她訴苦時焦躁極端的一面,不夠顧及他人感受,令一直依賴她的同學開始疏遠和排斥她的一天?還是她因壓力遲交作業,使老師認為她是自私的學生而冷落並重新審視她,將注意力轉至她的假想敵身上的一天?或是小息時段圍繞她的人群開始變得依稀,只能開始騷擾存在感極低的我的一天?又好像是她意識到自己變成了名不符實的模範生的一天。
大概是昨天或前天?
那天,我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被她停截,她又向我重複那擾人的一百三十分貝,不,那天的聲量更強化至一百三十五分貝。我受夠了,我做了整個校園生活最正確的決定,便是無視她逕自前行,我相信我很快就能找到那件法寶,趕快讓她住口。我在圖書館尋找關於那法寶的資訊,遍尋不獲,直至闖到禁書區,發覺角落的監控頭被毀壞。天助我也,無法無天。禁書區入口沒有門禁或保安,只有告示張貼於牆壁:「有同理心的學生請乜內進,以免造成學校困擾。」我無視告誡步入區內,在一排排燈光幽暗的書櫃間搜索,找到敏敏所說的其中一本《共情秘笈》,由校友張慧撰寫。裏頭提及那淺黃眼藥水並非真的眼藥水,而是以特殊化學物料混合而成的毒藥,能抽空人腦裏多餘的情緒,令人不露半點瑕疵地演繹上帝視角的共情。藥物卻被批判違背共情原意而停產,現在只能在黑市以高價購買。正當我翻到藥物資訊時,那頁已被撕毀,只能依稀看到「催促」二字。急功近利,自取其亡。一聲清脆巨響赫然離我左耳的十米墜地,令我的神經短路,擦出微弱的火花。我的左顳葉傳來硬殼破開的脆響,蟻群從我的耳道湧入,用腹部摩擦出一百三十分貝的共振,將慘叫聲轉譯成工整的摩斯密碼——
吃.掉.你.吃.掉.你
滋吱吱滋,那三十二秒的寧靜,滋吱滋,突然像眼藥水滋潤了我長久乾涸的眼球,滋吱吱,我想起纏繞媽媽皮膚的蟻群在狡猾地低笑,滋吱,將敏敏的屍體當作蜜糖搬進我思緒的角落,吱,成為媽媽屍骨的淺黃補充劑,滋,我想起她小小的身子被蟻群貪婪地鯨吞。後來,我便如暴露身份的臥底被教訓和隔絕,桌子常常出現用圓珠筆或鎅刀烙下的「殺人犯」。「殺」字的「木」有時少了頂帽子,「犯」字的「㔾」有時偷偷封口。這些都讓我心理不平衡,不禁自行修補錯字,或向創作者本人檢舉錯處。自此,他們似乎更懂我心了——關於我的議論雖更激進,卻離我更遠。我的作業被撕碎,黝黑的書包還額外附上繽紛的塗鴉,偶爾還貼心為我製造紅嫩而熾熱的胭脂。不知名的老師或同學都憤然質問我是否沒回應敏敏的求救,儘管我壓根未弄懂他們對「回應」和「求救」的定義,我仍敷衍地點頭認罪,因為我只想儘快將僅餘的人聲靜音。
趁環境變得清淨,我再次到圖書館尋書,享受冰涼的空調,學生證卻不知好歹地失靈,多次令門鎖亮起紅燈。我嘗試用蠻力拉扯並拍打玻璃門,窺看空蕩蕩的黑色書櫃間會否憑空出現替我開門的人,在無人的服務台偵查館長的聯絡電話。一絲罕有的冷風吹過,我張望陰暗寂靜的走廊,捕捉了一位不認識的老師。她個子矮小,閃閃縮縮,頂著帶有明顯M字髮線的烏黑菇頭,帶淺黃長方框眼鏡,全身都穿淺黃蕾絲套裝,像藏匿了滿腹心事般回答,我不清楚,不如妳去尋求其他同學的幫助吧?四周沒有任何同學的身影,畢竟他們只能接通有血肉之軀的情感,未能接通書裏其他澎湃的情感,他們大抵喜歡熾熱的螞蟻,壓根不需圖書館裏的冷空氣。一輪折騰無果,剛才那位老師從她的辦公室裏探頭,被我敏捷地發現並與她眼神對上。她靦腆地喚我過去說,我剛向校務處詢問,大概了解到妳的情況,妳先進房回答我一些問題,再看看情況有沒有轉機。
我瞄到她房門掛著「審查室」的牌子,裏頭全是淺黃牆壁、淺黃桌椅、淺黃地板、淺黃擺設,有沒有一種可能其實她喜歡黑色,她內心的底色是黑色?她越故意讓和煦的淺黃與自己掛鉤,代表她越努力遮蓋自己最真實的黑暗。我大概預判到十秒後將會被重複提問,妳能否意識到敏敏的不快、有沒有想為她流淚的時刻、有沒有想幫助她的衝動、她死後有沒罪疚感等等,而我會目睹一個個血紅交叉將我的名字在紙上封印,因我會一律誠實回覆沒有,避免被深入研究。預判應驗,老師淚流滿臉地引導我說句關心她的話,我留意她的髮線是由蟻群縫出,細看會發現微微蠕動的黑影。我沉默半秒回答,淺黃看起來代表明亮的希望,但事實是它又醜又難搭配,老師妳大可喜歡黑色。她怒瞪我指責,老師整房整身都是淺黃,妳稍為動腦子也能猜到我是喜歡淺黃的吧?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淡淡地重新視察環境說,越喜歡的就越不需要以這種方式強調,妳最貼身的髮色、銀包、手機底色都是黑色的,老師只是想隱藏自己的陰暗面吧?其實妳有沒有真正拋開虛假的面具,選擇不聽虛假的聲音,追問自己為什麼需要共情?心底最渴望的又是什麼?或許你們都不是真正共情,只是在用他人的痛苦餵養自己道德優越感。會否有一種可能共情是包裝精美的情緒和道德綁架,它只不過是一種不比冷漠更好,更深層的自私?她凌厲地收起眼淚怒斥我,閉嘴,妳竟然沒有人類最寶貴的情感,無法設身處地去為他人流淚,多可憐的孩子呀!吱吱吱吱,電鑽聲又開始在我思緒裏作響,吱吱吱,我不懂為什麼一定要共情,吱吱,我只是認為她的哭聲是久違的噪音,吱——
老師說只要我在一星期內閱讀指定書目,寫一篇三千字的悔過書,便能解除圖書館門禁。我拿着點名紙到懺悔室,裏頭空氣極不流通,還有一陣刺鼻的辛辣味,逼使我的眼睛通紅,幾乎要流眼淚。難道這是懺悔室的特效?哭着懺悔會比較真誠?或只是滿足懲罰者的特殊癖好?我不知道。三本指定書目整齊疊在桌面,包括《共情的重要》、《我們的共情世界》、《踏上共情之路》,分別是紅黃綠硬皮書封,如同一盞安靜有禮的交通燈。我翻開書頁,皺眉分析不合理得使我焦躁的句子:若我們為他人分擔悲傷,悲傷就能減半。不,分擔悲傷等於製造多一份悲傷;當他人悲傷時,可以陪在他身旁聆聽。什麼?他不開心關我什麼事;先設身處地安慰他人,再講道理。錯,人要自己調節,只要問題解決,情緒就會消失。我不耐煩地閱讀了數千頁,越讀越覺得論點都是荒謬的,我想起敏敏的一百三十分貝。假如共情如此奏效,為何擁有龐大共情能力的她仍然絕望?其實共情只不過是一場巨大的演藝競賽吧?我不自覺拿起紅筆,標記完所有邏輯謬誤、二元分立、雙重標準的位置,還在空白處列出我的辯證過程,半小時便寫完三千字題為〈共情只是一種集體模仿行為〉的論文交給老師。
老師無聲垂泣,眼淚暈染我論文的墨水筆跡,我勸她儘快停止,以防弄髒我的論文,我想趕快到圖書館找資料。她微微搖頭呢喃,沒救了沒救了,我不屑地企圖搶過她攥緊的論文。她卻寧死不放,猛力搖頭,跺腳大喊,為什麼為什麼,人最基本的情感為什麼你沒有?到底哪兒出錯了?你就不可以關心一下人嗎?社會敗類,自私精!我瞅到她桌上的名牌寫著張彗,牆上掛起「共情模範生畢業證書」後問,老師是害怕辛苦偽裝回來的憑證消失嗎?妳是否已分不清自己真正喜歡和討厭甚麼?是否已忘記自己是怎樣的人?既然本來不是渴望或擅長共情,為什麼還要苦苦掙扎?人活成這樣不會感到可悲嗎?這時,她的眼球突然爬出三隻螞蟻,沿著淚痕鑽進論文皺摺。不不不,妳閉嘴,我很幸福,所有人都喜歡我!她一邊顫抖,一邊後退,於是我逼近追問,你是不是用了淺黃眼藥水?她瞠目問,為什麼妳會知道這款眼藥水?我像連續發炮地質問,若我的猜測是正確的,以模範生身份畢業意味妳要背叛最真實的內心,擁抱面具渡過一生作為條件交換,是嗎?妳閉嘴妳閉嘴妳不懂妳不懂。沒錯,我不懂為什麼不願意也要強迫自己共情,但抱歉,你們也沒有做到真正的共情,你們只想所有人認同共情。她緊掩雙耳囁嚅,不不不,對不起,老師只是共情到妳無法共情他人的痛苦而難過,為妳感到可惜。我搖頭否認揣測說,我很自在,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希望其他人有煩惱也不要騷擾到我。她使勁抓着我的雙臂說,不要怕,妳是逃避型人格而已,老師帶妳感受共情的幸福。我嫌棄地推開她,這時她的尖叫終於到達一百三十分貝,戳痛我淺薄的耳膜,剛剛對她稍微閃現的憐憫便迅速消逝。反之,隱蔽的蜜糖罐彷彿在我思緒某處傾瀉,惹來一群螞蟻圍着我的神經兜圈,輕盈地舔食那裏誘人的糖漿——
翌日清晨,我離學校還剩步行距離三分鐘的斜路,卻發現學校外牆連接水管的角落有一窩螞蟻在苦苦掙扎。我猜是懶惰的同學自作聰明的傑作,明明過一條馬路便有垃圾箱,難道他們擔心螞蟻沒有糧食?難道這就是他們對螞蟻的共情?不動腦的共情是甜蜜的毒藥,人會對自己善良的面貌上癮,從而忘記原有問題的關鍵。我檢查手錶,現在不上斜便會遲到,我回望螞蟻虛弱的手腳,窩裏散發着熟悉的糖漿酸味,我的目光被黏稠的漿液綁緊,與思緒間盤旋的螞蟻連繫。吧唧吧唧,吧唧吧唧,牠們相約一起啃吃我的神經,用餐時間為三十二秒,吧唧吧唧。刺耳的一百三十分貝又開始重複,妳在幹什麼?遲到了欸。小愛頭髮蓬鬆,眼皮厚重,聲音沙啞,應是睡過頭。
鐘聲響起,我們來不及跑了,我緩緩站起來與她並肩而行。她走到課室前駐足,從書包裏翻出眼藥水,底部印有「共情催促劑/精神迷幻毒素」。我疑惑地凝望她淺黃的淚水滑落,散發濃郁的糖漿酸味,與螞蟻窩裏的氣息完全吻合。當她眨眼時,下眼還會短暫浮現螞蟻列隊的投影,那群整齊的六足生物正從敏敏屍體裏搬運澎湃的情感荷爾蒙。我的眼球也開始有點乾澀,或許最近空氣太混濁。甫到課室,老師凌厲地瞪着我倆,質問我們遲到的因由。她悽楚地拭去臉上虛假的淚珠,壓着哭嗓辯解,途中遇到受傷的婆婆跌倒,她膝蓋的傷綻成紅光,像在向我發求救訊號,我不忍不理,跑到便利店買急救包為她作初步消毒。老師滿意地點頭稱讚她的「美德」,全班又開始熱烈附和:婆婆遇到小愛真幸運,小愛為了幫人而不惜遲到,小愛可真是聖母轉世呀。
天花板突然落下微細的黑色碎屑,我伸手接住發現是燒焦的螞蟻屍體,牠的觸鬚仍黏著那些淺黃眼藥水的結晶。老師隨即嚴肅地怒視我質問理由,我喉頭猶如被堵塞的壞零件,慢條斯理地謊稱,看風景看得太入神,卻忘了看時間。老師憤然斥罵我的態度不認真,我辯解說小愛分明是賴床才遲到,還在門口滴眼藥水才進來哭。她口齒不清地責怪我,妳連偽裝共情都不屑,這才是真正的邪惡!
嘩啦嘩啦嘩啦,小愛的哭聲掀開我的頭蓋骨,一百三十萬隻螞蟻正用顎部拆解顳葉的溝回,組成一條直通耳膜的虛線。我腦裏的蜜糖罐已經完全跌碎,螞群貪婪地吸吮超標的糖分,不夠數秒便清空了我思緒裏僅餘的甜味,吃飽便滿足地從我的腦中解散。嘩啦嘩啦,那尖銳的一百三十分貝反覆鑽進我的神經,嘩啦——
我的顳葉終於被牠們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