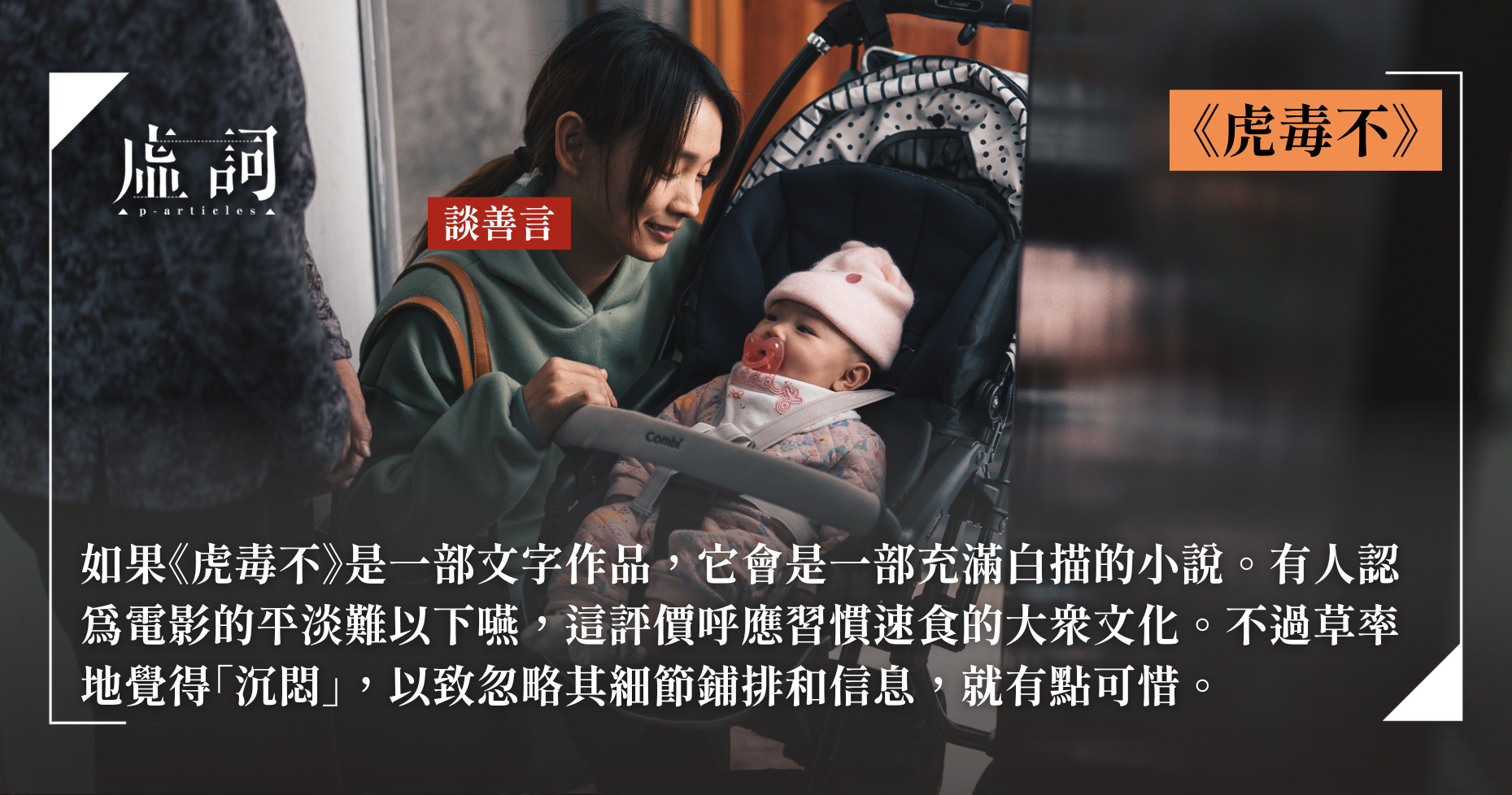當母職成為現代禮教,誰謀殺了楊淑貞?——《虎毒不》
影評 | by 筠 | 2025-05-20
編按:標題由編輯部擬定。
晨早的陽光曬在嬰兒床上,掛床玩具上,曬在孩子的臉上。母親手抱著孩子坐在陽台,看著孩子的臉,一句一句的輕聲說著話。
如果《虎毒不》是一部文字作品,它會是一部充滿白描的小說。有觀眾認為電影的平淡難以下嚥,這評價呼應習慣速食的大眾文化,並非未能預料。不過草率地覺得「沉悶」,以致忽略其細節鋪排和信息,就有點可惜。本文嘗試就筆者所見,進入主角楊淑貞的處境,去明白是什麼導致悲劇發生,結局是否合理。
電影頭二十分鐘,一個普通家庭:愛錫寶寶的媽媽,同住的奶奶,主力工作間中幫忙的老公,孩子百日慶祝道賀的家人。這家庭,貌似典型,可能許多人看來正常得很。
細看,在不經意的話語互動裏有權責分工:太太生病時丈夫說「我幫你頂幾日」,彷彿照顧孩子從不是他的工作;奶奶幫忙照顧孩子又暗示覺得麻煩,後來終於明講媽媽的責任就是要主力帶孩子,假手於人就是卸責。家庭角色裏暗藏牢固而不容挑戰的「理所當然」。
在家庭的權責框架裏,淑貞逃出的辦法是有自己的外間工作。有個社會學的入門概念叫Second Shift(第二輪班):傳統的性別定型下,假如夫妻都有工作,女性下班後打理家務、育兒的責任通常仍比男性多,猶如第二個輪班。不過淑貞沒有埋怨這些,嘗試兼顧兩者。在丟失餅店工作之前,丈夫和奶奶對他還算遷就而容忍。而淑貞在反駁奶奶時也顯得有膽量。勞動身份和帶來的經濟貢獻,多少有提升淑貞的自信和家中地位,使她話語比較有份量。
內化的完美母職
有些人批評淑貞不是完全沒有想法的人,也夠膽違抗奶奶,為什麼到後來卻不夠膽為自己做選擇?我想這關係到(1)她的經濟資本、(2)她對自己母職的理解,及(3)她的精神狀況。淑貞也並非沒有嘗試抗命,她站在地產舖門前向經紀查問的背影,瘦削的背影想著出走,其實相當激進。不過窮與婦女的身分多元交織。若她財力有餘,她心頭也許沒捏得那麼緊,甚至可以經濟力量與老公討價還價。但她在五千元以上月租面前卻步了。
除此以外,「楊淑貞之女」手帶一幕,帶出這個母職不單是家人加諸於淑貞身上的,也是一個內化的責任。即或母性對於媽媽有其身體的、來自荷爾蒙的因素,現代的育兒畢竟充滿人為干預和期望(寶寶生長指標、照顧指標、學習指標……)。淑貞看到女兒的手帶,我猜浮現在她腦海的,更多是她自己與別人期望中「稱職媽媽」的落差。淑貞曾說,她生孩子之後,原本的自己好像一點一點消失。在手帶那一幕之前,她內心的掙扎都是以矛盾的形式進行着。從淑貞和淑貞母親的對話裏可知她想守著心中一大片的自我,不單以孩子的幸福為自己的幸福,她很知道本體的幸福是獨立的,但手帶那一幕,當她看自己不及別的「稱職」母親看似專注甘心地育兒,又看著自身無力獨立,她的自我徹底崩塌。她似乎從那天起決意為着寶寶把自己埋葬掉。這個也讓她與自己的內心越來越遠,精神越見萎靡。
而這種斷崖式的決定,和她身邊人對他原本價值的否定有很大關係。縱觀他生命中對他重要的人:老公、母親、情感上疏離但同住的奶奶,沒有人對他追尋自己的方向表達肯定,加上對於孩子的愧疚,淑貞似乎總是覺得自己沒有把最好的給孩子,這種內疚使她更忽略自身追求和想望,進一步邁向自我毁滅。
沒有明說的抑鬱
電影似乎不想明講淑貞應該是患有抑鬱症,雖然這突出外在的體制如何壓制人,但可能部份觀眾不明白淑貞的心理發展,以致有說「出戲」。淑貞把頭髮剪短暗示她對「稱職母親/丈夫/新抱」要求的順從,她自此卻踏進抑鬱之門。淑貞的自我一點一點消去,加上失去反抗的意識,憤怒內化,變成對自己的指責,這些都是容易構成抑鬱症的一些關鍵思維。片段式的剪接拼湊而成的是一幅抑鬱症的圖畫,可是身邊人都不知道。
並非人人了解,患抑鬱症的人可能做不了平常人覺得輕而易舉的決定。走佬啊,對抗老公啊,話返奶奶啊,搵人幫手啊……當你被抑鬱籠罩着可能你想到的就是怪自己,怪這個世界。尋常如淑貞的家人,也完全沒有為意到她在抑鬱潭中下沉。
海灘的假日看似充滿浪漫的想像,男人牽着女人在沙灘漫步,但卻是壓斷淑貞的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你想……?
阿偉這個角色有性別定型之外之內的部分,儘管說話語氣似是溫柔,卻不是那麼善解人意,例如口裡應承但沒有把修理奶泵一事放在心上:「我養你、打本畀你做老闆娘 」話語裏沒什麼掩飾的父權(而不自覺)。當他在家中正式擔當了經濟支柱的角色,說話的語氣漸漸都不同了,甚至能不問意願地期望淑貞生育。他其實對於淑貞的意願和需求沒有興趣,他懂得買自己愛吃的湯圓給太太,但對太太最需要的,分擔育兒責任不屑一顧。他只知道自己覺得什麼是對她最好,而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浪漫,經常在「男人都係咁架啦,老公係咁樣……」諸如此類的定型下被接受。可是對於內心孤立無援而自我崩潰的淑貞,丈夫的徹底不理解、強加的期望,再來似是無盡的育兒生活,甜言與冀盼就是溫柔的殺手,粗暴扼殺了最後一道似有還無的希望。
在這個家庭,彷彿沒有什麼預感,悲劇悄然來臨。
假如我們置身其中,我們又能否覺察這其中的壓制與剝削;關係中的我們是否肯定自己沒有把責任強加於伴侶之身、兒女之上。可不可以在說「我幫你」(我養你)之前,先問一問,其實你想我點樣幫你?
電影帶出的共感
坊間對電影評價兩極,批評意見有說戲中狀況不符合現代。誠然,於香港20世紀中至後期作為母親的女性,所承擔的母職重擔應該會比21世紀的媽媽沉重,電影裏的狀況會更普遍。但只能夠說,因着現代家庭造成背景的複雜,戲中的狀況在此時此地絕非不會發生。電影的其中一個叩問,在於殺嬰慘劇的起因。除了表層的個人情緒問題,母親身處的景況、對母職的窒息理解、失效的支援網絡,難道不是殺嬰的共犯嗎?假如有觀眾認為現代的母親不會承受淑貞的處境,他/她着實應該好好關心一下身邊為母親的人。即使你能做到獨立自主,不代表別人的處境可以啊。
最後想淺論一下演技和電影的社會性。談善言的演技着實令人驚豔的,她把媽媽的角色演繹得自然而具細微的情緒變化,角色性情與她過往的角色有大反差,令人驚喜。記得在一些導演訪問裏,導演說儘管談並沒有養育孩子的經驗,但是她演繹角色情緒,例如哭泣的處理,能演到的層次和深度都很廣很深 。一些微表情的處理、憂傷的不同程度,獨白的拿捏,她都發揮得恰到好處。拿下電影評論學會的最佳女演員大獎,我覺得是實至名歸的,甚至值得再下一城。十分期待阿談下一部電影的演出。
劇本埋下了很多符號性的電影語言,如一一細說或者要另文詳述了。頗圓滿的前後呼應,角色的小行動、對白的遣詞用字帶出的背後意思(特別是家人對淑貞的用語),這些處理都很細緻。唯獨作為一部敘事電影,這套電影的確沒有太「扭橋」,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浸淫在速食文化的觀眾多數看不慣。很寫實,但略未能引起追看的興趣,以至於訊息的傳遞打了折扣。從電影背後的意念、善良的動機和社會意義來說,我會毫不猶豫推薦這齣戲。至於電影本身的敘事和劇情來說呢,也許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比起原先劇本中的法庭結尾,我可能更喜歡現在這個與第一幕陽台互相呼應的版本。淑貞那一句「媽媽真係好期待見到你呀」,純淨的愛與盼,希望隕落之殘忍,在電影院裏迴盪,心頭顫動。誰之錯?誰讓母子夭折——虎毒不吃兒,吃人的禮教,現在就成了完美「母職」那種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