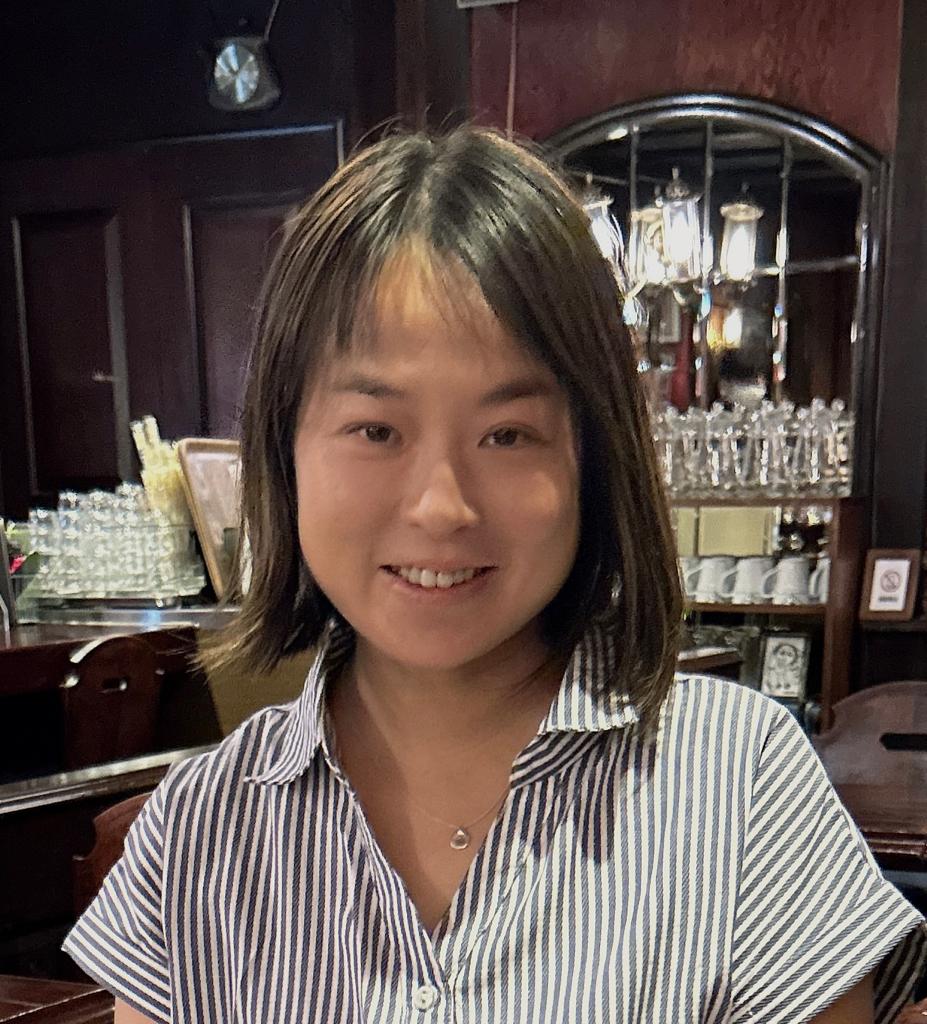夢裏不知身是客——也談《酒徒》的意識流
在公路上飛馳的小巴,傳來那一首歌,把你拋進哪年哪月?偶然,瞥見坐在身邊的男人,不知為什麼嘴角牽動了一下,他在看我嗎?從上司的房間走出來,禁不住內心的騷動。這時候,誰的內心在上演什麼劇場?讀意識流小說,就像一個偷窺者,在冷漠又看似互不相干的城市,讓我只愛陌生人。
很多人覺得,到今天還講意識流小說,其實也很落後了,畢竟吳爾芙的Mrs. Dalloway已經老態龍鍾。也有很多人,一聽到意識流小說,就想起一連串喃喃自語——得個悶字。不過,因為《酒徒》這本號稱「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所以很多人還是唯唯諾諾的找來看了。
第一次學習「意識流小說」,覺得怎會有這樣「便宜」的寫作手法?實在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不就是直接模仿腦海裏隨時彈出來的詞彙和句子,然後把他們拼湊在一起嗎?(真相絕非如此,意識流是內心獨白〔interior monologue〕,再加上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主角對外物心有所感、自言自語時,這些獨白式的描述,會以非常隨意的方式不斷跳躍。)意識流書寫模仿意識,意識是一條河流,浮在小溪上的東西,不捨晝夜。
後來,我當然也沒有完全看完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除了還記得那個甜美的貝殼蛋糕,作為一個開啓記憶的鎖匙。看意識流小說就是看一種感覺吧,有時候你不會記得細節。看流行小說你會記得驚世駭俗的情節。但在看意識流作品的時候,卻肯定不會記得每一個字,變成在記憶中游泳的感覺,讓你浸淫在小說家創造的氣氛裡,像電影《玩謝麥高維治》一樣進入了敘事者的腦袋。
香港作家崑南的《地的門》,創作於1961年,(比《酒徒》還早一年)更是自資出版的!這本像傳說一樣的小說寫一個剛畢業的香港青年,面對愛情、民族等現實與觀念的衝擊,也是在妓女身上尋找愛情,既如念經又如念咒的大段大段《山海經》、《淮南子》引文,讀來其實比《酒徒》更顯狂狷。青澀少年讀之是會面紅的,又有人會覺得九唔搭八。
白先勇《遊園驚夢》的意識流經過精心的平行設計(歐陽子語),小說中對於錢夫人過去與鄭參謀曖曖昧昧的部分,以錢夫人的意識流動來寫。不單純是插敘,遊園驚夢就是錢夫人最歡快最纏綿的回憶。援引一節︰
那團紅火焰又熊熊的冒了起來了,燒得那兩道飛揚的眉毛,發出了青濕的汗光。兩張醉紅的臉又漸漸地靠攏在一處,一齊咧著白牙,笑了起來。紫簫上那幾根玉管子似的手指,上下飛躍著。那襲嫋娜的身影兒,在那檔雪青的雲母屏風上,隨著燈光,仿仿佛佛地搖曳起來。洞簫聲愈來愈低沉,愈來愈淒咽,好像把杜麗娘滿腔的怨情都吹了出來似的。杜麗娘快要入夢了,柳夢梅也該上場了。…然而他卻偏捧著酒杯過來叫道:夫人。他那雙烏光水滑的馬靴啪噠一聲靠在一處,一雙白銅馬刺紮得人的眼睛都發痛了。他喝得眼皮泛了桃花,還要那麼叫道:夫人,我來扶你上馬,夫人,他說道,他的馬褲把兩條修長的腿子翻得滾圓,夾在馬肚子上,像一雙鉗子。他的馬是白的
中學看時完全不明白,後來讀完《牡丹亭》,再讀懂那段象徵的白馬,才驚艷於白先勇文字的綺媚詭譎,真是流麗。
讀劉以鬯先生《酒徒》中的意識流,便有一種刺激感,模仿腦海裏面思想的速度,行雲流水把要說的內心獨白、潛意識或夢境寫出來。
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推開窗,雨滴在窗外的樹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腳步,從葉瓣上滑落。扭開收音機,忽然傳來上帝的聲音。我知道我應該出去走走了。然後是一個穿著白衣的侍者端酒來,我看到一對亮晶晶的眸子。(這是四毫小說的好題材,我想。最好將她寫成黃飛鴻的情婦,在皇后道的摩天大樓上施個「倒捲簾」,偷看女秘書坐在黃飛鴻的大腿上。)思想又在煙圈裡捉迷藏。煙圈隨風而逝。屋角的空間,放著一瓶憂鬱和一方塊空氣。兩杯白蘭地中間,開始了藕絲的纏。時間是永遠不會疲憊的,長針追求短針於無望中。幸福猶如流浪者,徘徊於方程式「等號」後邊。
這是小說的開首,生銹的感情可以指敘事者的回憶,「思想在煙圈裏捉迷藏」,然後跳躍到窗外的雨。一個侍者端酒來,敘事者從亮晶晶的酒杯中,可能想到情人 ?但思緒又立刻跳到準備要寫的四毫子小說; 我們只知道作者在餐廳,但是究竟是誰扭開收音機呢?這段文字包括清醒的意識,更包括無意識、夢幻意識和語言前意識。在意識流之中也可以說是一個萬物有情的世界,雨和酒杯都會引起意識的轉向,空間是放著一瓶抑鬱的,讀者跟著作者轉換視角,讀來不知不覺投入在作者的內心活動之中,行雲流水,歡快無比。
小說中亦常見用意識流的方法,把刻意遺忘卻深刻的記憶,在日常秩序中蹦折出來。那是作者無意識的部分,在身處當下霓虹璀璨、歌舞昇平的香港,就像作者與女人糾纏,朝生暮死,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墮落。現實是只爭朝夕或朝不保夕的,舉杯消愁,是在沒有防空洞的地方找尋虛無的山腳避難。
小說中總是把酒醉的部分以意識流的方式呈現出來;夢囈就如炸脆麻花一樣,與酒、賣文生活、妓女愛情參差交纏,真箇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赤裸的直覺、情感、夢,有時更有力量。直面內心,越刮越深,於是作為偷窺者竟不知不覺的也旋入敘事者的意識流之中,突破了時空的藩籬,在天真、執著、天人交戰的獨白中飛翔,讀來不覺手心冒汗,甚或如癡如醉。
小說的後段作者失去了寫黃色小說或武俠小說的地盤,他忠誠的文學朋友麥荷門教他失望了,他所愛或不愛的女人都已離他而去。身上又再次沒有錢,沉醉在酒精中不能自拔,於是小說出現了長達三頁的獨白,徘徊在酒醉和清醒之間,十分精彩 ︰
一切靜止的東西都有合理的安排。唯人類的行為經常不合邏輯。情感與升降機終究有不同,當他下降時一樣如物體般,具有變速。我又去喝酒。我遇見一個醉漢,竟也說我偷了他的眼睛。我覺得他很可笑,卻又不能對自己毫無憐憫。他是一面鏡子,我想當我喝醉時我也會索取別人的眼睛嗎?群眾的臉群中的笑容一切都在模糊中淡出了……
很難想像《酒徒》不用意識流的形式呈現。劉先生把文學這頭悲哀的獸好好地藏在酒徒的軀殼之中。剛剛在陳子謙的面書讀到,學者鄭樹森認為《酒徒》並不算是意識流。我覺得廣義來說,酒徒也實在有意識流小說的特質。清醒時我們自以為能夠分得開夢與真實,其實真實就是夢裏不知身是客。倒不如看酒徒的自白,陪著他輕呼著煙圈,在文學的泥沼中不能自拔。
2018年6月13日
劉以鬯紀念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