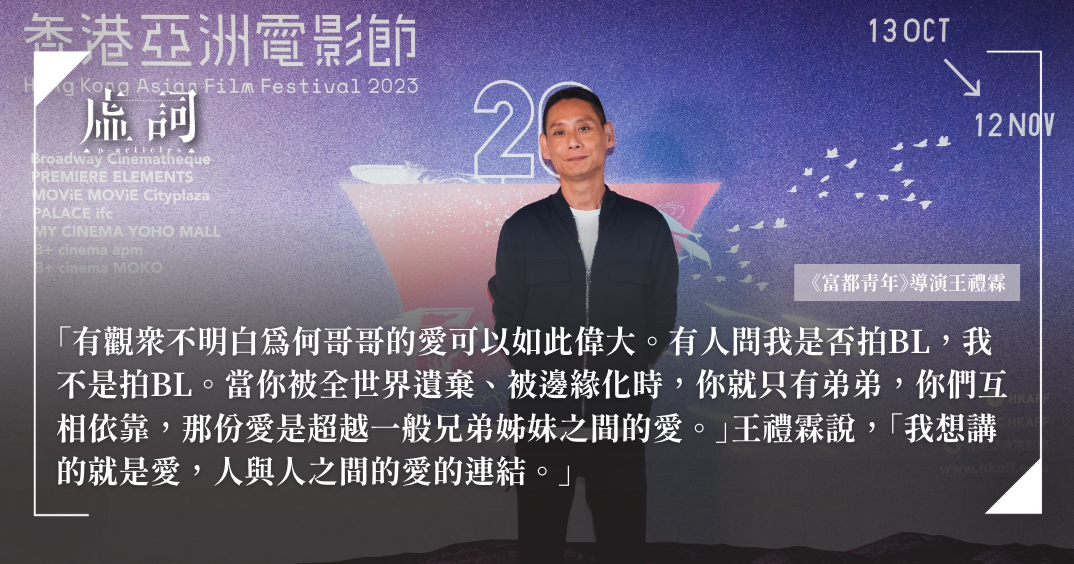【無形・過敏鳥】前置詞:明明無餘地再過敏?
無秩序編輯室 | by 無形編輯部 | 2024-01-02
過敏,是人體接觸環境中一些過敏原後,所引發的一系列超敏反應現象。那既是一種身體症狀,也可是一種心理狀態,由日常小小搔癢煩惱,到人際間的磨擦,甚至放大到社會整體,過敏粒子時刻都在碰撞。這些過敏原無處不在,偏又微小隱密,讓人難以言說,甚至羞於表露,免得被冠上反應過敏甚至玻璃心的標籤。然而,文學的價值正在於為幽暗而難以知覺的物事,給予恰如其分的言說。近年社會開始關注高敏族人士,呼籲人們肯定自身獨特與感受,如今或許正是書寫的時候。 (閱讀更多)
【新書】《字造海洋:香港.文學.海洋讀本》——前言:在香港讀海洋
書序 | by 黃冠翔 | 2023-12-29
香港島及諸離島星懸海上,與九龍半島對望,九龍則背靠新界諸山,可說整個香港地勢是背山面海,但從文學、文化角度看,香港長期都是背海之城。在城市發展歷史中,尚未出現如西方《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Sea )和《白鯨記》(Moby Dick)一類磅礡的海洋文學名著,甚至在早期,海洋鮮少成為作家投射、想像、稱頌的對象,海洋隱身於陸地之下,被城界排拒於外,海洋在文學作品中佔比偏低。然而,這個現象到了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有了變化,受到本土意識興起的影響,作家們開始看到本地的海洋,一九九〇年代甚至到了千禧年代之後有更顯著的轉變,許多作家開始挖掘香港海洋文化的價值,以海洋意象及想像作為創作主體,「文學海洋」在香港開始受到創作者重視。本書的編輯初衷,便是想喚起讀者和研究者的興趣,去探尋香港文學中「海洋」的面貌,藉此找回這座城市的海洋文化及其意義。 (閱讀更多)
香港作家李怡、譚劍同獲台北國際書展首獎 漫畫家智海奪金蝶獎銀獎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12-29
2024台北國際書展將於明年2月底舉行,近日(28日)公佈「國際書展大獎暨金蝶獎得獎名單」,當中香港科幻及推理小說作家譚劍新作《姓司武的都得死》,以及去年逝世的知名作家李怡晚年所寫的自傳《失敗者回憶錄》分別獲頒「小說獎」及「非小說獎」首獎。另一方面,本地漫畫家智海所設計的書籍《觀景窗》成功奪得台灣出版設計大獎「金蝶獎」銀獎。而近年移居英國的本地漫畫家黃照達,其由鄧彧、何萍萍操刀設計的漫畫結集《那城THAT CITY》,亦獲頒「金蝶獎」銅獎。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