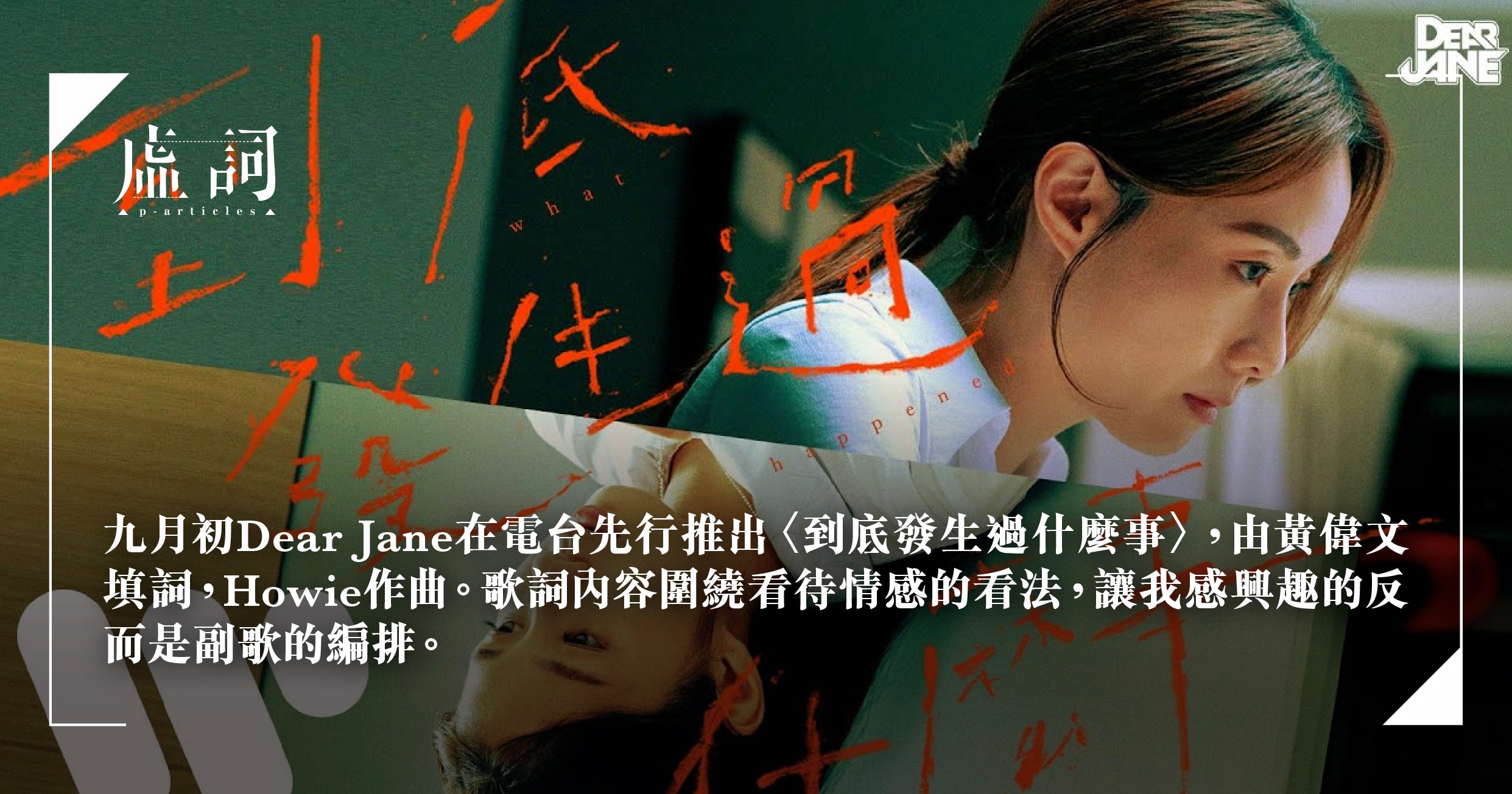九月初Dear Jane在電台先行推出〈到底發生過什麼事〉,由黃偉文填詞,Howie作曲。歌詞內容圍繞看待情感的看法,讓姚慶萬感興趣的反而是副歌的編排。黃偉文為Dear Jane所填的〈人類不宜飛行〉或〈脫骹的華爾茲〉,第一、二段的副歌皆是重複,這與大部分廣東歌的結構相像,但〈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卻在作曲上改變了一點結構,而黃偉文在這個帶有稍微變化的作曲上,注入了敘事的巧思。 (閱讀更多)
【一眼關七】觀眾需要隱喻
影評 | by 葉七城 | 2022-10-25
電影中的社工楊琦(周家怡飾)有句勉勵自己的座右銘:「體制夾縫中盡做」。今日的香港電影在這個體制之下,遭遇很大的打擊,在「新時代」的嚴苛電影審查制度下,電影不能描述與2019年社會運動有關的事情,創作空間被收窄,很多導演只有在還可以拍的題材下,滲進一些「隱喻」,抒發情懷,自我砥礪一番。《深宵閃避球》屢次提出:「喺邊度跌低,就要喺邊度再跌低!」是很中聽的,它消極中帶點積極,雖然放在電影的脈絡中有點語意不明,但不打緊,在這些年來有挫敗感的人,定能夠對號入座,找到箇中意義。 (閱讀更多)
【一眼關七】猛鬼.凶間.閃避球
這年頭,常有感於言論自由被打壓,真心話很難說,甚至不敢說,你不怕,團隊之中都有其他人怕,怕踩到無形的政治紅線,所以,於大眾娛樂作品裡能夠接收到某些聲音,就總是覺得份外討好。然而,借作品去說話,為反映當下政治現實,滲入各種弦外之音,說穿了其實不足以令它變成好作品。 (閱讀更多)
遠走何太遲?評《飯戲攻心》
透過四場主要的「飯戲」,〈飯戲攻心〉既莊重又溫情地回應一家人吃飯的傳統,同時也以吃和歡樂為武器,打破家庭這長久以來作為維繫道統倫理的關係,讓江俊豪印象深刻的,是導演陳詠燊為電影設計了大量金句,其中也有以零碎張愛玲腔調嘲弄家庭成員的。 (閱讀更多)
【建築雙年展 2022】尋找群展以外的行動者
空間 | by 蔡寶賢 | 2022-10-20
本屆《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以「集籽種城」為題集結兩地各建築專業、社區設計等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的參展單位,共同探討城市、建築及建構環境的議題。混雜些許疑惑與期盼參觀展覽,蔡寶賢認為每個參展單位背後所屬的策劃團隊、協作成員涵蓋不同界別的成員,箇中的社會影響力亦感染作為觀眾的她。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