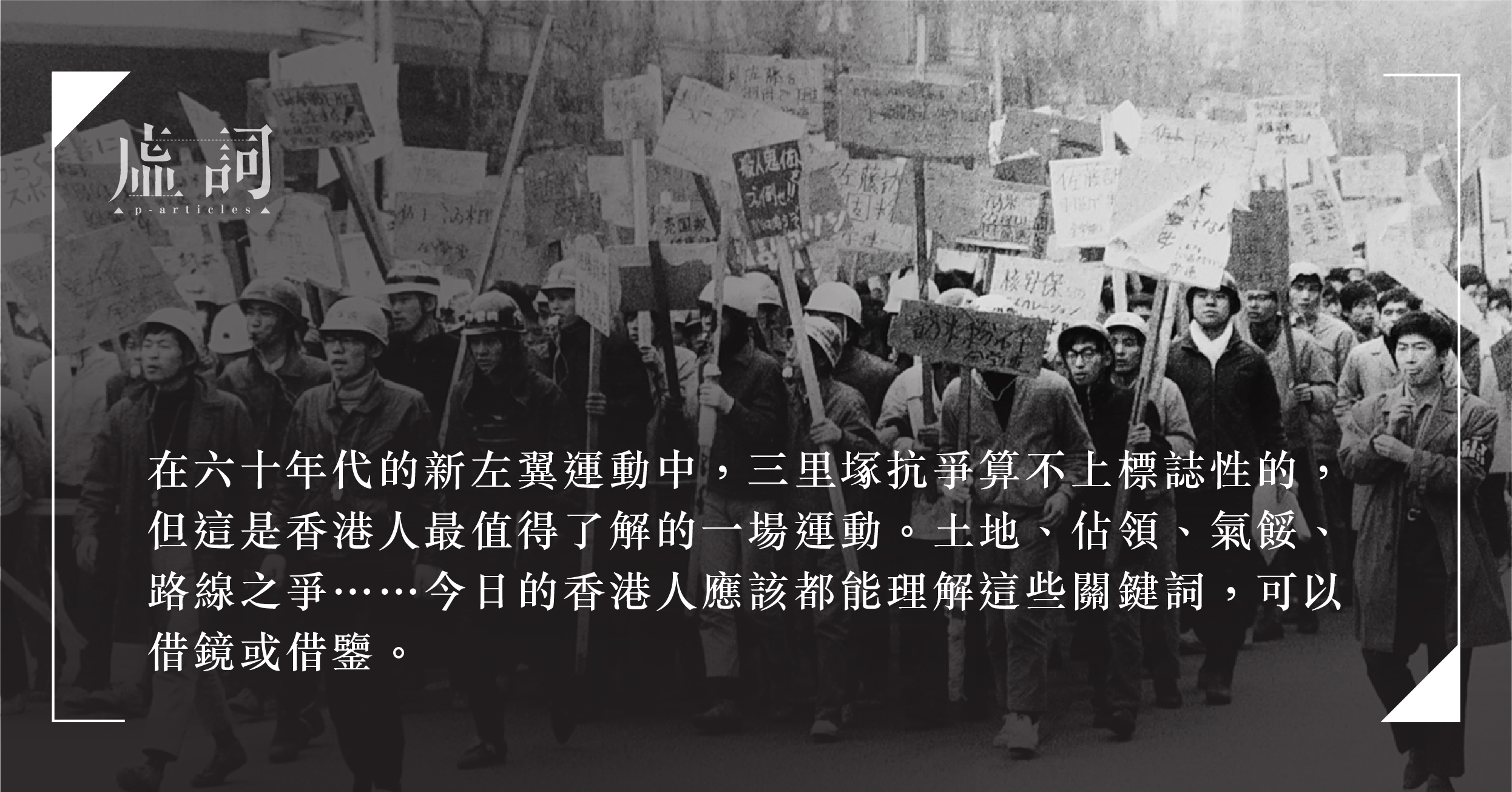命運、悲劇和善的脆弱性——評《我們與惡的距離》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閱讀更多)
聲有飛沉,響有雙疊──評戴望舒〈望舒詩論〉
對於戴先生,我還是十分尊敬的,原因就在於他曾翻譯了我最喜愛的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萊爾的作品,且譯得不錯。因此我在翻讀全集的時候也特別留意他對於詩歌的見解,其中〈望舒詩論〉就清晰地記下了他對詩的見解。這篇詩論以點列的方式書寫,應是創作雜感,篇幅不長僅有17句話,但這短短的17句話中矛盾重重⋯⋯ (閱讀更多)
當論述為國家機器服務時——南韓紀錄片《金君是誰》
影評 | by 伍麒匡 | 2019-05-10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閱讀更多)
《大象席地而坐》:不得不如此/去看看吧
大象並沒有代表什麼,牠或它很可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他們一行人來到中途站,老伯說,撐不下去了,他想帶孫女回去。不得不如此,要出走,不得不如此,要歸去。那一場韋布和老伯的討論,我總想起黃碧雲《失城》的陳路遠。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