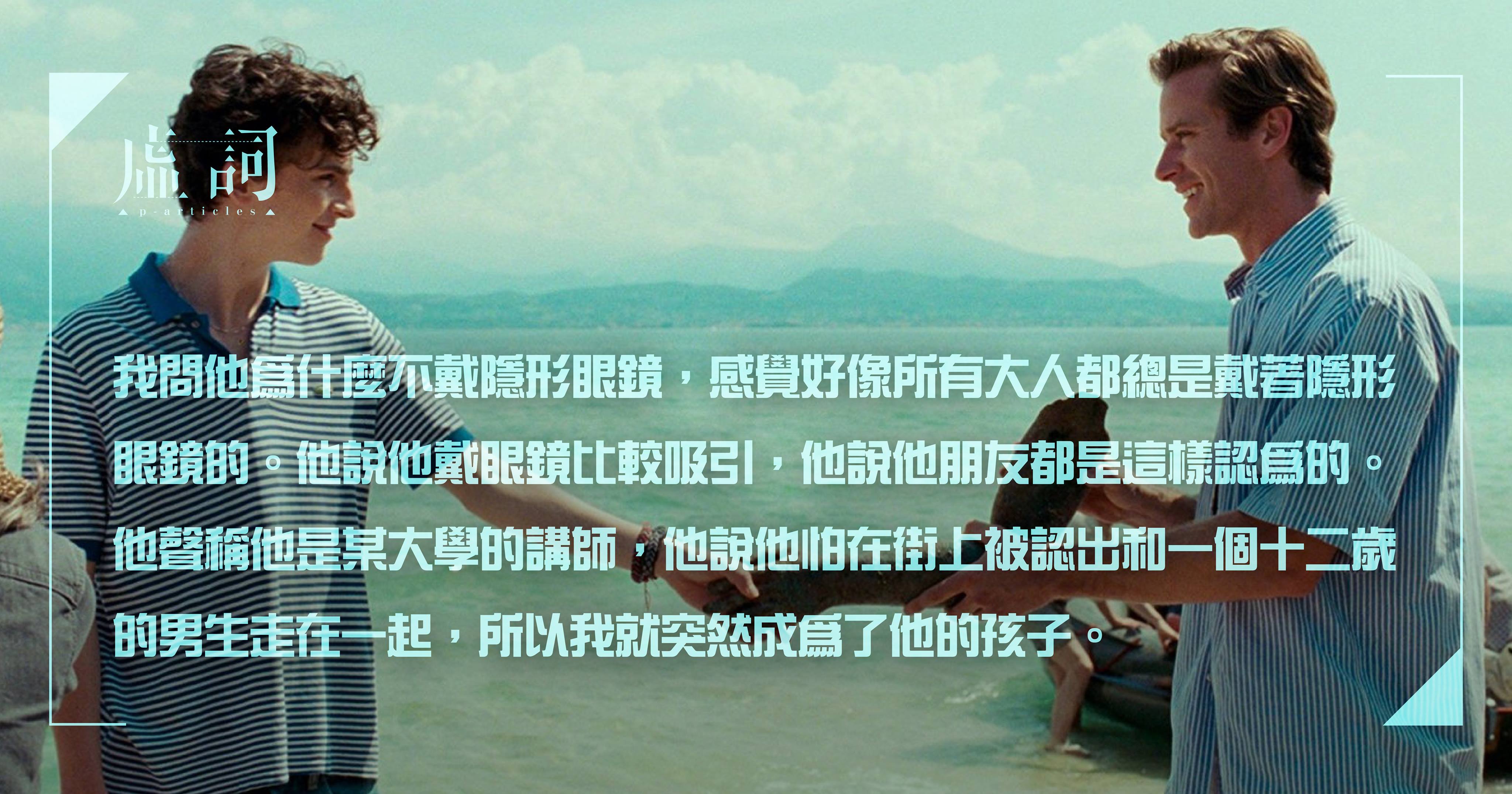十二歲
小說 | by 李楊力 | 2021-07-22
現在想起來,原來那時我還是十二歲,就只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我背著小書包,穿著漆黑皮鞋,獨自站在葵芳地鐵站A出口前,等待著他。我身穿天藍色短袖校服,天藍色是香港獨有的天藍色,那種永遠沾染著灰塵、曖昧朦朧的天藍色。但我不喜歡這件校服。老師和父母生硬粗暴地把我塞進這襲曖昧的天藍中,叫我站直,然後他們再一粒一粒紐扣扣緊了,如同縫紉著一道傷疤。
他們總想在你變壞之前把你弄壞,由他們弄壞了你,他們就得以治癒你,修補你。他們說我們是國家的花兒,所以我們總會有腐壞的一天,不是嗎?
十二歲是個適合腐壞的年齡。那腐壞的十二歲到底是什麼概念呢?
所謂正常的十二歲是:小學生放學時,會有一群家長在校門外簇擁著,等待著自己的孩子奔跑出來,然後那些小孩子就會跳進他們父母的懷抱裡面,就好像躁鬱症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跳樓自殺一樣。而我父母幫我在放學通告選擇了自行放學,表示我已經成長了,能夠獨立自主。所謂的獨立,就是獨自站立在茫茫的大街上,環顧四周等待著某個誰來接走自己。
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新聞報導,有小孩子在街上被陌生男子拖上貨van。那個男人緊緊抱著那個小孩子不放手。至少他們互相擁抱著,在交纏的手臂與肩膀間交換著體溫,那個小孩子的耳朵緊貼著那個男人的胸膛,傾聽著他澎湃的心跳聲。那輛貨van消失在CCTV的鏡頭之外,人世間的各種喧囂和混亂,從此,與他們無關。
真好。
當自行放學的小孩們如水散開,我站在學校門外附近的一棵大樹前,陳老師看到我自己一個,便走過來問我怎麼還不回家,我露出牙齒笑著對他說:「我正在等怪叔叔拐走我呢。」他臉上浮現出驚恐異常的模樣,應該是被我的蛀牙嚇壞了,果然喝得太多可口可樂。
還有三種正常的十二歲:要麼直接跑回家玩「跑Online」,要麼跑去補習社學習數學公文式。又或者,下課後在小賣部買一罐汽水和一盒魚肉燒賣,和小夥伴們一起吃,吃完便去足球場踢波。我有時候是屬於第三者的。所以,十二歲,就是汽水罐拉環拔開的那一聲,清脆而甜膩,只是我獨自習慣了某種乾裂而沉默的渴,一直解不開,好像斷開了的拉環,如果再去勉強拉開的話,就會割傷手指。
喝完汽水就去球場公廁的尿兜小解,用毒綠色的洗手液洗手,把一雙嬰兒肌的小手洗得如龜殼般乾燥。確實大部分時間我都活在這種正常之中,就當我決定到葵芳運動場的前一刻,還未腐壞的前一刻,嘉軒和家樂亦有問我:「諾然,你不一起踢足球嗎?」我打了個突兀,不知道怎樣開口解釋自己將前往葵芳,和一個素未謀面的網民叔叔見面,如果推託不去和他們玩,會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呢?應該也不會吧,畢竟有時候我也會自己回家看動漫,譬如看蠟筆小新,或者打機過副本。
我花了好些力氣擠出一句:「下次先。」
下次,十二歲就要腐壞了。
他與我相差二十歲,他聲稱。許多人所聲稱的事情,都不過是喉嚨發出的空氣震動而已,唯有外表是最為真實的。他戴著一副黑色粗框眼鏡,乾癟的臉上零星地散落著凹凸的暗瘡洞,瘦削修長的身段掛著一件灰白方格恤衫,穿著深藍色牛仔長褲,他看起來就像一塊洗壞了的毛巾,濕漉漉地懸掛在生鏽的欄杆上,只是比起相片,真人的骨感更加浮突。
我問他為什麼不戴隱形眼鏡,感覺好像所有大人都總是戴著隱形眼鏡的。他說他戴眼鏡比較吸引,他說他朋友都是這樣認為的。他聲稱他是某大學的講師,他說他怕在街上被認出和一個十二歲的男生走在一起,所以我就突然成為了他的孩子。
其實這個男人戴不戴眼鏡、到底是否存在著他所謂的「朋友」、到底是不是某大學的講師,都並非重點,重點是他是一個孤獨的中年男人,一個渴望著我的男人。
一個兒童的權力意識是從幾時萌生的?不是有所謂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開始,而是當我確確實實意識到:他(們)渴望著我,如同信徒渴望永生。我甚至覺得,我足以定奪他的生死。我叫他帶我去葵芳廣場的小食店買牛奶味雪糕和一罐可口可樂,等待著買燒賣的途中,我瞥見有一間格仔鋪有賣蠟筆小新的鎖匙扣,我情不自禁跑了過去,叫嚷著要買。而他也是非常配合我。
這個塑膠鎖匙扣上的蠟筆小新露出了他那童稚的陰莖,我每次望著蠟筆小新甩動著他那條「大象」,我不禁想像著:如果把他的陰莖放在嘴巴,那會是什麼味道呢?麥白色的短小陰莖會不會像麥當勞的炸薯條,只不過被人拗斷了?鬆脆的,鹹鹹的,吃了一條,還想再吃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還要蘸一蘸茄汁潤滑。
買好了雪糕和可樂之後,我們帶去葵芳運動場的長椅上吃。
那個男人為我撕開雪條的包裝,從上而下緩慢而克制的撕下,彷彿那撕下的是我的內褲。現在的我應該再也笑不出來,但那時的我掛著十二歲該有的笑容,天真無邪得合格,我把雪條毫無保留地含吮在舌尖與幼齒之間,我把頭歪側到一邊從下到上舔著雪條,櫻桃色的嘴唇四周黏著一層薄薄的乳白色的汁液,我再次伸出舌頭,闔上眼皮,舔乾淨嘴邊殘留的汁液。
他吞了一抹口水,在我耳邊問道:「你有試過接吻嗎?」我感覺自己臉頰頓時通紅,羞澀靦腆的暖流從頸椎湧上臉龐。我只顧著搖頭,除了搖頭,我也不知道能如何回應他。
這是愛,這是我的初吻。
他把我按倒在廁格灰藍色的牆壁上,不斷舔吻著我的嘴唇,那舔吻的頻率仿佛蒼蠅在小狗流血的屍體上嗡嗡自鳴似的。不知道為何,我的身體就是很自然而然地反抗著,試圖推開他,但到最後身體漸漸變得柔軟,好像被打火機燃燒的塑膠,融化的過程中一點點液化,滴濕了。他脫下我的校褲,他不斷與我摩擦著,那一刻,我發現我居然勃起了。我忽然明白了常識科教過的青春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
他將陰莖塞進我的嘴巴裡,原來陰莖的味道是鹹臭的,嚐起來像是放了太多鹽醃製的茄子,雖然鹹了點,但還是有營養的。我記得我媽媽晚餐的時候,也特別喜歡在我的飯碗上塞滿各種的菜,滿溢得飯粒都掉在桌上,仿佛飯碗就是我的洞穴。在瀕臨高潮的前一刻,那個男人拔出陰莖,射在廁板上。他抹了抹自己,抱了一下我,他的頭靠近我的眼前,他那黑色粗框眼鏡上浮起一層薄薄的水氣。他打開廁門跑了出去。其實他並沒有對我做過什麼,而這也是他對我最後一刻的慈悲。我那件天藍色短袖校服上,沾染了他混合著薄荷牙膏味與白飯味的口水。那是一種體貼而造作的香味,試圖用一種慾望掩飾著另一種慾望。我扣上校服鈕扣,一粒一粒慢慢縫紉上一條濕臭的裂縫。
那個男人也是一個寂寞的人呢,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