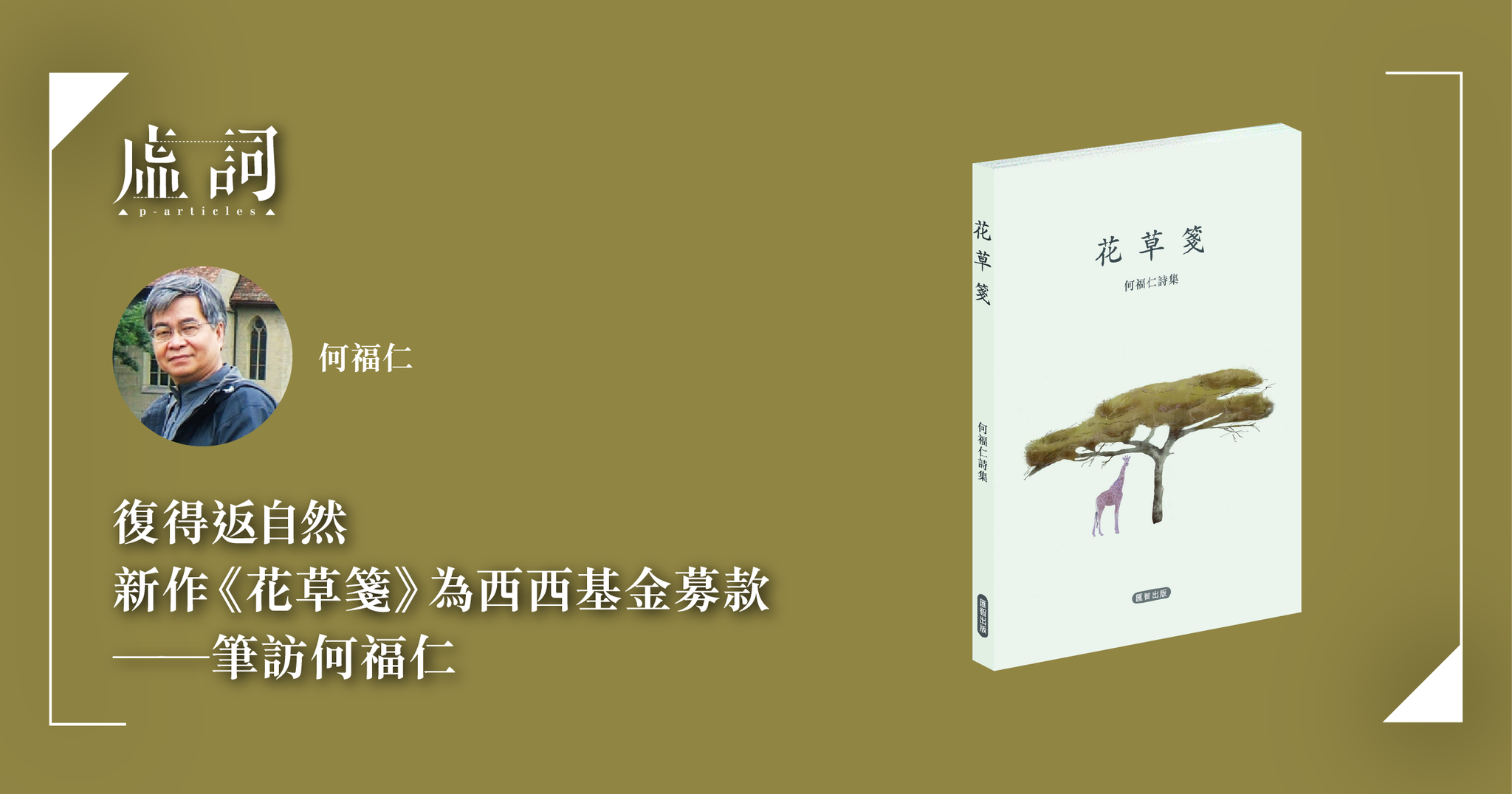「我希望電影能帶給人生存的勇氣」——訪康城影帝役所廣司
專訪 | by 王瀚樑 | 2023-11-07
曾出演《談談情 跳跳舞》、《鰻魚》、《失樂園》等經典電影,三奪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的役所廣司,今年憑藉在《新活日常》(Perfect Days)中飾演公廁清潔工平山一角,成功在康城影展上登上「影帝」寶座。役所廣司近日接受香港亞洲電影節邀請到港宣傳新作,並接受傳媒訪問。這名新鮮出爐的康城影帝,訪問中卻說會努力讓自己生活得像一般人,因為他認為「像普通人一樣關心事物,對人保持強烈的好奇心,是作為演員的重要特質。」 (閱讀更多)
如回憶都失去了 由我們幫她記住這個家 ——訪《4拍4家族》導演賴恩慈
專訪 | by 王瀚樑 | 2023-11-01
繼2010年首次執導的獨立電影《1+1》及延續篇《N+N》後,賴恩慈在新作《4拍4家族》之中,再次講述一個家的故事,不過這次她以音樂為題材,透過搖滾音樂,把支離破碎的一家重新連結。創作是一種自我剖白,賴恩慈在訪問中透露,對家的故事念念不忘,是因為她在成長之中沒有機會感受尋常家庭的溫暖,於是把這份溫暖放進電影之中,與觀眾分享她的記憶。 (閱讀更多)
訪問鄭宗龍《池上專屬版——天光.霞》:將身體交付天地,剝開內在霞光
池上氣候生猛,一邊低著厚雲,另一邊太陽就亮晃晃地撒下燙熱。 沿著滿街的標示,搭乘前往「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舞台的接駁車,從池上市區逐漸駛入金黃稻海,人也變得燦爛。如同某種朝聖旅途,距離秋收舞台十分鐘路程外下車,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的觀眾披著日光徒步,身旁無數稻穗飽滿折腰。 一整個地方的慷慨展現眼前。 池上的學生們夾道歡迎,喊出熱情口號;居民們作為志工指引方向,猝不及防送上一個笑容。外界紛擾似乎就此止步,心靈無負重地邁進山巒環繞的田野。 (閱讀更多)
詩人化身小說家,寫一個另類武俠世界——訪韓祺疇新書《虛風構雨》
詩人寫小說,也許平常不過,但如果詩人寫武俠小說呢?曾拿下台灣金車現代詩獎的「最年輕得主」韓祺疇,於本年的「天行小說賞徵文比賽」獲獎而得以出版其參賽作品《虛風構雨》。與傳統武俠小說不同,這部具有後設元素的武俠小說,不僅以「九流十家」作為派別,更將不入流的「小說家」秦顧設為主人公,連同縱橫家懷玉,兩個末代傳人,對抗儒法大道,足見其破格創新與匠心獨運。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