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李嘉儀《曝光》:透過文字來攝影,直面回憶的療癒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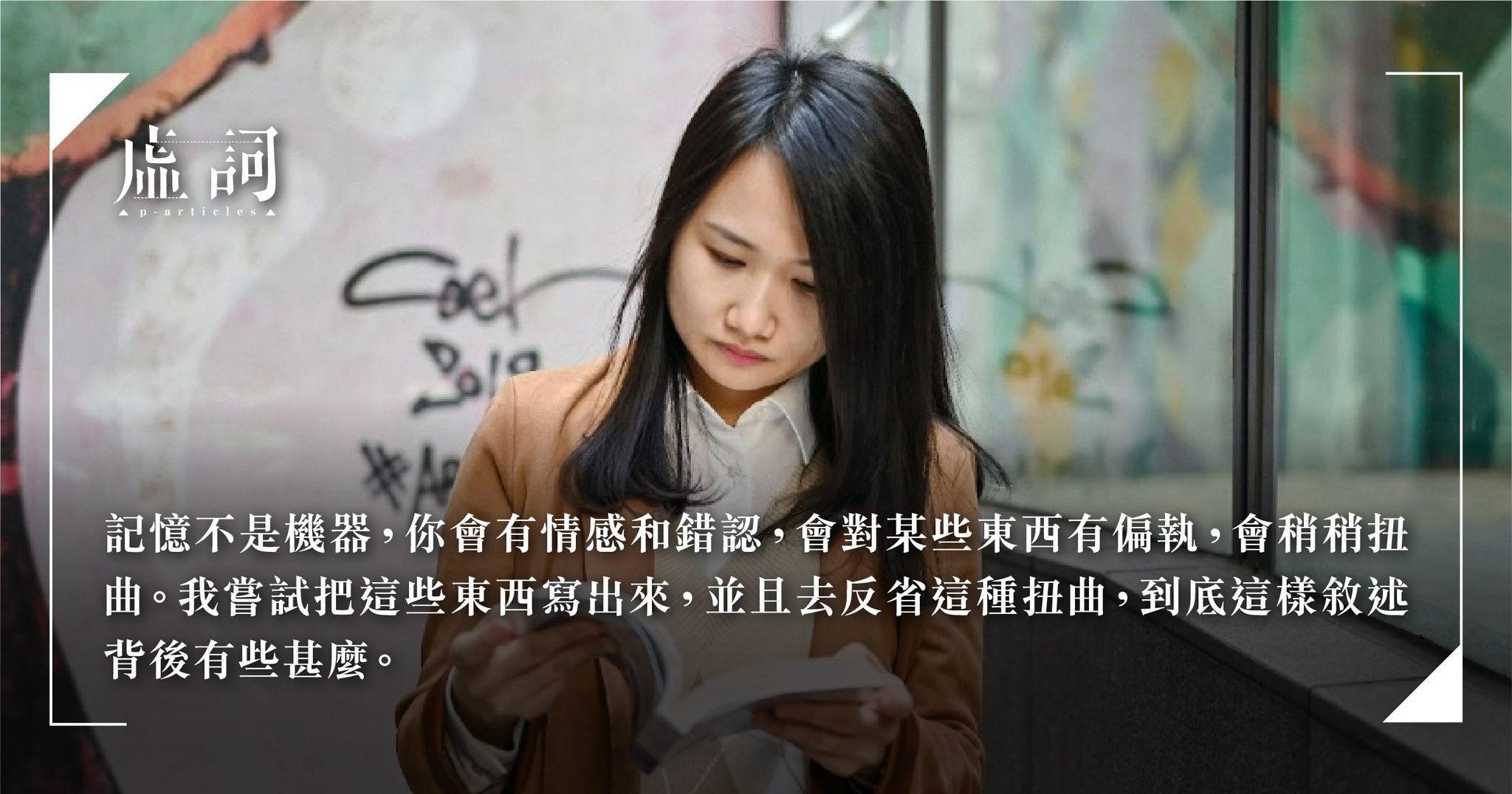
322628365_472775025061348_4227695284437259868_n.jpg
法國作家杜哈斯(Marguerite Duras)是李嘉儀喜歡的作家之一。杜哈斯在《情人》裡書寫只有她一人看見的記憶影像,李嘉儀新近出版的、以旅行為主軸的散文集《曝光》,其實跟杜哈斯的書寫同樣,是一種朝向回憶、朝向自己的姿勢,回憶的擴寫和延續,好像潮水一樣,退了又再回來,無窮無盡,如永晝白光。
《曝光》的文章經年修改,一趟文字旅程,把不同時間點的自己疊加在回憶的影像之上,一再敘述它、橫越它,並且保留一個再被橫越的可能。「這是我的曝光。」李嘉儀說。對於不諳攝影的她而言,文字就是她的攝影術。
我可不可以透過文字來攝影?
李嘉儀形容,她是一個視覺主導的人,腦裡有時會出現很多一閃而逝的畫面,就像畫集一樣充滿了影像。她一直很想學畫畫,羨慕別人可以把腦裡的影像畫出來。
《曝光》裡的文章,記述了2014年和16年的兩次遠遊,雖然出版前她一直有回去修改、擴寫它們,但那回憶的起點,幾乎就像照片一樣,拍下來,意義持續增生。旅程的發生其實跟創傷有關,那些年經歷人生挫折,記憶和創傷糾纏如黑暗團塊,濕疹首先發難,過去熟悉的詩也突然變得陌生,「那時好像被詩歌棄絕了,甚至不想寫詩,變相希望尋找另一些媒體讓我表達,感受自己。」
她嘗試寫散文,亦接觸了星野道夫、森山大道和杉本博司等攝影師所寫的札記。她感興趣的不只是他們的攝影作品,甚至問她會不會有興趣學習攝影時,她幾乎斬釘截鐵地回答,「完全沒想過要學」;對她來說,無論是講求瞬間的星野道夫和森山大道,抑或思考如何累積光、如何把時間壓縮在底片上的杉本博司,真正有趣的是這些攝影師如何操弄時間。
「我覺得攝影師和作家很相似,其實我都是在操弄我的記憶而已。」作家嘗試在文本中打開一個無限時間,如何把時間停住、延長,把一分鐘寫成一萬字,都是她覺得很有趣的書寫經驗。而在創傷記憶裡,原初場景緩慢流動,就像在她腦裡留下一個畫面,顯影一個影像,「但我沒有辦法把照片沖曬出來,亦沒有辦法回去拍攝自己。那麼,我可不可以透過文字來攝影?不是單純描述,而是我也變成風景的一部分?」
永遠前進的文本
透過文字來攝影,抑或透過文字來處理回憶的影像,處處令人想起杜哈斯《情人》的回憶書寫。
李嘉儀形容,《情人》最開頭的部分其實是杜哈斯通過不同時段的自己來敘述過去的事,時性不是統一的,而是不同時間點的自己會突然加插進去,又突然以兒子的照片比照十五歲半在渡輪上的少女杜哈斯,「其實是兩個時間在同一個文本裡疊在一起。」後來《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一樣是對同一段記憶的操弄,只是切入和呈現方式不同。
這種疊加,也是李嘉儀的書寫姿勢。她說,《曝光》的文章雖然是關於2014和2016年的旅行,但她這幾年一直修改文章,把不同時候的自己加插進去:「一篇文章裡有2014年的聲音,一直修改,到2021年有些事情的想法可能不同了,或者我改變了,好像不斷有聲音加進去,不同的敘述在溝通。」她形容,就像一直處於一個未完成或修改中的狀態,是一個永遠前進的文本,「不同的影像混雜、壓縮在一個文本裡,這個文本就是一張照片,是我的曝光。」
情感作為書寫索引
李嘉儀有見治療師的經驗,曾和治療師一同嘗試敘事治療。這些經歷某程度上啟發了她的書寫:「例如它需要你回到原初場景,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正正是寫作過程。」她提到,散文往往要求真實性,但經歷同一件事的人往往有自己的觀感,這些情感就是文學所在,「記憶不是機器,你會有情感和錯認,會對某些東西有偏執,會稍稍扭曲。我嘗試把這些東西寫出來,並且去反省這種扭曲,到底這樣敘述背後有些甚麼。」
歷年修改,說來就是一趟反覆回顧和反芻,不斷從原初場景中增生的旅程,作品彷彿跟她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甚至在其中獲得了有別於作者的,一己的生命。李嘉儀沒有嘗試站在一個制高點來書寫自己,而是像身處敘事治療的過程中,沿著生命裡的刺點作為書寫索引,一再回到記憶,回到自己身上,分裂以作保存,「你是用第三身角度去看,敘事治療通常要你講另一個故事,你可以做事件裡的自己,同時可以跳出來跟當時的自己說話。」
她形容,每次完成敘事治療,都會發現原來自己對同一件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情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自我不是完整、全知的,反而是可以溝通,充滿可能。「所以我對那種傳統記事抒情,或記敘一件完整的事和感受,不是太感興趣。反而我們沒有打開自己的一些可能性,沒有讓自己進入這些空間去理解。或者說,我們自己是不是可以溝通的?我覺得寫作就是給了一個好好的空間,讓一些內在聲音得以被聆聽。」
書寫他人的權力
在《曝光》裡,李嘉儀抵達了加拿大、泰國、美國拉斯維加斯,細心閱讀,會發現她鮮有以觀光客的目光來凝視他地,而是遭逢了一個又一個的人,原住民後代、言語不通的泰國女生、住在美國賭城的家人⋯⋯如果說書有一半是通往自我的心靈風景,另一半可能就是由人的關係交織而成的網絡。
而書寫他人就跟書寫自己一樣,她無法站在一個制高點去寫:「其實我是誠惶誠恐。寫作一定存在權力,因為你有說話的聲音,很多人可以聽到看到,被你寫進去的人可能永遠沒有這把聲音。」對於書寫可能造成的傷害,她只好盡量承接,盡量坦誠,對於無法肯定的事,她很多時以「或許」、「也許」來寫。書中〈木屋〉一篇尤其明顯,「那篇特別多『或者』,我會呈現出來,不是那種已經知曉一切,或一個敘述者高高在上,而是把一些可能性還給那些人。寫的時候盡量保持這份質疑。」
幾次旅行,比起觀光,她更在意當地人的生活,尤其是她內心極為嚮往的原住民文化和自然風景。也不是一種消費性的凝視,而是一再通過「我們」這個主語來嘗試接近人類的普遍經驗,譬如加拿大原住民對族群、言語、神靈和地方的情感,從中提取一種對連結的渴望。「我想,在旅程中有很多機會接觸到別人的眼睛。單單用我的眼睛並不足夠,我期望可以借用他們的眼睛,這個借用某程度上都詮釋了他們如何看待世界。」
對自我的質疑
然而,對於自己的這份善意,她不是沒有質疑。
譬如她在〈賭城散步〉裡提到的拉斯維加斯的乞討者,出於旅人的好奇注視他們,卻被長居賭城的親人責備她招惹麻煩,前者是同情心使然,後者是每天發生槍擊案導致的不信任情緒,兩者某程度上都可以理解。「最恐怖是我要用姐姐的視角,自此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注視他們,原來我要在這個地方生活,都要跟從這些法則。我姐姐應該都認為他們很慘,但你一定要轉換視角,如果你太有同情心就很難在那邊生活。」
自己的眼睛,他人的眼睛,想起《曝光》的封面是一對圓藍的眼睛,中間是一抹半透明的印花。所謂風景或人生在世,或許永遠是在兩者之間擺盪。
談到寫作,李嘉儀總是說,文本是未完成的:「我只是放棄修改它,往後可能還會不斷修改。」書寫既是一次坦誠,也是未竟全功的長路風景,回憶的影像可以疊上更多層次,就如人的不斷成長,不斷前進。惟有回憶始終沒有結束,永遠沒被遺忘,回憶的強度恰好在於它容讓我們一再往返,一再在水裡沉默潛行。而出版對李嘉儀來說,只是浮上水面的瞬間,聽見了空氣流動和他人的回聲。
「然後我就可以繼續游。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好像未完成,但即使未完成,都是一個我橫越了的⋯⋯是不是可以這樣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