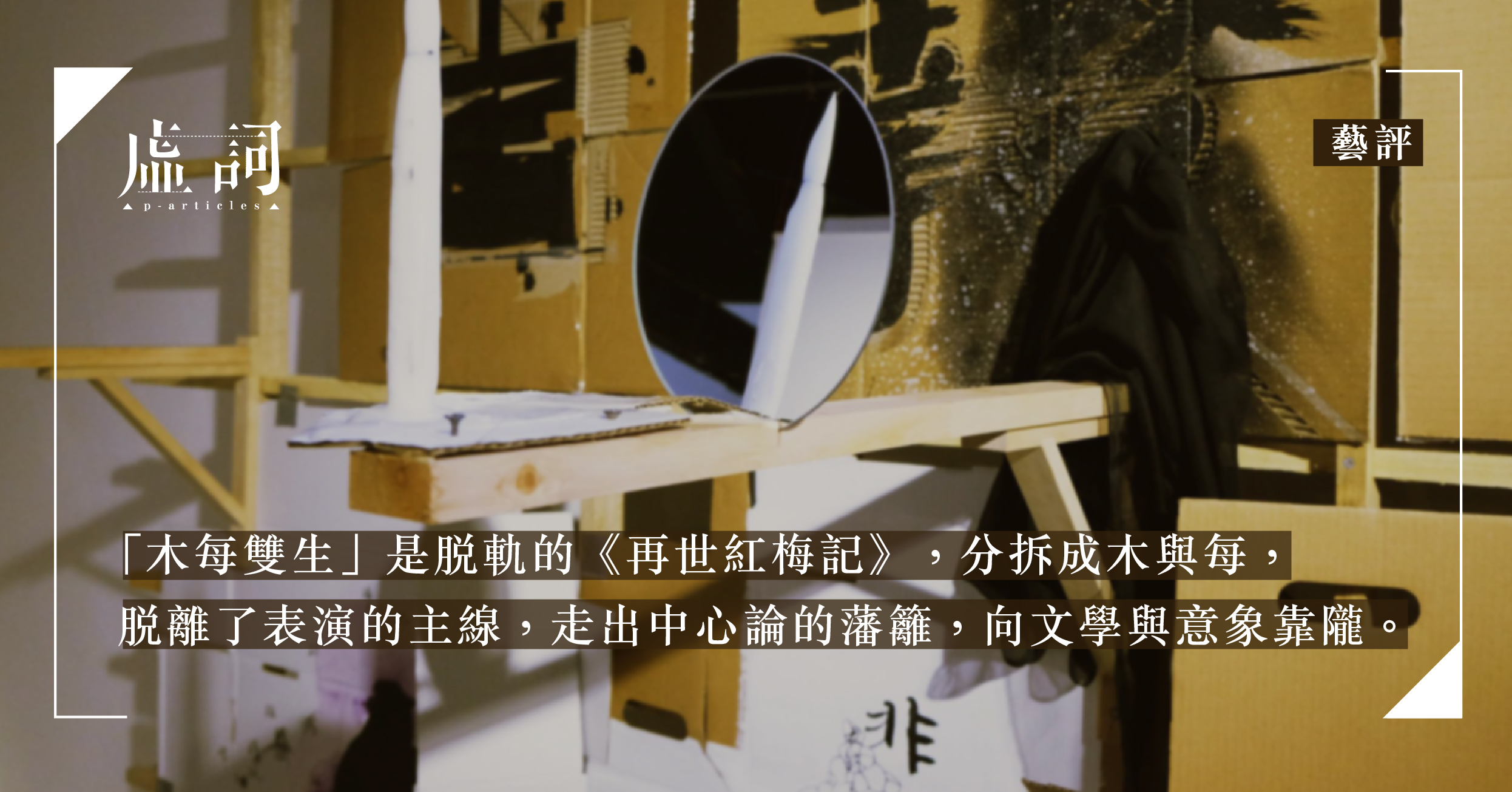記得當日出席展覽「木每雙生:文學視藝的再世紅梅」的開幕後,到了附近的餐廳晚飯,在旁的一枱客應該是戲迷,剛聽過阮兆輝、秋孟的開幕講座,然後你一言我一句,語氣帶點權威,除了討論誰與誰的唱法外,還提到文化博物館中的粵劇照片出錯,又說戲曲中心的導賞只作建築上的解說,而不講解劇目等,當然,我無法考證當中的真偽,因他們所熱衷的唱唸範疇,正是我所陌生的。 (閱讀更多)
「藝術勞動・買定離手」:讓被挑選的小朋友玩一下藝術版大富翁
跟據網上的資料,遊戲「大富翁」的設計原意為抗議地主壟斷土地,玩家在遊戲的過程中,必定經過人生高低起跌,甚至破產入獄,但我相信絕少人會因此而害怕玩「大富翁」,說到底,它始終都只是一個遊戲,甚至,我有懷疑過壟斷、爭勝可能是人性本有的慾望,實際上我們透過遊戲取得便捷的快感,然後,我們只能從網上的資料,才得悉「大富翁」的設計原意⋯⋯ (閱讀更多)
《城巿行者日記》與狄雪圖的步行理論
因為黃志恒策劃的「火花!城巿行者日記」展覽前言引述《日常生活實踐》中的這句話,讓我又回去重讀理論家Michael de Certeau(狄雪圖,又譯塞杜/塞托)。他是在研究院時其中一個受到教授重點推薦的名字,當時我記下的重點是生活每個細節都可以是讓主體變化違規的機緣,然而那些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一再對於意義的塗抹消弭,總是在記憶中難以捕捉。在香港,我們幾乎無法相信,可以有一整個視覺藝術展覽是根據一套理論而策劃出來,這個城巿實在是太反對抽象了。但重溫狄雪圖的理論後,我則傾向認定,黃志恒對狄雪圖的引用絕不止於斷章取義或只作為一個起點,而是將其思想貫穿在展覽的編排中。 (閱讀更多)
一旦視覺崩解,願回憶與氣味同在
香港文學館展覽「氣味相投」,以飲食切入文藝,取中醫藥理中的「五味四氣」——「辛、酸、甘、苦、鹹;寒、熱、溫、涼」——為起點,邀請九組作家和視覺藝術家通過創作對話,每一種屬性配對一位作家和一位藝術家(唯獨「寒」的黃仁逵例外,一人包辦文字與視覺創作),結構沿襲自文學館過去策劃的展覽如「島敍可能」和「無何有之香」。創作者各各自由發揮,不過藝術家須閱讀文本,部份作品呼應、轉化文本,另一些組合的操作則更為鬆散,各自發揮特定屬性誘發的想像。 (閱讀更多)
等待景至:策展前中後的九項線索
藝評 | by Ivy Ma | 2019-01-14
我一直對一幅畫的生成非常感興趣。十多年前,培根(Francis Bacon) 的工作室被「移植重組」成陳列品,在都柏林美術館展出,我看過後印象深刻。之後我便認為工作室的種種硬件,以及畫家如何使用這空間,其日常性、勞動的模式及由此衍生的心理狀態等,這都跟畫家最後完成的畫作,有著微妙的密切關係。 (閱讀更多)